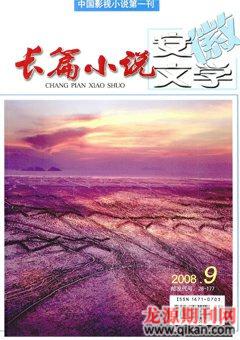社场上的风
王学银
一入夏,天气便炎热起来,知了也整天在枝头鼓噪,晚上坐在空调的屋里,身上被风吹得凉凉的,这时便想起儿时在乡下的社场来。想起它,便让人不由得想起那些亲切而生动的日子。
乡下的社场一般选在地势较高,离村庄稍远,交通便利,四周无障碍的空地。这些要求除了便于收割庄稼、便于搬运、便于排水以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了扬场时好找风向。没有风,粮食中的草屑、杂质便无法分离出去。在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没有电灯,也没有平顶房屋可上去的年代,这样光光的社场,加上地势迎风,自然就成了全村老少夏夜纳凉的首选去处。经过白日的酷热折磨了一天的人们,在场上铺上麦秸秆织成的稿荐,上面再铺上高粱篾席子,仰面躺着,面对满天繁星和浩瀚的月光,舒心异常。白天难耐的酷暑和辛劳都随这夜风飘逝而去。
“风婆婆,放风来,大风不来小风来(小风不来大风来),莫把口袋扎起来……”闷热难耐的时候,场上总有孩子们在嚷。越是没有风,睡不着的孩子们喊得越凶,而此刻的大人们却能容忍孩子们的喧嚣,有时还鼓励他们下点劲,“喊风”的声音再放大一些。
往往,会有一丝凉风习习吹来,人们便四下里拽着铺盖找风向,一排排铺得整齐的床铺,便重新整合。无论从哪个方向飘来的一缕凉意,都让这些赤身裸体的汉子们欣喜、兴奋!
最苦的是家中的女性了。男人可成群结队地来到场上,赤身裸体地享受缕缕夜风,而女人则只能呆在家里,顶多坐在门外的软床上扇着芭蕉扇。为了全家人的一顿晚餐,她们每个晚上都要被汗水洗过几遍。那时吃的是青一色的杂面馍馍和稀饭,有时能吃上一顿面条便是上等的饭食了。有的家庭早晚只喝稀饭,别的啥也没有。但无论如何,只要能填饱肚子,剩下的就只有快乐了。
每天晚上,最早到场上的都是一群一群的孩子。在大人们未到之前,他们疯跑追逐,做游戏。刚刚洗过的身上马上又淌满了汗水,等大人们到后,便又纷纷跳进黑乎乎的水塘里,扎上几个猛子再爬上来。
社场上最吸引孩子们的,是那些走过南闯过北,又有些文化的人,他们用古今故事,迷倒一大群爱动的孩子们。像唐僧、沙僧、猪八戒、猴子精所遇的九九八十一难,像门闩、门鼻、门镣条智斗妖婆的古,像白蛇爱许仙的故事,还有尼克松访华见到中国爆米花时的惊讶等等。尤其是那些流传于乡间,发生在南山北湖,与村人、乡邻有关的神、鬼、人、妖的故事,让人听了既惊恐又兴奋,而且感到亲切。
其中说到,几十年前庄上有个叫王老六的,长得高大威猛,是方圆百里有名的土匪。某一天,他们那帮土匪在寿县、凤台交界一带犯了事,官兵将其拿下并砍头示众,同时被杀的有几十人。庄上有个卖糖果的生意人,背着布口袋在凤台城墙外看到了被高高吊起的王老六的头颅,据说那人头看到他后,两眼使劲的眨巴三下。生意人心中有数,当晚三更时分他摸到城墙上,从众多的人头中找到了那个朝他眨眼的,装进布袋背着连夜返乡。生意人一路上害怕极了,汗水和头颅流出的血水顺着他的脊背往下流。由于心里慌张又遇上是夜黑头加阴天,生意人根本也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水,遇岗翻岗、遇沟扑沟,只管朝着东北方向没命地狂奔。半路上他觉得背上的那个头老是乱骨碌,吓得头毛都竖起来了,他边走边念叨:“老六啊,别吓我,我带你回家。老六啊,别吓我,我……”那头倒也听话,听过之后便不再动了。天亮的时候,生意人终于回到了村里。村里人给王老六买了口棺材,并请木匠师傅为他做了个木头身体,将头放在木人的脖子上,穿上新衣服后,葬在了庄东头的松岭。原来,那王老六生前虽作恶多端,但从不祸害村邻,在家里始终都表现得很谦恭、很老实、也很懂礼,看不出他哪儿像个土匪,只是恶名在外罢了。而那生意人原本也很仗义,看到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同伴,客死他乡、身首异处,心里挺不是滋味。所以才肯冒死去偷他的头颅带回家安葬。
那些故事现在想来是有些简单、粗糙、零乱之嫌,但那时听到的,要比什么小白兔、大灰狼之类的东西,地道得多、睿智得多、够味得多!许多人家城里亲戚的孩子,一到夏天就到村里来,一过就是一个暑假,开学了都舍不得走。我想这与当时“社场文化”的吸引是分不开的。
农村的生活简单而质朴,孩子的生活则更单纯。
白天,大人们在生产队长的哨音催促下,一队队地下地干活去了。全村分为劳动力、妇女、青年三个组,有时还有科研组。根据各组自身的特点和条件,各组工作的内容、性质也不相同。而孩子们最大的愿望是能在天一亮就跑到社屋去抢一条牛放,抢着一条牛放,一天也能挣3分工。由于孩子多耕牛少,有时候不走后门还放不上牛咧!生产队也有数量较少的驴、马、骡子等牲口,它们被称为“圆具”牲口,我想可能是因为蹄子呈圆形且不分叉的缘故吧。而这些牲口是万万不能让孩子们靠近的,更不敢让他们去放了。它们性子一般都很刚烈,常常踢人,好尥蹶子,头硬,小孩子根本拽不动它们。而那耕牛就不一样,它们性格温顺、舒缓,整日里慢条斯理,如宽厚仁慈的长者一般。想怎么牵就怎么牵,想怎么骑就怎么骑,它们从不欺负小孩子。放牛的孩子们常常折柳枝编帽子戴在头上,称自己是“朝鲜军”,在河滩上玩打仗,互相抓稀泥做子弹。打得激烈的时候双方参战人员的鼻子、眼睛都被稀泥糊住;实在看不见了,跳进水里洗洗,然后上岸再战。最得意的时候是中午、晚上,等所有牛都吃饱了,到了收工的时间,孩子们纷纷爬上牛背,坐在像方桌一样的牛背上,戴着“朝鲜帽”,甩着鞭花,唱着随心所欲的歌,晃晃悠悠地往家去。看看那长长的牛队,总让人觉着有那么一种从战场上凯旋而归的神气劲儿。
抢不到牲口的孩子只能靠割草来为家里挣点工分了。每天傍晚在社屋旁的水塘边,总有长长一排的青草堆在沟里泡着,天快黑了大人们收工了,饲养员才开始用大秤称青草。能走上后门的一般先称,且草筐从沟里抬上来马上就称,筐里的水流得哗哗的。走不上后门的就不行,必须让草筐在地上放一会,待水快流尽了才给称。能挣几分工的孩子,回家后大人当然很高兴,但若真的不愿干也没什么,很少有大人逼着孩子去割草、放牛挣工分。这些活计主要是孩子自己想干,人多成疯,成群结队干什么都快活,根本就没有苦和累的感觉。真正酷热难耐的时候,村里所有活计都放在早晚做,孩子们便整天泡在水塘里洗澡。
那时候,农村七八岁以上的孩子全会凫水。在好几米深的大塘里,上面的水皮被晒得很热,甚至烫人,下面的水则清凉清凉的。有时全村二三十、三四十个孩子集中在大塘里比赛,比扎猛子时间长、比谁扎得远、比凫水速度快。最高级的是比扎猛子抓塘泥,抓塘泥是一般孩子很难做到的。在5米深的塘里大多数人只能扎到一半就憋不住气了,只得赶紧返回水面。而能一猛子扎下去抓上一把塘底的稀泥上来的,那才叫过劲,才叫厉害。
抓塘泥的过程让人体验着多种感受。首先从被晒热的水皮向下,到温水,再到凉水,最后到更凉的塘底,那感觉真叫爽得过瘾。但在潜入水底的瞬间,在那冰凉冰凉的水里,除了刺激以外,还会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一种在陌生环境里的孤独和紧张。在那极其兴奋而紧张的几秒钟过后,自豪感便立即涌上心头。抓上来的塘泥自然舍不得扔掉,都抹在自己或伙伴的脸上、头上,抹得乌黑。与其说是为了感受塘底稀泥的凉意,倒不如说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本事。
当然,夏天孩子们的乐趣还有许多。比如在竹竿头卷上一层一层的蜘蛛网,或直接用面筋粘在竹竿上,去粘满树鸣叫的知了,去粘落在辣椒、瓜果秧上、小树枝上休息的各式各样的蜻蜓,还有到屋檐下掏麻雀,去田埂上掏黄鳝,用麻纱布捉虾,捉青蛙喂鸭子等等。每一项活动都充满乐趣,充满智慧,也讲究技巧和方法。一旦迷上某件事,几个伙伴一干就是许多日,乐此不疲。
无论白天疯到哪去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孩子们便纷纷带着铺盖或三五成群,或由大人带着来到场上,一天中最有乐趣的时刻便又开始了。
今天,空调的凉气让人能够很舒心地度过炎炎夏季,让人迷恋四四方方的房间。而我却常常想起三十年前那阵阵自然的风,以及那烙入心扉的人和事。尤其在夏夜。
一阵风,飘到了社场上。飘到那个繁星满天、皓月当空的夏夜;飘到那个令人怀想、轻松和谐、无忧无虑的年代……
责任编辑赵宏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