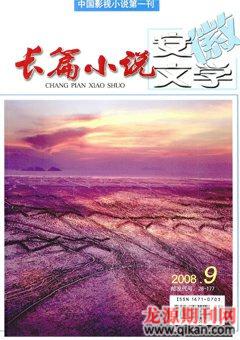瞎子阿姨
倪 东
下乡第五年的春节,我从苏北农场回常熟探亲,第一次见到了瞎子阿姨。她大约50来岁,矮矮的个子,齐耳短发。她双目失明,还驼着背。可她的耳朵特别灵,听到我的脚步声,她便猜出我是谁了。母亲把我拉到她的面前,要我像小孩似的叫她一声“阿姨”。可我从前不认识这个女人,吞吞吐吐地叫不出口。母亲说:“20多岁的小伙子还像大姑娘似的害羞呢?”倒是瞎阿姨先开口,亲切地叫我“阿东阿东”,还问长问短的,弄得我十分尴尬。
母亲告诉我,瞎阿姨是居委会干部。能说会道的,挺能干。她对我家的处境十分同情。前不久,造反派要揪斗父亲,是瞎阿姨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竟然把造反派挡了回去,使父亲免受一些皮肉之苦。为此,母亲深为感动,把她当作知己,又如姐妹一般,无话不说。说到伤心之处,母亲一串串泪珠总是带着辛酸。那是她听到了许多关于知青的悲惨故事后,为我在农场痛苦的命运担忧。瞎阿姨劝我母亲想开一点,劝着劝着,有时她也跟着我母亲流下了泪水。
瞎阿姨是单身女人,一生没有嫁人,也没有领养孩子。但她说,特别喜欢男孩子。那段时间,瞎阿姨几乎天天来我家,母亲总是热情招待,还把我刚从苏北带回来的两斤花生米送给了她。这又大又饱满的花生米,是苏北的土特产,在常熟很少见。瞎阿姨非常喜欢,还夸我很孝顺。她连续几天熬夜,特地为我织了两件厚厚的毛衣。说是苏北的冬天要比苏南冷得多,让我注意保暖。她虽然是个瞎子,但她织毛衣的花纹却很好看。我记得一件织的是菱形花的,另一件织的是元宝针,还配上又大又白的钮扣,很别致。穿在身上感觉暖和、柔软,挺大方的。说实在的,我心里挺感激她的。
这年春节探亲后,我没有按时回农场。呆在家里,整天无所事事。母亲心疼我,怕我在农场垦荒累坏了身体,要我在家休养一段时间。瞎阿姨对母亲说,她喜欢我,要正式认我当外甥,以假成真。对她的生活也算有个照应。母亲感到有些意外,却又不好推辞,便答应了。瞎阿姨送给母亲一个见面礼:她要把我从农场抽调回常熟城里。这是母亲做梦也没想到的。这对我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我激动了好几个夜晚,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可我又想,把我调回城里,能行吗?再说我父亲还被关押在“学习班”里挨批斗,在当时像我这种身份的人,是劳动改造的重点,在人前只能唯唯诺诺,不敢有半句怨言,想回城真是难上加难。母亲说,别小看瞎阿姨,她的能耐可大呢!据说她和街道办事处的人很熟,还能和县里上山下乡办公室的邓主任说上话呢!邓主任虽然官不大,可他是个实权人物。根据当时我家的处境,能攀上瞎阿姨这门亲戚算是十分荣幸了。
瞎阿姨好长时间没有来我家了,家里好像冷清了不少。我就跑到她家里去看看她。她似乎早已料到我要来的,她说:“关于你回城的事,邓主任已经知道了,不能着急,慢慢来。”我听了这句话,像喝了蜜糖似的,心里甜滋滋的。谢了瞎阿姨,转身想走,却被瞎阿姨叫住了:“你不想陪阿姨说说话?”“嗯,下次吧。”我说。“好吧,路上慢点走。”她挺关心我的。一路上,我连蹦带跳地回到家里,急忙把这好消息告诉母亲。母亲愁苦的脸上不时展开笑容。
瞎阿姨又来我家了。她一脸春风,我想定有喜事。母亲还留她在我家住了几天。她们经常一起说说笑笑,很开心。有时她们之间嘀嘀咕咕,说话声音很低,一直谈到深夜,我一点也听不清,我想这一定是在谈与我有关的事。
瞎阿姨告诉母亲,前一阵子,她为我回城的事在奔波,现在总算有眉目了。母亲想到我即将跳出苦海了,一阵激动,扭过脸去,悄悄地抹掉两滴眼泪。忽然母亲对我说:“怎么还不叫阿姨?”我叫阿姨时,感觉很顺口,不像从前那样别扭了。瞎阿姨笑着对我说:“邓主任很欣赏你的才华,让你写封信给他。”我知道邓主任是在考验我,不知瞎阿姨在邓主任面前是如何夸奖我的呢?当时我兴致很高,当场写信,信的内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是用毛笔写的,我把信交给瞎阿姨,由她转交给邓主任。
信寄出后,我心里忐忑不安,邓主任看了我的信会说些什么呢?我天天盼望瞎阿姨的消息。不久,瞎阿姨那边有回音了,邓主任看了我写的信,印象很深。说我回城的事基本已定,只是时间早晚罢了。我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母亲对瞎阿姨说:“我们应该当面谢谢邓主任呀!”瞎阿姨说:“现在时机不成熟,不要见面。”瞎阿姨建议我暂时不要急于回农场,免得苏北苏南的路上来回奔波,干脆在常熟城里等通知,如果能接到调令就不用回农场了。这正合我的心意。这段日子我最开心了,不用开河爬坡、不挑粪、不用冒着风雨突击插秧。我整天在家里看小说,练小提琴,有时陪瞎阿姨逛逛商店,身体一下子胖了许多,被海风吹黑了的脸,也已经开始泛白了。
三个月过去了,“四夏”农忙即将来临,我回城的事还没有实质性进展。母亲急了,我心里更急。一直呆在家里也不是滋味。当我想到农场老队长一天到晚板着脸,动不动就骂人的脾气,我心里就害怕。我在城里偷懒,哪一天我回到农场,老队长肯定会狠狠地批评,说不定还会把我当作典型,在知青大会上批斗呢!可瞎阿姨说:“阿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再等几天吧。再说你现在回农场,小杨也不同意呀!”“小杨是谁?”我问,我真有些弄糊涂了,怎么突然冒出个小杨来了呢?“是我为你介绍的女朋友,你不信问你妈。”瞎阿姨边说边笑,还真有点卖关子呢!母亲向我点了点头,算是有这么一回事。噢!我想起来了,莫非那几个晚上她与母亲窃窃私语,谈的就是这件事?瞎阿姨说:“小杨比你小两岁,是色织厂的女工,小杨母亲宋阿姨与邓主任是老同事,这次你调动的事,也有小杨的一份功劳呢!”能有个“城里妹妹”作为女朋友,我心里真高兴,可我担心,我家庭出身不好,人长得土里土气的,能配得上人家吗?我急着问她:“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我和小杨能见面吗?”瞎阿姨说:“暂时不要见面。当务之急是你回城的事,你能回城,什么事都好办了,不要急于谈恋爱。”我被她说得满脸通红。还好,她看不见我失态的样子。就这样,我在城里又被瞎阿姨留了下来。
瞎阿姨说,她一个人生活并不感到孤独。因为她家里有两个人跑得最勤,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小杨。对她来说是一种安慰,一种寄托。我想如果能在瞎阿姨家巧遇小杨也是一件令人惊喜的事。可偏偏不巧,有时我到瞎阿姨家,小杨刚走。有时我刚离阿姨家,小杨就来了。有一次,瞎阿姨无意中说起,她明天下午陪小杨去新华书店买书,那天下午我一个人悄悄地去了书店,把书架上的书翻来翻去,佯装买书,眼睛一直盯住大门口。小杨究竟长得什么模样,能和她说几句话吗?可整整等了半天,直至天黑书店关门,也没有见到她和小杨的踪影。难道瞎阿姨是和我开玩笑吗?仔细想想,我觉得我和邓主任、小杨之间的信息交流就像地下党似的,只有通过瞎阿姨才能单线联系,真是太神秘了。见小杨就这么难,那么见邓主任呢?还有回城那件事,我正走在一个渺茫不可知的方向,我不敢往深处想。
夏天即将过去,天气渐渐转凉了。不知什么原因,瞎阿姨来我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我总觉得她隐藏着一个女人难以启口的孤独。其实瞎阿姨也怪可怜的,瞎着眼,伸着手东摸西摸,佝偻着身子,走路跌跌撞撞的,生活难以自理,一朝失去了依傍,她的空虚落寞之感,将更甚于我母亲吧。我在城里吃闲饭的日子再也呆不下去了,心里堵得发慌。我准备悄然回苏北农场。临走前我还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瞒着瞎阿姨,直接写信给上山下乡办公室的邓主任,关于我调回城里的事问个明白。我把信投入邮筒后,感到一身轻松。究竟是与否,马上就能见分晓了。一个星期后,上山下乡办公室果然派人来了。那位负责人对我说:“你写的信我们收到了,关于解决知青问题,是今后的一种趋势。不过,我们办公室根本没有邓主任这个人,你是不是搞错了,还是受了别人的骗?”我呆在那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几乎是致命的。我没有立即告诉母亲,我怕她伤感,一时受不了刺激。我在她面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还勉强做出一丝微笑,但一滴泪水,却悄悄地从我的眼角里渗了出来……
回农场的前一天夜晚,我在整理行李时,无意中看到了瞎阿姨编织的两件毛衣。在这朴素的毛织物里,她编织着我终生难忘的故事,让我在最艰苦最无助的日子里度过了一段梦一般的美好时光。我最后一次去了瞎阿姨家。那晚她家停电。在黑暗中,给我的感觉是她比谁都寂寞。我对她不禁起了无限怜悯。我告诉她,上山下乡办公室已经来人了。她的手微微抖了一下,一切全明白了。“这么说来,邓主任、宋阿姨、小杨这些人都是你瞎编的?”我问她。她低着头不做声。我忽然想起曾经让她转交给邓主任的那封信,她说:“这封信我摆在脸盆里,然后放了水,让它浸烂后撕掉的。”我总算松了一口气。沉默片刻,彼此不交一语。可有谁能拨开这个女人心头的乌云呢? “不要问了,你走吧,是我对不起你。”她说话时噙着一眶泪水……
“你走吧,是我对不起你。”她说这句话,一转眼已经30多年了。可有谁带来她的下落呢?母亲去世也有10多年了,那些恩恩怨怨已经成为过去。瞎阿姨,我早已一点也不恨她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那些爱和恨、真与假,究竟有什么是永远的,又有什么是值得认真的呢?
责任编辑鲁书妮
——纪念上山下乡48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