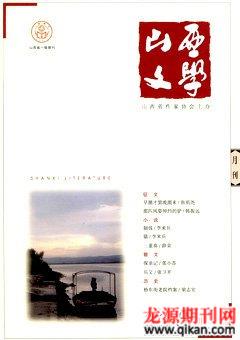岳父
张卫平
回去参加表弟的婚礼却意外地得到岳父病重的消息。
我正在母亲家里吃饭,妻眼圈红红地赶过来,我父亲病得厉害,你快过去吧!
我去了的时候家里一屋子的人。
岳父脸色惨白地躺在炕上。
岳母背过身子摸眼泪。大姨子小姨子小舅子眼圈红红地挤在岳父周围。
小姨子喊,爸,你看,谁看你来了?
听到喊声的岳父慢慢睁开眼,他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爸,他是谁啊?小姨子仍在喊。
岳父艰难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这——不——是——卫平——么?
全家人都高兴地笑起来,他还能认得卫平他还能认得卫平!
岳父有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年前不是还能下地行走么?怎么几天功夫就病成了这个样子?
岳父看着我,嘴一咧孩子似的哭起来。岳父的哭又引得儿女们一片啜泣。岳母说,这几天他老爱哭,谁来看他他就流泪。
看着流泪的岳父我不知该怎样安慰他老人家。
岳父曾经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啊!
岳父是代县陈家庄人。
我们那地方十年九旱,特别是陈家庄一带,更是处于缺水的半山坡上,遇到干旱年份,地里一片焦黄。为了讨生活,人们常常要走口外。走口外大致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西北方向,如呼市、包头,最远能到达外蒙古;一条是东北方向,如海拉尔、牙克石、大兴安岭等。五十年代初期,由于生活所迫,岳父只身来到遥远的大兴安岭。
那时的大兴安岭还是一片蛮荒之地。
年轻力壮的岳父扛工、打草、喂牲口……遇到什么就干什么,只要能填饱肚子管他什么苦活累活。
听妻子讲,那时草原的草特别长。
岳父每天给人打草。四周是望也望不到边的绿。站在草海中间,手持长镰刀,左右一划拉,身后便毯子般铺满了又绿又长的草。割完草,还要打了捆起了垛。起垛的时候,一人在下面,一人在上面,岳父身高力大,自然站在下面,抓住捆好的草,嗖地抛到半天中,上面的人伸手一按,草捆落在脚下。垛越起越高,岳父的草也越抛越高。起了垛的草像小山一般。舍得出力气的岳父每天都能在草地上立起好几座山。由于岳父干活实在不耍奸,每年都能揽到好多活。
大兴安岭建起林场后,岳父当了一名伐木工人。
伐木工里最辛苦的活莫过于装卸了。岳父那时正值盛年,凭着人高马大又吃苦耐劳,很快成了林场里一名很有名气的装卸工。
那是岳父人生中最火红的一段岁月。
十几个精壮的汉子赤着黑红的脊背站在巨松的两侧,一声号子,巨松落在汉子们的肩上,大伙喊着号子,把巨松装到准备出发的火车上。一根又一根,一年又一年,成千上万的原木就这样通过岳父他们的肩膀被发送到天南海北。
我见过岳父中年时期的一张照片。
那是怎样精壮的一个汉子啊,高大威猛的个头,棱角分明的脸型,粗壮结实的身材。你无论怎样想象,也无法把照片里的人与眼前躺在炕上病得一动不能动的岳父联系在一起。
晚年的岳父似乎非常留恋年轻时的那段岁月。
岳父喝点酒,或者遇到什么开心事的时候,常常会哼几段他们干活时的号子:
哈腰挂哎——
咳吆,咳吆。
往前走哎——
咳吆,咳吆。
大步走哎——
咳吆,咳吆。
岳父的舌头有些僵,喊出来的号子含混不清,只有仔细分辨才能听清号子的内容。岳父似乎想到了他年轻时英武的样子,满是皱纹的脸上裂出难得一见的笑意。
岳父当装卸工的时候,家里的人口也一天天多起来。那正是个崇尚多子多福的年头,先是四个大姨子,然后是妻子、小姨子、两个小舅子,再加上岳父的老父亲母亲,一家十几口人,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六十年代正是中国的困难时期。
岳父为了让一家人吃饱肚子,起早贪黑开荒种地。大兴安岭上是漫山遍野的荒坡。荒坡上长满了半人多高的茅草、荆棘。岳父干完林场的活,便拿上镰刀、镢头上了野外。把草割掉,再一镢头一镢头翻过地。东北的土地肥得流油。第一年种下去,茅草和庄户一般高。岳父只能一根一根把茅草薅掉。第二年茅草就少了。第三年荒地就成了熟地。岳父在自己开垦的荒地里种上大豆、玉米、山药蛋,特别是山药蛋,一块巴掌大的地能起十几麻袋,山药蛋又大又沙,成了一家填饱肚子的重要食物。
经历过六十年代的人都尝过挨饿的滋味。
每提起那段时光,妻子总是很骄傲地说,我们没挨过饿,我们吃得饱饱的。
那个时候能吃饱饭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
岳父家里有一张七十年代的照片,岳父岳母坐在中间,大姨子小姨子小舅子围坐在一边,妻子梳着两个小辫子噘着嘴站在后面。一家人穿着臃肿的棉衣棉裤。孩子们看了照片,直喊土!女儿说简直老土死了!土是土,但岳父一家的精气神还不错,妻子的两个脸蛋也吃得胖乎乎的。
不过,从照片上看岳父似乎老多了。
身材有些臃肿,脸上是密密麻麻的皱纹。五十多岁的人显得是那样的苍老和疲惫,与三四十岁的岳父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
由于苦大,岳父的身体越来越差。岳父已远不是当年那个能一肩扛起巨大原木的岳父了。
没过几年,岳父从一线上退下来,由一个威风凛凛的装卸工变成一个看门打更的守夜人。
也许劳累了几十年的岳父也真的该好好轻闲轻闲了。
只是不知道,这个一辈子靠力气吃饭的汉子,在自己体弱力衰的时候,内心会有一种怎样寂寞而又怅茫的心境。
往前走哎——
咳吆,咳吆。
大步走哎——
咳吆,咳吆。
岳父一辈子只会也只喜欢哼这一首歌。
这首歌在岳父心里哼了几十年。
也许在岳父那无数个打更的日子里,只有这首歌陪伴着他老人家度过了那一个又一个枯寂而又无聊的长夜。也许也只有这首歌才能让他老人家回忆起自己那段身强体壮红红火火的岁月。
岳父为人老实不爱说话,特别是由一个装卸工变成一个看门的守夜人后话似乎更少了。
有一天,体弱的小舅子病了,岳父只好请了假背着小舅子去了医院。岳父一点也没想到一场莫名其妙的灾祸正向自己袭来。
就在岳父离开林场的时候,岳父看守的林场被盗!
林场保险柜里几千元钱不翼而飞!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事,几千元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目!
岳父赶回林场时天已黑下来,不知就里的岳父看到敞开的大门一头闯了进去。
大门上、保险柜上、地上都留下岳父慌慌张张察看事故的痕迹!
面对满屋的手印脚印,岳父就是长一千张嘴也说不清啊!笨嘴拙舌又忠厚老实的岳父被关进了看守所!
天塌地陷!我们能想象到无依无靠的岳父一家是怎样的欲哭无泪愁肠百结!
岳父在看守所被关了多长时间,我记不清楚,我只记得妻子说,等案子查清楚,岳父从看守所出来时,头发全变白了!
岳父在里面的熬煎可想而知。
1997年岳父在阔别代县五十多年后回到故乡。
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岳父。
我和妻结婚的时候岳父没有回来。岳父在我的头脑中也一直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现在七十多岁的岳父突然回来,心里也不知是种什么滋
味,是喜悦,是期盼,是空落落的心里有了很踏实的感觉?是,又似乎都不是。我和妻去了火车站时,岳父他们已从火车上下来,岳父岳母身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包袱。妻喊声爸、妈跑了过去。父女母女们一通亲热。岳父看看冷落在一边的我,急忙说,这就是卫平吧?
妻子返回头瞪我一眼,还不叫爸?
还没等我喊出口,岳父已伸过手来。
岳父回到代县后就再没有回过东北,和我们住了一段时间后,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处房院。有了自己的小院子,岳父一天也闲不住。把地翻过,撒上粪,再细细地种上菠菜、韭菜、黄瓜、西红柿,夏天一到,岳父的小院子便葱郁出一片嫩绿。
这些活根本不够岳父干。种完菜,岳父还要去拾柴禾、挖树墩,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公路两旁留下很多废弃的树墩,岳父带一把锹,慢慢把树墩挖出来,然后想方设法把树墩拖回家。挖树墩不是个简单的活,树墩下面根根叉叉扎得很深,一个树墩往往要费好几天的功夫。把周围的土挑出来,用斧头砍断树墩下面的根根叉叉,树墩才肯挪出来。遇到大的树墩,岳父要挖一人深的土。公路旁边只露出岳父白白的头颅。一夏天,岳父能挖十好几个树墩。冬天的时候,岳父便在门前嘣嘣嘣砍那些树墩,岳父的窗台下很快会垛起几垛烧火的干木柴。
下了班、星期、节假日我常和妻子孩子们去岳父家。
岳母炒几个菜,我和岳父小饮几盅。我不能喝酒,几杯下肚脸便变红。岳父呢,半茶杯酒一点事也没有。岳母说岳父血压高,不能喝了!我们两个说些家常话,孩子们小,跑出来跑进去,追得鸡飞狗叫一片混乱。妻大呼小叫责骂孩子们,岳父总是说,孩子们顽皮点好孩子们顽皮点好。
前年我有幸被调到太原工作。
我走的前一天去和岳父岳母告别。
几年下来,岳父越来越老了。岳父背驼了,走路也拄起了拐杖。我和妻离开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岳父拄着拐杖蹒跚着送出大门外。我们走出老远,还能看见大门下默默站着的伛偻着脊背的岳父。
此后我每次回去总要去看看岳父。或许是年轻时用力过猛吧,岳父衰老的速度明显加快,似乎一次比一次厉害。年前回去,岳父连走路也成了问题,每迈一小步都非常困难。看着他用全身的力气迈那一小步,我心中不知有种怎样难受的滋味!儿女们都大了,日子好过了,正是享享清福的时候了,可怎么一下就老成这个样子了呢?岳父什么活也干不了了,每天只能从炕上挪到家门口,呆呆地坐在那里,看日起日落。
岳父还在流泪。四大姨子用毛巾揩去岳父眼角的泪。也许岳父知道自己现在这个样子意味着什么。
我给岳父点根烟递过去。
四大姨子喊,爸,卫平给你烟!
岳父手哆嗦着夹不住。
四大姨子夹住烟,让岳父一口一口地吸。
岳父抽得很香,眼角挂着泪花,嘴里喷出长长的烟。
往前走哎——
咳吆,咳吆。
大步走哎——
咳吆,咳吆。
看着被病痛折磨的岳父,我的头脑里似乎又出现了那个赤着黑红脊背、喊着号子、扛着原木大步往前走的岳父!
岳父还能站起来吗?
岳父还能健健康康地好起来吗?
但愿,但愿一切都能遂人愿!
责任编辑:白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