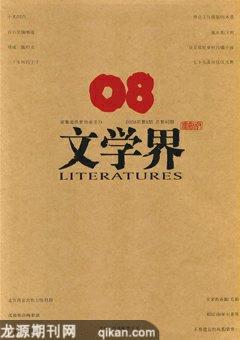小小的事,小小的我
我的老家在一个山弯里,分上下两村,相距不远,打个喷嚏或放个屁,都听得到。每天娃崽们赶着牛羊在村后会合,问今天到哪里放去?我说,去老禾坳若何?四癞子连连摇头:“去不得!去不得!昨天三公在那里碰见个老虫,尿都吓出来了。”我不以为然,问:
“是死的还是活的?”“当然是活的。”
“是活的怕个屌!早跑到云南了。”
“对,怕个屌!”大家附和着。
为防万一,我把狗唤到前面去。若狗不敢前行,往人群里钻,说明那虫还在,去不得!反之,放心好了。于是牛羊之声又沸扬起来,腥膻与泥土的气息,搅得空气变了味儿。
到了老禾坳,四癞子又不愿停了。他说,干脆再远点,到豹子岩去。我说,行,好久没去了。
豹子岩在老禾坳的前方,是荆棘柴草满布的石头山。山下有一片开阔的草地,是放牧的好场所。
深秋季节,大地一片穷黄,天空一片穷蓝。放牧中午不兴回家,饿了挖茅根吃。那根儿细嫩,慢慢咀嚼,生津解渴,越吃越想吃。我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说:大家听着,我介绍放牛的经验。每讲一条,你们各自向我奉献两茎茅根。
“要得,要得。”有人举起手来。
四癞子在土坎下撒尿,不情愿地答道:“那要看讲得对不对!”他提起裤子,尿液滴在手背上,用鼻子去嗅。
我说第一,牛绳不能系在腰上,牛下水时,人就不会出危险。于是我得了一把茅根;第二,抽打牛羊应用竹梢,痛而不伤筋骨,还是防蛇的好武器。于是我又得了一把茅根。
四癞子生妒了,他说:“你吹什么牛!我们来真格的,比赛打鸡公棒如何?”我应道:“比就比,谁怕你三根癞子毛!”
青妹打头阵,突然失手,棒儿打有我眼睛上。这可坏了,若瞎了日后怎么过呢?
“我服侍你。”青妹哭着说。
“哈宝!你不嫁人了?”
“就嫁给你吧。”声音羞涩,脸很红。
“不行!不行!还没出五服呢?”什么叫五服呢?听父亲讲,五服即五代,是近亲……
这时,夕阳只留下一方红头巾,挂在高高的树尖上了。青妹拉着我的手,一步一步往回走。
家乡的河不大,约20来米宽,水清澈见底;浅水处有跳石,仿佛历史跋涉时脱下的脚茧;古老的水车日夜不停地转……大自然在这里造不出干旱,却造出许多风湿病,使乡亲们在天气骤变的日子里——喊“痛”!
水不深,少有危险。
夏天里孩子们去打水仗。七公不许孙子去,他偷跑去了。老人追到河边,他掳着小“鸡鸡”喊:
“爷爷,爷爷,要咬我两粒牛睾子么?”
老人气得忘了身份,骂道:“狗杂种!”
麦子收割季节,女人们舞了一天连枷,浑身痒痒的,结队去河里洗身。“蛇脑壳”和二牛躲在河边树丛里偷看。
“女人的身子为何那么白呢?”蛇脑壳问。
“太阳晒得少呗。”二牛答。
“不对!天上的云为何越晒越白,没有太阳反而黑了呢?”
“天上是神仙住的地方,你管得着吗!”二牛是个急性子,脚一动,踩落一个石头,“咚”地掉进水里。女人们尖叫一声,慌乱一阵,辱骂起来……骂过了却依然嘻嘻哈哈,半藏半露地蹴在水里,怕人看见,又好像怕人看不见。
庵堂大都在山上,我家乡却有一座在山下,离村不远。时过境迁,不知何时何故,尼姑走了,菩萨走了,道士叔住进去,一个学校住进去。我去读书。
先生为我三次取“名”。头一次重复,村里已有那个名了;第二次与父名共一字,父亲说:“要不得,要不得!祖先灵牌有倒挂的么?”第三次先生翻开字典,半晌没有抬头……道士叔从窗外伸进脑袋:“我看别费那个劲了,他姓黄,‘维是他的辈份字,取‘一吧;万丈高楼从地起,哪个字能离开‘一呢?”先生频频颔首点头。
“黄维一”三字就这样小草般拱了出来,后来的岁月里,旱过、涝过,被不是牛羊的“牛羊”啃过,没死,又青了。
村里除先生外,道士叔算半个秀才,三十六卷经书能横直倒背,我们“啧啧”地连声称赞。他有个儿子是我的同学,我原以为他读书也一定不错,那天早读课先生命他背书,他站着一声不响。
“背!”先生催他。
“……”他还是一声不响。
先生火了:“你说,到底晓不晓得?”这时有个结巴的声音答曰:“晓……晓得……就是不告诉你听!”哄堂大笑,先生也窃笑了。道士叔在擦拭手中的菩萨,闻声说了一句:“木头。”——说谁呢?不清楚。
久旱无雨的夏天,村民们心急火燎,想求菩萨降下甘霖,法师自然是道士叔。三天一过,道士叔眼红声嘶地喊我:“来,小侄,为叔诵上一段。”
我说:“行吗?”他说:“行,谁说不行?碰到‘生字跳过去就是了。”
我惊愕得朝他一望,他却伏案睡觉了。天气热,我穿着短裤,忽然小“麻雀”被虫子咬了一口,痒痒的,我伸手搔了搔,把他摇醒。
“叔,搔过‘麻雀的手可以翻经书么?”
“可以。”
“菩萨不降罪吗?”
“嗨,哪来的事,菩萨是木头。”事后他悟知说漏了嘴,嘱我莫外传,为叔留口饭吃。我惨然想:愚味者迷信,迷信者未必都愚昧。
他祈祷了半辈子,最终还是死了。有人说是病死的,有人说是饿死的,没细究。那年头,毛主席还有半年没吃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