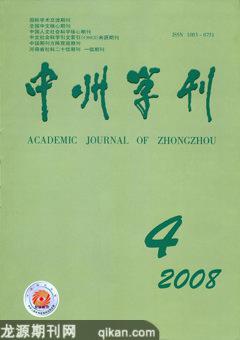论陈亮的文学观
摘要:陈亮的文学观是以传统的“文以载道”观为基点,进而落实为“明道致用”。他标举“意与理胜”这一文论核心,若兼艺术形式而言,就是他所主张的“理得而辞顺”,具体表现为诗、词、文等不同文学体裁均可通用的“立意精稳,造语平熟”。陈亮具有诗、词、文通体看待的文学观念,并由此决定了他独特的词学观的形成。在艺术风格上,他则是喜爱阳刚豪放,同时亦不偏废清丽婉约之作。
关键词:陈亮;文学观;艺术风格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4—0211—03
收稿日期:2008—03—21
作者简介:李小山,男,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陈亮,世称龙川先生,有《龙川文集》行世,并以现存的74阕龙川词奠定了他在词史上的地位。陈亮作为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其作品是建立事功的壮志和爱国激情的抒发,是南宋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的产物,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但学界目前对这位作家的文学观念、审美心理很少深入论述。我们通过对陈亮文学观念的全面梳理,并结合他在创作中体现出的审美旨趣和实际倾向,可以发现其文学观是有着丰富内涵且独具特色的。整体来看,陈亮的文学观仍是以传统的“文以载道”观为基点,但是在他这里,“文以载道”已经落实为具有强烈事功精神和鲜明时代特点的“明道致用”。由此,陈亮标举“意与理胜”这一文论核心,若兼艺术形式而言,就是他所主张的“理得而辞顺”,实际表现为诗、词、文等不同文学体裁均可通用的“立意精稳,造语平熟”,并自然延伸出诗、词、文通体看待的观念特点,也因而决定了他独特的词学观的形成。在艺术风格上,他则是喜爱阳刚豪放,同时亦不偏废清丽婉约之作。陈亮作品的风格面貌与其文学观念、审美心理是气息相通的,是其文学观在创作上的实践和落实。因此,探讨和把握其文学观,对我们深入理解陈亮作品、正确评价陈亮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提倡“明道致用”
陈亮以豪杰自居,以事功自任,耻与文士为伍,故其论文斥去浮华,不尚修饰,大要以明道致用为本。六经是他心中的仪则,其论《书》曰:“概于道者百篇,而垂万世之训,其文理密察,本末具举”,论《诗》曰:“将使天下复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他评欧阳修的文章是“根乎仁义,达之政理,盖所以翼六经而载之万世也”①。他强调“古人之于文也,犹其为仕也,仕将以行其道也,文将以载其道也”。概而言之,文以载道,教化垂训,本是儒家文论的老调,陈亮于此并无创新。但陈亮的“道”是祛除了本体论层面上的玄思冥想,直接与日常事物合一,并要求表现在人间的事功上的,是用事功标准来进行衡量,因而他的“道”就具有了强烈的事功精神和鲜明的时代特点。“他没有将道的实际内涵狭隘地理解为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性命,而是将时代内容、现实生活以及作家本人的思想情感都包括在内的。”②所以陈亮特别指出:“吾以谓文非铅椠也,必有处事之才。”这显然与当时社会上弥漫的空谈性理的习气相对。
总之,陈亮认为创作应以“载其道”为目的,但“其道”要求能够“平施于日用之间”、“达之政理”、并经由事功标准的检验方可,正因为此,“文以载道”在其实质内涵上就发展落实为具有强烈事功精神和鲜明时代特点的“明道致用”了。具体到陈亮所处的时代和他的个人主张而言,“为文”就是要为南宋的社会现实与政治现实服务;“政理”就是南宋的民族恢复和民族中兴大计;“日用之间”就是要唤醒对此的明确认
识并付诸行动、建立事功,这也就是陈亮一生无论做人、论学还是发为文章都念兹在兹、九死而无悔的“道”。
二、标举“意与理胜”
与“明道致用”的目的相适应,“意”是陈亮文论中的核心观念和首要标准。他在评诗、赋时同样以“意”为首要标准,其赞语或曰“立意精稳”,或曰“意广而调高”,而《书作法论后》中的一句话尤其值得注意,它可以用作陈亮文学观点的总结语,即“意与理胜”。宋代文人的头巾气重,好发议论,重“意”、重“理”是普遍现象,陈亮也不例外。但是陈亮作为南宋卓异的思想家和军事谋略家,永康事功学派的创始人,其“意”特高、用“意”极深,其文学观念、文学创作所主之“意”自然与一般文人不同,有必要详述之。
我们结合陈亮作品中的实际创作倾向并分析其人格心理可知,他文论中所主之“意”偏重在认识层面上。陈亮的古文创作无疑是以“意”为主的,这一点早成学界共识,故不必赘言。本文在此则以词作为例,采用文、词对读的方法,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陈亮以意为主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特色。陈亮在词中长于寓“意”和运“意”,其“意”仍是重于认识层面上。比如其代表作《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之末句“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实是全词重心所在,如果把这句话理解为“胡运如赫日当中”而当做是对南宋小朝廷的反讽之语看,放在结尾显然与全词的昂扬气象不和谐,与作词以壮行色的特定场景也不吻合。故学人大都直接把它理解为“南宋国运如赫日当中而胡运衰竭”,但这样做不免有失表面化和简单化了,因为这与当时宋金两国的实际历史状况不符。此词作于淳熙十二年(1185),南宋朝野风气萎靡,唯求苟安。而此时的金朝,社会经济等有着较为良好的发展,史家对此有“小尧舜”之称。在这种形势下,要想北伐金国,谈何容易?陈亮对此当心知肚明。故一般认为,所谓“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不过是句良好祝愿而已,等同于喊口号,当时就有宋儒“以夸大少之”,甚至到现在还有学人专门撰文反驳说“南宋的国运是赫日当中吗”?之所以造成这种纷争,正是由于没能深入理解陈亮其人其文及其文学观念上所特有的“意”。
《龙川文集》中陈亮还说了一句与“赫日当中”相类似的话,《又乙巳秋书》中曰:“赫日当空,处处光明。闭眼之人,开眼即是,岂举世皆盲,便不可与共此光明乎?……亮以为:后世英雄豪杰之尤者,眼光如黑漆……及其开眼运用,无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赖以撑拄,人物赖以生育。”此文与《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作于同年,词中“赫日当中”与文中“赫日当空”、“赫日之光明”具有内在意义的共通性,可以互解互证。由此可以这样理解,即虽然现状看起来是宋弱金强,恢复中原非其时,但这只不过是闭眼者、盲者之所见,而英雄豪杰之尤者(指章德茂,亦以自指),眼如点漆,目光如炬,开眼看来,则我宋确有可胜之道,我宋必有可胜之理、可胜之事,此昭昭在人眼目,如同赫日当中,无往而非赫日之光明也。陈亮在这一时期曾以政论家和军事家的眼光分析策划,指出“揆之天变,验之人事”,赵宋如能励志奋发,战略性地不断扰乱敌国、发展自己,则只需有计划有步骤地准备上五年,然后即可北伐金国,恢复中原故地,绝不应该只图自保、只求苟安而已。
淳熙十五年二月,陈亮到金陵、京口,观察山川形势,并作《念奴娇·登多景楼》一阙,词云:“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这里的“意”,是山川形势在军事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上呈现出的“意”,是作为政论家、军事谋略家的陈亮眼中所见之“意”,它是客观的,是经过理性分析而得来的,无疑也是偏重于认识层面的。于是陈亮下面就在词中摆出了自己对山川形势所会的“意”,即“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陈亮的古文名篇《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云:“故尝一到京口、建业,登高四望,深识天地设险之意,而古今之论为未尽也。……京口连冈三面,而大江横陈,江傍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这里所谓虎之出穴,明指此天地设险之“意”,在南宋方面来讲,是宜于采取攻势而非守势的。所以陈亮大声疾呼:“江南之不必忧,和议之不必守,虏人之不足畏,而书生之论不足凭也。”我们把词和文对读,则陈亮所主之“意”昭然若揭。陈亮的这类作品中当然有着浓郁的英雄忧世的情感成分,但其振憾人心的艺术美感和艺术力量却主要是来自于“意与理胜”,来自于他既具有英雄特质又具有思想家特质的理性认知所表现出的高度、深度与穿透力度。由此可见,陈亮文论所主之“意”的特点是偏重于理性认识层面而言的。
三、主张“理得辞顺”
就文学形式而言,陈亮不主张在文字、技巧上多下工夫,只要造语平熟、平正和顺,达到某种文学样式在形式上的基本要求即可。对于古文,陈亮认为在形式上只要做到“布置有统,记载有法……一般说去”就够了。对于诗词赋等韵文,他认为在形式上能做到有节奏、抑扬顿挫也就够了。为文的目的是要达“意”、达“理”,故“理得辞顺”成了陈亮对文学内容与形式风格之间关系的辩证认识。他说:“大手之文,不为诡异之体而自然宏富,不为险怪之辞而自然典丽,奇寓于纯粹之中,巧藏于和易之内。不善学文者,不求高于理与意,而务求于文采辞句之间,则亦陋矣。”他同意杜牧的看法:“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也对黄山谷所言“好作奇语,自是文章一病,但当以理为主”极为认同。陈亮明确表示:“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③由于认为依程式作文即可,不必刻意追求形式技巧上的变化,要在于达意、达理,因此有学人认为后世八股文风即可溯源于陈亮。但陈亮强调作品内容上“意”和“理”的重要性,其实也并不否定“好语言”、否定“奇”和“巧”,而是说要对形式技巧喧宾夺主的可能性保持高度警惕,不能因为务求于文采辞句而妨害达意、达理。这种文学观念无疑是比较保守的,但是若能做到将“好语言”“自然”地熔铸于宏富、典丽的风格之中,将“奇”、“巧”化于纯粹、和易的行文之内,那当然是陈亮非常欣赏的。
四、偏爱豪放风格
陈亮是一个心胸开阔、豁达大度、兼收并蓄的人,故他对于艺术风格和形式,也持较为兼容的态度。就风格而言,陈亮对纡余、妍丽、清秀、精绝之作能够欣赏;但是英雄豪杰的人格特质决定了他更为欣赏的是阳刚之气、豪放之风、劲健之美。他对杜氏兄弟诗赋的评价就明白地显示了这一点。陈亮评赏杜伯高的赋“如奔风逸足”、“笔力如川之方至,无使楚汉专美于前”,称奖杜叔高的诗“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气”,而评价杜仲高的词则只是“发春妍以辉映于其间”,并最后总结说“此非独一门之盛,盖亦可谓一时之豪矣”④。可见,陈亮虽对清丽婉约的文风也颇能够赏爱,但其对豪放风格的偏爱和推重则是无疑的。
陈亮自言平生不能诗,其集中的诗歌仅4首,或许是为了藏拙。他对诗人和诗作的评论之语数量很少,也不甚经心。他唯独倾心于李白,作《谪仙歌》并序,序言:“寥寥数百年间,扬鞭独步,吾所敬起慕者,太白一人而已。”同时,他也有意仿效太白豪放诗风写道:“仰天高声叫李白,星边不见白应声。又疑白星是酒星,银河酿酒天上倾。奈无两翅飞见白,王母池边任解醒。”又曰:“我今去取昆山玉,将白仪形好雕琢。四方上下常相随,江东渭北休兴思。会须乞我乾坤造化儿,使我笔下光焰万丈长虹飞。”可知陈亮最为心仪的是飞动的气势、宏大的力量和豪放的风格。他自己的创作也明白地显示了这一特点,只是他的豪放,兼有思想家的认识底蕴和英雄豪杰的人格特质。陈亮自许“人中之龙,文中之虎”,他的传世名篇中,无论是诗文还是词,最为人所瞩目、为人所称道的无一不是精警奇肆、气势雄放之作,被誉为“可做中兴露布读”。他本人也自豪地宣称:“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则亮差有一日之长。”⑤
五、诗词文通体看待
陈亮文学观念的另一大特点是诗词文通体看待。由于其诗作太少,故我们可以通过对陈亮的词学观点的考察来进行说明。陈亮的词学观在两宋文人中颇具特色,是其文学观的自然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在陈亮看来,词这一艺术体裁,除了形式上的要求以外,并不具有足以与其他文学体裁区别开来的特质,即写词除了要遵守词体艺术在形式上的基本要求(词体的节奏、声韵、句式)之外,就不应该再做其他任何要求了。因此,可以用词来表达诗、古文里所能表达的一切东西,诸如情感、志意、逻辑推理等。反过来说,完全可以用一般文章的写法进行词的创作,只是要符合词体艺术的形式外壳。事实上,在陈亮零星的文学评论中,他也经常会把诗、词、文混起来谈,这在本文前面所举的他评论杜氏兄弟作品的例子中已有明白显示。另外陈亮在《桑泽卿诗集序》中所说:“予平生不能诗,亦莫能识其浅深高下。然尝闻韩退之之论文曰:‘纡余为妍,卓荦为杰。黄鲁直论长短句,以为‘抑扬顿挫,能动摇人心。合是二者,于诗其庶几乎,至于立意精稳,造语平熟,始不刺人眼目,自余皆不足以言诗也。”这里主要从形式上界定三者的区别,正说明陈亮认为诗、词、文在本质上是共通的,而其所谓立意精,造语平,不刺人眼目,也实在是可以通用于三者的。套用陈亮的话,就是他的词学观、诗学观、古文观是“直上直下,一个头颅做成”⑥。
陈亮还有直接论他自己作词的一段话:“闲居无用心处,却欲为一世故旧朋友作近拍词三十阕,以创见于后来。本之以方言俚语,杂之以街谭巷歌,抟搦义理,劫剥经传,而卒归之曲子之律,可以奉百世豪英一笑。”⑦由此可知,无论是方言俚语、街谭巷歌,还是义理经传,陈亮都认为可以毫不避忌地用为作词的材料,只是最后要“归之曲子之律”。从中亦可看出陈亮在对词的艺术形式、娱乐功能有一定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是将诗词文通体看待的,认为它们之间并没有天然的鸿沟,也不存在严格的界限。
由于陈亮的文学观一反“词为艳科”、“词别是一家”的传统看法,而是将诗词文通体看待,直言作词就是要陈“经济之怀”,公开宣称“抟搦义理,劫剥经传”,这就比苏轼、辛弃疾等以诗为词、以赋为词之类的做法走得更远,更不受传统词论的束缚,创变意识也更为强烈,这自然是词史上的离经叛道,堪称词史上的“大变”,极大地改变了词的面貌、体格、筋理,但同时也给后人在研究陈亮词时采用文、词对读,以文证词的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至于这一改变是好是坏,是利大还是弊大,恐怕是一个可以长久争论下去的话题。本文在此试图说明的是陈亮诗词文通体看待的文学观念,并认为这一观念特点值得我们重视,它可以说是陈亮独特词风和词学观点形成的重要内因。
总之,陈亮的文学观既是首尾一贯、合乎逻辑的统一整体,同时又是具备了多方面的内涵与特点的。陈亮的文学观始终贯穿着这位南宋永康事功学派创始人的事功追求和事功精神,是事功精神在文学上的显示和体现。在今天看来,这种文学观不免有些忽略文学情感性的特质和形式美感,对文学持有过分功利化的倾向,但陈亮正所谓不讳言功利者,而他自己的作品正是对其所持有的文学观念的忠实实践。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陈亮:《陈亮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245、287、327、339、349、389页。②董平:《陈亮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58页。
责任编辑:一鸣中州学刊2008年第4期试论李清照词的意境创造2008年7月中 州 学 刊July,2008
第4期(总第166期)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No.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