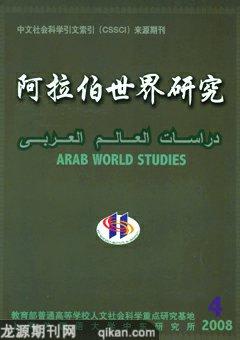后现代视野中的阿拉伯—伊斯兰传统
摘要:后现代仍然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只不过是批判性、颠覆性的那一部分。而现代性是根植于西方基督教传统的一种业已意识形态化了的并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渗透到世界各地的观念形态。本文认为,阿拉伯-伊斯兰传统虽然日益受到西方现代性的逼仄,但却仍然是独立于西方现代性之外的、可为思考西方现代性问题提供借鉴的一种文化资源。
关 键 词:后现代;现代性;阿拉伯-伊斯兰传统
作者简介:周传斌,博士,宁夏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宁夏银川750002)。
文章编号:1673-5161(2008)04-0059-08中图分类号:G371文献标识码:A
一、后现代:现代性之反思
要讨论“后现代”,就必须先讨论“现代性”。“modernity(现代性)”一词在西方学者的用法中有三种含义,分别为“时期”(period)、“特性”(quality)和“经验”(experience)。与“现代性”相联系的有一系列概念,包括“现代”、“现代主义”、“现代化”和“后现代”等。学者谢立中曾讨论了这些词义间的联系和差别(如下表)[1]25-32:

上表说明,与“现代性”有关的这些词汇都跟一种历史分期模式有关,即“现代/前现代”的对立。在欧洲中世纪,对“时间”的理解是由神学提供的,“时间”被看作人类生命短暂性的明证,是对于死亡和死后生活的一种永恒提示。同时,基督教末世论也提供了一种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的流逝着的时间性意识,这种“不可重复性时间”的感觉是现代性得以产生的土壤。在文艺复兴早期,已经出现了关于欧洲历史的三时代分期法: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且这三个时代被转换为价值判断:“古典时代和灿烂的光明联系在一起,中世纪成为浑如长夜、湮没无闻的‘黑暗时代,现代则被想像为从黑暗中脱身而出的时代,一个觉醒与‘复兴、预示着光明未来的时代”[2]25。这样,现代性就与发展、进化等观念联系起来,成为影响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思想意识。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指出:“‘现代主要指的是‘新,更重要的是,它指的是‘求新意志——基与对传统的彻底批判来进行革新和提高的计划,以及以一种较过去更严格更有效的方式来满足审美需求的雄心。”[2]而且,有两种彼此冲突却又相互依存的现代性:一种从社会上讲是进步的、理性的、竞争的、技术的;另一种从文化上讲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它致力于对前一种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观念进行非神秘化。
其实,现代性问题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其所具有的“现代/前现代”(主要是中世纪)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二是其中隐含着的以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调的进步、发展的观念。这两种观念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常识,但其中却蕴涵着内在的矛盾和缺陷。
首先,“现代/前现代”的二元对立提供了反传统的依据,似乎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要“反传统”。但实际上就连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本身也还是“传统的”、基督教欧洲的思维模式,并无任何创新之处。从表面上看,现代性是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的反传统、反宗教开始的,现代性与基督教之间的分裂似乎是彻底的。但当代许多学者已经看出,“现代”的很多杰出的思想家,其思想无论如何都必须被放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才能被加以理解,无论如何离经叛道,他们都仍然代表着这个传统的延续,即使如马克思主义这样激进的无神论也是如此。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哈贝马斯指出:“上帝死了,但在他死后他的位置仍在。人类想像中上帝和诸神的所在,在这些假想消退之后,仍是一个阙如的空间。无神论最终的确理解到,对这一空间的深层测度勾勒了一个未来自由王国的蓝图。”[3]73现代性与基督教传统的这种内在联系,一再地被揭示出来,以至于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所谓现代性问题,是否也具有其基督教的根源?在现代性最核心的“现代/前现代”二元对立问题上,正是鲜明地体现了基督教末世论的影响。《新约·启示录》为基督教提供了世界最终的结局,“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与撒旦的直接对立与斗争提供了二元论式的思路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二元论,无论其是否具有摩尼教或诺斯替教(Gnosticism)[注:诺斯替教是古代中东、地中海一带流传的一系列秘传宗教运动,对基督教有很大影响。其主旨在于认为只有获得“诺斯”(Gnosis),意为“秘传知识”或“灵知”,才能获得拯救。刘小枫主张把Gnosticism译为“灵知主义”,因为这里的“诺斯”是指一种神秘的、属灵的救恩特殊知识。在伊斯兰教里,“诺斯”可对应于阿拉伯语的“伊尔凡”(‘irfān)或“马厄里凡”(ma‘rīfah),本意是“知识、知道、知晓”,作为一个苏非术语则专指那种神秘的知识。关于诺斯替宗教,可参见[美]汉斯·约纳斯著、张新樟译:《诺斯替宗教:异乡神的信息与基督教的开端》,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的根源,都已经成为基督教世界观最核心的部分之一,并为从十字军东征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从冷战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供了理论支撑。所以,现代性问题本质上是“基督教的”,是基督教传统自身延续(无论发生了怎样的变异)的一种表现形式。
其次,关于社会发展、“进化”的观念为人类社会虚构了一个进化论式的演进史,并打着“科学”的招牌使自己合法化。如果说生物进化论是一种科学观点,将其援引到社会历史领域而诞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是一种伪科学。这种进化观念自启蒙时代以来也是深入人心,但同样具有很大的虚假性,对现代性的批判很多都集中在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泛滥上,就是一个证明。科学主义与工具理性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膨胀,即认为人类可以仅仅依靠自身逐步解决所有的问题,并因此盲目乐观地追求一种普遍主义或意识形态神话,“所有现代规划都以一种关于整个历史的终极目的论幻想为前提”,“现代性所有主要的‘解放叙事本质都是基督教范式的变种”[2]294。更有甚者,这种“进化论”图示还不自觉地为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适者生存”的理论支持,为近几百年来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倾轧提供了“正当的”理由。
“现代性”是有“问题”的,这是“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得以诞生的前提。如果现代性追求的是宏大叙事(grands récits)、全球化、同质化等类似的前景,那么,后现代刚好追求对这些命题的反叛。赵景来认为,后现代性能够近似地被概括为如下的主张:没有可用宏大叙事法描述的历史;没有一种话语有前后一贯的意义;没有作为表象的知识;不存在具有普遍逻辑和客观真理的科学;剩下的只是语言游戏自由地在权力关系网中游荡,暴露出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依赖。后现代性强调的是非决定论而不是决定论,是多样性而不是统一性,是差异性而不是综合性,是复杂而不是简单。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源自对工具理性及其恶果(集权统治、核恐怖和生态恶化)的批判。它要否定的不是现代性的存在,而是现代性的霸权;不是现代性的优点,而是现代性的局限。它欣赏现代性给人们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进步,同时对现代性的负面影响深恶痛绝。后现代性提出的问题是:能否有效地汲取现代性的优点又有效地避免现代性的弊端?[4]但后现代并非“现代之后”的又一个新阶段,它仍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后现代性在批判与颠覆的同时,似乎没有建设什么,也未能提供现代性的替代品。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仍然面临的窘境。但既然现代性是源自西方的、基督教传统的,那么,在这个传统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不同的文化传统?其他传统是否有可能提供反思并超越西方现代性问题的思路和范式?
二、陷入西方现代性泥沼的当代伊斯兰世界
人类生活于同一个宇宙中,但对这个宇宙及人类命运的解释却各不相同,这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17、18世纪以后,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改变了以往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方式。欧洲历史从上帝的创造和拯救史变为进化论的历史,表现在历史分期上,就是划分古代(前基督教的希腊和罗马)、中世纪(基督教时代)、现代等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且想当然地认为现在优于过去,历史指向进步。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这一有重大缺陷的启蒙历史模式逐渐被推广到全球,几乎为所有的国家和民族所接受。
在整个中世纪,伊斯兰世界一直遏制着基督教的欧洲,1492年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和标志,也可以说是西方“现代性”之全球扩张的开始。1492年之前,“在地中海的西端,东方借助穆斯林之手,保持了对西方的优势。”[5]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穆斯林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个政权格拉纳达陷落;二是西班牙航海家“发现”了新大陆。此后,一个漫长的殖民主义时代开始了。对欧洲来说,是开始了一个“辉煌的现代”;对于亚洲、非洲和美洲来说,则是堕入了殖民主义的黑暗深渊。伊斯兰世界被迫进入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现代”。从那时起,伊斯兰世界就不仅处在政治上的混乱无序之中,而且在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之下,自身传统被肢解,各种思潮纷起且各有其支持者和反对者。这一混乱局面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
有学者提出了“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概念,并以之作为伊斯兰世界“现代化”和“进步”的标志,19世纪首批接受西方教育的穆斯林知识分子是西化思想的先驱。埃及的塔哈塔维(Rifa‘ah Rafi al-Tahtawī,1801~1873)、突尼斯的哈伊尔丁(Khayr al-Dīn,1810~1889)都因为在巴黎留学而主张接受西方式的社会改革。19世纪伊斯兰世界最著名的思想家哲马鲁丁·阿富汗尼(Jamāl al-Dīn al-Afghanī,1839~1897)站在穆斯林的立场呼吁穆斯林内部的团结,主张塑造国家观念,提倡泛伊斯兰主义,以对抗殖民主义的压榨。他的弟子穆罕默德·阿卜杜(Muhammad ‘Abd,1849~1905)作为“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试图弥补传统伊斯兰势力与西化势力之间的裂痕,认为伊斯兰教具备变化和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应该把欧洲文明融进伊斯兰教的基本思想中,使伊斯兰教适应现代文明。他的思想奠定了此后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基本论调,即调和伊斯兰传统与西方现代性。与他的老师阿富汗尼相比,他是从泛伊斯兰主义走到了民族主义。他开创的所谓“伊斯兰现代主义”其实是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一潮流席卷伊斯兰世界,但其本质上却只是西方现代性之全球扩张中的一个小小的支流而已。我们发现“现代”伊斯兰世界实际上包括两种完全相反却又本质上相互联系的思潮和运动:一种是上述的“西化”或西方现代性之传播的浪潮,一种则是西方刺激下的回归传统的浪潮。“西化”即完全接受西方启蒙主义以来的现代性思想体系,追求政治上的世俗化、经济上的工业化、传统和宗教的衰落以及世俗文化的兴起。“回归传统”或“复兴”的字眼则标志着完全相反的取向。但这种“回归”已不仅也不能是复古,而只是在复古旗帜下与舶来的西方价值观的对抗,且这两种倾向相伴而生。
到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回归传统的思潮在伊斯兰世界已经成为主流思潮或主流的反对派思潮,具有极强的活力和能量,在世界各地产成了广泛影响,并可以进一步分为激进、温和、极端等不同的派别和表现形式。但不容否认的是,即使是最激进的“基地组织”和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也都不能摆脱西方现代性对他们的制约和影响。那么,就有这样的问题:在西方现代性的全球逼仄下,还有没有独立的伊斯兰传统?伊斯兰世界的“回归传统”有没有可以回归的指向?还是仅仅是一种虚幻的“乌托邦”之梦?
三、重拾超越西方现代性的伊斯兰传统
何为“传统”?何为“伊斯兰传统”?在英文中,穆斯林把阿拉伯语的“逊乃(Sunnah,即圣行)”译为“tradition”。因此,所谓伊斯兰传统,不是汉语的“传统”[注:在汉语语境里,“传统”二字应做如下理解:根据《说文解字》等的注释,“传”字与“遽”字互训,“皆传车驿马之名”,蕴涵一驿站传一驿站的意思,引申为传授,唐《经典释文》说:“传者,相传继续也”。“统”的本义是茧的头绪,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众丝皆得其首,是为统”。“传统”一词取“传”的相传继续和“统”的世代相承某种根本性的东西之意。]这两个字和英文的“tradition”这个词能够完全加以表达的,它必须要回到伊斯兰语境中,回到“逊乃(Sunnah)”中。阿拉伯语的“逊乃(Sunnah)”一词,其本意是“道路”,专指先知穆罕默德所表率的一种生活方式,中国穆斯林称之为“圣行”。所谓伊斯兰传统,应该是独立于西方现代性之外的、没有受到现代性困扰的、并有自己绵延不绝的沿革史的一种独特的文明传统。
当代最富盛名的穆斯林哲学家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博士(Dr. Seyyed Hossein Nasr,1933~)在反思“传统”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思路。纳斯尔教授在哲学观上秉承“传统主义学派”(Traditionalist School)的观点,该学派又以“永恒哲学”(Perennial Philosophy)、“永恒主义”(Perennialism)著称,认为各大宗教传统都可上溯到同一个本原,即“永恒智慧”或“神授智慧”,而现代西方则恰恰中断了其与这一神圣源头的联系。纳斯尔认为,永恒智慧存在于各大传统之中,通过我们直观到的不同的形象(如使者、先知、化身、圣子或者其他传达者)启示或者显现给人类,这一“永恒智慧”,在西方传统中就是拉丁文的sophia perennis,在印度传统中就是梵文的sanatana dharma(恒法),在伊斯兰传统中则是阿拉伯文的al-Hikmah al-khālidah(永恒智慧)。[6]67 因此,纳斯尔所代表的传统主义学派强调知识的神圣性,认为“传统”与“现代”的区别不是时空范畴内的“先后”关系,而是在同超验、永恒、神圣之域的关系上的“圣俗”关系。这样,传统主义学派已经进入了社会批评领域,对西方现代性的“进步”、“进化”等观念提供了有价值的反思。
根据纳斯尔博士提供的思路,可以进一步追溯伊斯兰传统与欧洲传统之间的关系互动。一般认为,欧洲文明有两大源头,称为“两希文明”(Hebrew/Hellene),即希伯来的宗教精神(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和古希腊文明的理性、民主精神。如果加以类比的话,我们很容易看到伊斯兰传统也与这两大文明息息相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同属于闪米特族系,从语言、血统、宗教来看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况且伊斯兰教本身就认为所谓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传统实际上就是同一个一神教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亚伯拉罕宗教”(Abrahamic Religions)。至于古希腊文明,则在后期已经将其中心转移到埃及的亚历山大以及叙利亚、伊拉克一带的某些城市。伊斯兰兴起后,到阿拔斯王朝前期,大量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文献已经被悉数译为阿拉伯语,阿拉伯逍遥学派(Peripateticism,阿拉伯语mashshā ī)[注:泛指那些受古希腊哲学影响的伊斯兰哲学家,包括伊斯兰东方(阿拔斯王朝)的铿迪、法拉比、伊本·西拿、塞法兄弟会,以及伊斯兰西方(安达鲁斯)的伊本·巴哲、伊本·图非利和伊本·鲁世德等著名的哲学家和流派。]成为古希腊遗产的最重要的承继者和阐释者。经过穆斯林学者的翻译、整理和注疏,古希腊的遗产以两种方式得以留存:一是通过翻译再次反馈到欧洲,尤其是以拉丁语名字阿维森纳著称的穆斯林哲学家伊本·西拿[注:Ibn Sina, 全名Abū ‘Alī al-Husayn ibn ‘Abd Allāh ibn Sīnā,拉丁语Avicenna,980~1037。]、以阿维罗伊著称的伊本·鲁世德[注:Ibn Rushd, 全名Abul-Walīd Muhammad ibn Rushd,拉丁语Averroes,1126~1198。],对欧洲中世纪天主教经院哲学的兴盛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一点通常被论述较多,且很多西方学者认为在把古希腊哲学输回欧洲后,古希腊的影响在伊斯兰世界已经被完全清除了。其实,还有被忽视了的另一个方面,即:通过安萨里(al-Ghazzālī,拉丁语Algazel,1058~1111)、苏赫拉瓦迪(al-Suhrawardī,1153~1191)、伊本·阿拉比(Muhyi al-Dīn ibn ‘Arabī,1165~1240)等穆斯林哲学家、教义学家和苏菲学者的努力,古希腊的遗产被以一种转换了的形式继续保存在伊斯兰传统内部,成为伊斯兰传统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基督教欧洲与伊斯兰世界同样继承了“两希文明”的遗产,但对其进行取舍、诠释的思路却迥然不同,并因此发展成为完全不同的“传统”。当欧洲刚开始通过翻译穆斯林学者的著作而引入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时候,恰是亚里士多德学说作为一种理性主义体系而在安萨里的批判之下被伊斯兰世界拒之门外的时候。纳斯尔博士指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大姐妹文明在14世纪以后的分道扬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这一理性主义哲学在两大文明中所扮演角色的不同。在东方,通过安萨里及其他人如拉齐(Fakhr al-Dīn al-Rāzī)的批判,理性主义的影响力被缩减了,为苏赫拉瓦迪的光照学说的传播以及伊本·阿拉比学派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而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的来临对于早期建立在光照说基础上的奥古斯丁、柏拉图主义的破坏来说作用不小。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后果,它带来了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世俗化形式,这在后来的文艺复兴时期颠覆了中世纪经院哲学自身的堡垒。”[7]54-55
是否可以说,西方现代性问题的诸多症结实际上与欧洲文明仅仅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中断了与知识的神圣源头的联系有关呢?西方现代性面临的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如传统与现代化、神圣与世俗、超验与理性、宗教与科学等,是否都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之间的思想断裂?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即使在中国也几乎为所有的读书人所熟稔,它鲜明地表达了一种与“传统”决裂的“现代性”决心。而“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如今却成为西方现代性最大的困境之一。
伊斯兰传统则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与西方现代性的“求新意志”相反,穆斯林学术传统一直在“向后看”,一直致力于要把“当前”根植于传统当中。穆斯林哲学家很早就致力于调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分歧,如有“第二导师”之称的法拉比(Al-Fārābī,870~950)就曾专门撰文讨论二者之间的差异问题。这种调和不是简单的“和稀泥”,而是代表了一种中庸、兼顾的伊斯兰哲学传统的思维模式。到神秘主义大师苏赫拉瓦迪的时候,他则以“光照哲学”(Hikmat al-ishrāq)的名义把古希腊的智慧直接纳入了伊斯兰传统之中。他提出,“智慧”(Hikmat)或“哲学”,是造物主通过古代先知易德里斯(Idrīs,即“赫尔墨思”)(注:赫尔墨思主义(Hermeticism)是一种源于古埃及的神秘主义思想。1463年,弗罗伦萨的马西里奥·费西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翻译了被认为可能是由古埃及“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思·特里斯美吉司托斯(Hermes Trismegistus,three-times master)所作的一批文稿。赫尔墨思接受到关于物理世界的神圣知识,如同摩西接受到了关于道德世界的神圣知识一样。这批文献声称,造物主以数学语言书写了宇宙的奥秘,只有少数研究神秘学的人才能透过表面现象洞彻这些奥秘。有学者认为这些文献实际上在3世纪之前就出现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了,由埃及、希腊、犹太、诺斯替以及少许基督教的资源汇合而成。15世纪以前,这些不为欧洲人所知的文献和学说一直在穆斯林世界流传。一些穆斯林学者认为赫尔墨思即《古兰经》中的古代先知易德里斯,并认为他是哲学之父。)启示给人类的。后来,这一神授智慧分成两支:一支传到波斯,另一支传到埃及,后从埃及又传到希腊,最后,经由这两种资源——即波斯和希腊——进入了伊斯兰文明,而苏氏自己就是这两种资源的汇聚点。他明确地推崇古希腊更具有宗教精神的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而对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不感兴趣。以光照哲学为代表的伊斯兰哲学样式,贯穿了整个伊斯兰思想史。后世的伊斯兰哲学家都继承了这样的思路:承认理性的有限性,以及在理性之后凭借超验的手段获得与神圣源头(造物主)的交流。如17世纪伊斯兰哲学的集大成者波斯学者穆拉·萨德拉(Mullā Sadrā,1572~1640),他重新回顾并综合了伊斯兰思想的各流派,提出有三种获得知识的途径:启示(al-wahy)、实证或思考(al-burhān, al-ta‘aqqul)、精神的或“神秘”的视觉(al-mukāshafah, al-mushāhadah)。他提出了“超验哲学”(al-hikmat al-muta‘āliyah)的概念,并始终坚持在“存在”(being,阿拉伯语wujūd)的层次上讨论哲学的基本命题。三个世纪以后,黑格尔提出,西方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由于研究“存在者”(德语das Seiende)而走偏了,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对象应该是“存在”(德语das Sein)本身,这其实就是穆拉·萨德拉的思路。穆拉·萨德拉关于“存在”之深层思索,与20世纪最受推崇的西方哲学家之一的海德格尔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伊斯兰传统非常重视整体性和统一性,这与根源于基督教末世论的西方现代性之二元对立症结有根本的不同。而这种整体观是根源于伊斯兰教的根本信条“认主独一”(the Oneness of God)的。审视伊斯兰哲学史,“认一论”(阿拉伯语al-tawhīd)是穆斯林哲学家的底线,无论哪一流派均是如此。与基督教所体认的“三位一体”的上帝不同,伊斯兰教的最根本信条是体认真主绝对的“独一”。《古兰经》多次指出真主的绝对超越性:“你说: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敌”(112:1~4)。同样,与基督教所体认的以“道成肉身”的方式进入历史中的上帝不同,穆斯林学者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区分了作为造物主的真主是“绝对存在”(阿拉伯语wājib al-wujūd),而作为被造物的宇宙只是“可能存在”(阿拉伯语mumkin al-wujūd),二者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惟有你的主的本体,具有尊严与大德,将永恒存在。”(55:26~27)然而,通过“知识”(启示的、理性的或直觉的),人又得以与造物主沟通。每一个人凭借他自己对真主的体认,通过他自己的“知”与“行”获得向造物主、向终极实在回归的可能性;这也与“因信称义”的基督教救赎论有明显的不同。总之,“认一论”在伊斯兰传统中的绝对优先地位避免了哲学讨论中的二元论或割裂历史的倾向,因此不会产生西方现代性问题症结之一的二元对立问题。
在“认一论”优先的前提下,伊斯兰传统则一直保持着其“神圣性”而拒绝彻底的“世俗化”。前述穆拉·萨德拉所总结的获得知识的三种途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对于“知识”之可能性的多向度的定位,超越了西方哲学传统仅以理性为标尺的单一向度的困境。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是经由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之手从阿拉伯逍遥学派那里引入到中世纪天主教经院哲学当中的,并因此为反宗教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埋下了伏笔。“因信称义”的基督教教义本质上是与理性主义相矛盾的,因为基督教的“信”并不以“理性”为前提;这种矛盾导致了要么彻底地皈依宗教,要么彻底地皈依理性。而伊斯兰教恰恰把信仰定位在人的理性之上。据统计,在《古兰经》中,有50多处用到“理智”、“理解”等词,约100多处提到“知识”,约750节、1/8的篇幅都在鼓励人们研究自然、进行思考。伊斯兰教认为,“理智/理性”(阿拉伯语‘aql)和“知识”(阿拉伯语‘ilm)是人类能够认主、拜主并最终实现“复命归真”的重要工具;但理性又非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最高的、接近真主的方式是超验的直觉和心灵的观照。这种多向度的知识论以及把“知识”与神圣源头联系起来的观念,避免了对理性主义的崇拜,使得伊斯兰世界即使在西方现代性的强烈挤压下,仍能在思想领域保持自己以“认一论”为核心的强调“神圣性”的“传统”(阿拉伯语Sunnah)(注:阿拉伯语的Sunnah,有人主张译为“圣道”、“圣传”,以区别于含义已经固化的“传统”。而关于这一传统的论述,可以参见Seyyed Hossein Nasr:Knowledge and the Sacred,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郭晶:《神圣的“传统”——当代伊斯兰学者纳斯尔“传统”观引介》,载《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马效佩:《纳斯尔教授的“圣道伊斯兰教观”初探》,载《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
当然,如前文所述,当代的伊斯兰世界也是卷入西方现代性之中的,穆斯林们在现代性的全球逼仄之中,对于自己传统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甚至是缺失的。几百年以来,深受西方现代性熏染的几代穆斯林学者,尤其是留学西方的穆斯林学者,大都习惯了以别人的眼睛来观察自己,把伊斯兰传统视为“前现代”、“中世纪”、“过去时”的一种资源,认为应该采取西方式的手段改造之并使之“现代化”。其实,伊斯兰传统可能不属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现代”(modern),但却毫无疑问在时间上是属于“现在”(contemporary)的。所以,伊斯兰传统尤其是伊斯兰的学术传统,仍是一种需要回顾、发掘并重新阐释的资源。
四、结语
后现代思想对现代性的反思与颠覆,已经揭示了西方现代性的若干不可逆转的症结,但因为“身在庐山中”,后现代思想并未给出一个替代性方案。反之,后现代思想可类比于基督教末世论在西方现代性规划当中的投射:它像《启示录》一样描绘了一个崩溃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末世,但已被理性主义“驱逐”的上帝不可能像《启示录》中的“基督”那样复临。这种无建设性的摧毁,只能以美国大片中来自外星的“超人”或变异的“蜘蛛侠”来做想像的心理安慰。跳出欧洲传统的“庐山”之外,或许是一个必然的思路。而对伊斯兰传统的重新审视和梳理,相信能够提供一种远比现代神话真实的“他山之石”。
综上所述,人类生活的这个世界本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并存着若干不同的“传统”。但近代以来,诸传统之一的“西方传统”产生了“现代性”思想并将之传播至世界各地,却几乎成为今天世界上“独占”的思想体系。而与之同源异流的伊斯兰传统却恰恰能够提供反思、审视这一霸权话语的可能性,提供寻求“非西方”的“现代性”的可能路径;或者说,后现代的可能性,正是埋藏在类似伊斯兰传统这样的非西方传统当中,等待我们去挖掘和阐发。
[ 参考文献 ]
[1] 谢立中.“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J].北京大学学报,2001(5).
[2]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 哈贝马斯,恩斯特·布洛赫: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浪漫派[A].转引自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M].顾爱彬,李瑞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 赵景来.关于“现代性”若干问题研究综述[J].中国社会科学,2001(4).
[5] 张承志.地中海边界[J].读书,2007(2).
[6] Seyyed Hossein Nasr. Knowledge and the Sacred[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
[7] Seyyed Hossein Nasr. Three Muslim Sages[M]. Lahore: Carvan Press, 1988.
The Arab-Islamic Tradition in a View of Post-Modernity
ZHOU Chuanbin
Abstract Post-modernity is still a part of modernity, but it is the part of criticism and overturn. Moreover, modernity is a kind of ideologized idea form, which roots in western Christian tradition, and has spread throughout world along with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ough it has suffered from impending of the western modernity more and more, Islamic tradition is still a kind of cultural source standing out of the western modernity which can serve as an inspecting mirror to reason the problem of western modernity.
Key Words Post-Modernity; Modernity; Arab-Islamic Tradition
(责任编辑:李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