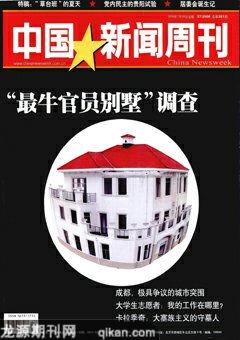“草台班”的夏天
秦 轩


周末,草台班的演员——上海的一群白领,去他们不熟悉的社区,在个人创作的戏剧里,反省自己的人生、自己所在的城市和社会……
2008年7月20日17时,下河迷仓。
上海南端有一条被称为“下河”的龙华港。龙漕路200弄,依河而建。上海独一无二的民间剧场“下河迷仓”就盘踞在100号3楼。
从仓库外的防火楼梯往上爬,从二层起,楼梯旁贴着各式演出的海报。这几年,上海几乎所有非商业的民间艺术团体都在这里排练或演出过。
进到迷仓,先是一套老式的电影放映机,破破烂烂,底下摆着其他的装饰物,还有些狰狞的岩石。旁边的墙上,有迷仓主人王景国写的募捐倡议布告。文字仿古,有点骈文的意思。布告写明这里不收钱,但希望大家捐助。
从入口进去的方向,先经过一个吧台,大约可以坐下十几个人。吧台旁摆着各式的装饰品。过道旁立着一个电话亭。走过吧台,经过一块传达室大小的平台,上面堆着杂七杂八的东西,这算是后台了。舞台和前台连在一起,迷仓顶端就是屋顶。衔接的地方有三层台阶。四方的舞台四角各有一根四方的大柱子。整个面积有一个半篮球场大小。
如果演了人以上的戏剧,舞台就显得很狭小。舞台的正前、左、右各有几排木质的椅子。正前方有一排VIP专用的沙发。整个剧场,连坐在地上的,大约能坐160人。墙壁、天花板与地面,都涂成漆黑,窗户也封死。白天进去,会突然感到眼睛很不适应。
下河迷仓
迷仓主人王景国,年轻时是上海戏剧界的活跃分子,后来去了美国。前几年回上海办小剧场——真汉咖啡剧场。据说真汉咖啡剧场是2000年上海话剧舞台的一件大事一第一个私人剧场,也是第一个咖啡剧场。但赔了,后来就开办了这个下河迷仓。
此时,上海一家民间剧社草台班戏剧社几名成员,在化妆间换衣服。
侯晴晖追着他们一个个登记收钱。第一次参加这次活动的除外,其余人都要交5块钱,迟到的要交10块。自草台班成立起,3年来,都由侯负责收这笔钱。上海的物价涨得很快,但这笔钱的数目一直没变。
赵川和“疯子”在台上接投影仪,用凉席支屏幕——待会儿要放一段关于草台班的纪录片,包括不久前演的戏剧《蹲》、在社区的个体表演等等。
搞园林设计的人高马大的刘念,在两边进进出出,一会儿提醒会员交钱,一会儿要大家把东西收拾好,赶紧准备训练。他爱说的一个笑话是,“我不会告诉你我有200多斤重。”
草台班是一个很普通的戏剧社。在上海这个地方,民间戏剧团体并不少。每年都有几个像草一样长出来,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消亡,无影无踪。和其他剧团比起来,草台班有点不一样。这可能是城市里最“草率”的团队,没有一个人是专业的。
核心成员中,“疯子”在一家画廊做企宣,在大学学的是信息技术。侯晴晖是家庭主妇,过去搞美术设计,参加草台班以前她只看过话剧《茶馆》,而现在她已经是草台班的女一号。庾凯是视觉艺术方面的自由撰稿。年纪最小的林辰在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念大三,编导专业。常来的一些人很多是搞摄影的。最近有个卖电脑的小伙子吕毅挺积极。总之,没有一个是以“演戏为生”的。
草台班成员的年龄,像一个金字塔。赵川和女1号侯晴晖是60年代生人。刘念、庾凯是70年代的。其他的几乎都是80年代生人。
说不清楚草台班是一个团队还是一个平台。想来参加就可以来,不来也没关系。坚持来的人,日子久了就成了核心成员,在班子里说话有了分量。有时,想来减肥的也有,想接受表演培训的也有。核心成员比较稳定的就十来个,但刘念掌管的那份人员名单,却有70人。
下河迷仓没有中央空调。夏天来这里活动的团队不多。去年夏天排练《狂人故事》,下河迷仓的温度让人记忆犹新。最近赵川和刘念一直在想办法找新的场地。经过一周的努力,他们并没有找到更合适的地方。有空调的场地是要钱的,只有下河迷仓免费。
活动的时间改在17点开始,长度大约4个半小时。晚上比白天凉快一些。
一切妥当后,十几个人脱了鞋,围坐在近半个篮球场大小的舞台上。头顶舞台专用的聚光灯,照射在漆黑的地板和每个人的躯体上。旁边一个老式工厂爱用的大电扇,嗡嗡地吹着。它其实管不上什么用。
他们“感谢”代号“海鸥”的台风。昨天,台风“海鸥”抵达上海,带来一场不大不小的夜雨,但没有风暴,温柔得像婴儿的呼吸。
侯晴晖在迷仓外阳台种的野花,快要开花了。
“疯子”的上海故事
“疯子”演戏时叫疯子,或者疯子××,上班时姓葛。上班就是上班。记者采访,他也不会占用上班时间。“我做这个事情就用这个名字,用真名反倒没人知道。”2005年,“疯子”毕业,此前他在学校里是戏痴。他在学校是话剧社的主力,毕业后还和一些爱好者演过《哗变》。女朋友就是在那时认识的。
“疯子”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上海人。这就使草台班的核心成员中,上海人成为极少派,只剩下1位——创办人赵川。去年草台班去台湾演出,和疯子的工作冲突,他就把工作辞了。“疯子”现在在一家画廊做策划宣传之类的工作。这活是赵川刚帮他找的。一个月收入大致在两三千。
“疯子”打耳钉,小腿上有文身,图案父母看不懂。父母是工人。父亲喜欢吹拉弹唱,家里摆着钢琴。
这段时间,除了上班、拍戏,他还在忙结婚的事情。两人刚刚办证,老婆住在丈人家,自己住在父母家。“以前租房发生了一些事情”,他的母亲要求他回家。
家里有他一套房子,几年前房价没有疯涨前就买好了。按他的想法,结婚后,两个人可以出去租房住。原来的房子可以卖掉。可母亲的意思是,结婚得有房子。房子是几年前买的,当时1万4一平米,现在已经涨到2万2。
到7月,装修已经进行一大半,地板也快装好了。
他住在海伦路,那里正在施工,修建新的地铁。“这里快变成老鼠洞了”。他说。从海伦路的地铁站绕着上海的内环,走40分钟到下河迷仓所在的龙漕路。沿途,不论走到哪个地方,转身四望,周围都被楼围得严严实实。
这是中国地价、楼价最高的城市之一。
5月份的个人创作演出,“疯子”表达了他对上海的感受。那次演出恐怕是他和草台班演出生涯最特别的一次,不是在剧场、帐篷,而是在社区浦东联洋年华社区中心人工湖畔的休闲广场上。
那天太阳很晒。
“下一个节目叫游戏。”报幕的刘念说,下面有几个孩子开始尖叫。前几个节目已经让他们乐得不行。刘念下面的话更可笑。他说,演出的演员叫“疯子”。围观的孩子和大人笑了,草台班的其他演员也笑了。掌声响起。
“疯子”拎着两个鼓鼓的麻袋,走到台中央。他抡起一个麻袋,绕着自己画了个圈
说,我要在这块地皮上建造我想要的城市。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堆塑料标签牌,牌子上写着地名。“疯子”一边念,一边把牌子立在脚下:市政府、南浦大桥……汤臣……新天地……地铁2号线……上海博物馆……
他说一个名字,底下的孩子跟着搭腔:“南浦大桥……汤臣……”也有孩子不耐烦地尖叫。他盖到“沿路高架”时,几个孩子围上去。有个小男孩想把他的牌子踢倒,刘念上去,把孩子哄到“台下”。
两个麻袋要掏空时,“疯子”喊着:学校?学校?游乐场?
所有的牌子都立起来,“疯子”说,为什么我们会被自己建造的城市围起来呢?我们会被围住么?说着将地上的牌子踢开,吓了众人一跳。
接着“疯子”鞠躬谢幕,一群孩子围上来,抢标签牌。草台班的成员也上去捡道具。刘念一边捡,一边从小朋友手里小心拿走标签牌,反复地说“小朋友小心手,会划伤。”
整个演出包括草台班6个演员的6部作品,都是个人表演,表现地震的山、卖洋娃娃躲避城管的商贩、拥有一堆卡的卡奴和水污染的城市等等。
他们带去的十几个小板凳都坐满了。周围四五十个观众,都是联洋小区的居民,老少都有,带孩子来看的居多。
戏剧前的杂事
有些人还没到,赵川决定看录像延后,先讨论一些杂事。
第一件事是多伦美术馆演出的事情。有人说,过去替人家热闹一下,没啥意思。没怎么讨论,这件事否了。
接着是杭州“江南藜果”邀请演出的事情。大家比较认同。3个月前,“江南藜果”的团队“水边吧”和草台班合作过一出戏,叫《蹲》。在那个戏里,最强势的掌权者要求人都站着,有钱和谋求挣钱的人认为“坐”才意味着优秀。“江南藜果”则表演一位难以被人理解的保护自己个胜的姿势,蹲着。
1962年出生的“江南藜果”,也是一个搞民间戏剧的。1995年,他在广州创立水边吧。迄今,“江南藜果”的水边吧戏剧实验室,已经创作约20部、上演约80场向多种方向探索的实验戏剧。骨干就他一人,现在挪到杭州去了。
第三件是印宣传明信片的事情。有人找到剧社的负责人赵川,说可以免费制作明信片。接触后发现是误会。对方的意思是可以为草台班免费发送,印刷还是要付费的。赵川决定不做。草台班自己并没有宣传打广告的钱。剧社坚持不搞商业演出。
与外界交涉的事情,一般是赵川做主。以前赵川写小说,也做编剧,曾被龙应台邀请去台湾做驻市作家。在台湾结识民众戏剧旗手级人物王墨林。2005年,在后者协助下,组织编导了“38线游戏”,讲朝鲜半岛的分合,参加了韩国的“2005光州亚洲广场戏剧节”。
那时赵川已经接近40岁。
除了办草台班,他还写一些关于当代艺术的文章和书。最近他发现,自己越来越被草台班的事情缠住了。
“草台班才是我一生的事业。”
看纪录片时,两个新人迟到。刘念单独找他们谈话,劝他们离开。赵川和其他老成员又将两人劝回来。他希望草台班能够保持一个开放的状态。
在刘念看来,这是个麻烦事。这次参加的人达到25个,只来过一两次而不是坚持每次都来的人多,训练时舞台都站不下。这样的草台班该如何管理,是个问题。
刘念是全剧团唯一一个MBA在读。草台班里,他最把这个社团当作一个团队,而不是平台。所有想参加活动的人的名单由刘念掌管。“人太多了,我那里有70多人,”他不停地抱怨说。他们说刘念是草台班的阿姨、保姆和服务器。
刘念从重庆来上海有8年了。30出头,他在一家公司做到高层。在草台班,他和“疯子”是戏龄最长的人。在重庆上大学时,他是学校戏剧社的骨干。据他说,这所工科学校有文艺传统。“忠字舞就是从我们学校传出来的。”
草台班的杂事、活动几乎都是刘念负责,包括通知团员参加活动。
公司里没人知道刘念的事,他们管他叫刘总。在草台班,大家称他是服务器、阿姨或者保姆。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只有笔筒和文件,没有任何照片或者玩具,更不会有他演戏的剧照。墙上钉的几张照片也是关于建筑的。
“我挣钱是为了让我妈妈开心,草台班才是我一生的事业。”刘念说。他中学时,父母离异。
到草台班排练,他会穿着宽松的大裤衩和运动背心,一双拖鞋明显比脚要小一号。“这是我妈给我买的。”他说。
这段时间,他在为搬家忙活。8年来,他差不多每两年搬一次家。这次他看了十几套房子,才算敲定。
最近草台班有些人注意到,最近他在刻意躲避。“他好像不在状态,几句台词也会背错。”有人说。
训练后吃烧烤,他抱怨说纪录片没有他演戏的镜头,让他很失落。
“身体”与“梦”
二十几个人在不到半个篮球场大小的舞台上行走。赵川负责喊节拍。行走的要求是,每个人要照顾和其他人的关系,保持舞台上疏密均匀。有时要快走,有时要慢走,有时要蹲下走,有时要跳着走……
走完,赵川要求大家学刘念走的姿势,二十几个不同体态的“刘念们”变成了螺旋型,绕着舞台转。
行走结束,大家围坐一圈。赵川给大家发了一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文章探讨如何利用和认识自己的身体。赵川说,“请大家用手指抚摸自己的身体,看看有什么新的发现。”
接下来,众人围坐一圈交流对自己身体的新发现及记忆。一个叫阿汗的演员说,我屁股上有个坑,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打针。林辰说,我发现肘部上有3块突出的骨头。
“疯子”说,我的下嘴唇上有块凸肉。小时候骑车摔跤,我自己的上牙把下巴咬穿了。我现在有点想不起当时自己吃自己的滋味。
从南京赶过来的摄影师李岩接口说,我也有类似的经历,不过是下牙顶着嘴唇。
主持话题的赵川说,看来要掀起一场揭伤疤运动。众人哄笑。赵川的女友吴梦说,刘念有话要说,他刚才就举手了。刘念打个怪腔,做惊诧状:我什么时候有话说了。随即又换笑脸说:我腿上的伤疤是上次排练疯子搞的,呵呵。不过我也弄伤过“疯子”现在两清了。
最后的大戏是即兴表演训练。赵川要求选一个人坐在舞台中央,表演做梦。舞台下的人根据做梦人的种种表情、动作暗示,进入梦境,作为梦中的要素出现或消失。
去表演的大都是社团的“老人”。
新来的吕毅主动上台“做梦”。他双臂环抱,思考了一阵说,“我梦见自己来到一个火箭发射场”。
赵川制止他,“不要用语言表现场景。”
吕毅只好改做一个简单的起床上班的梦。他还是免不了一边做穿衣服的动作,一边说,我穿衣服。
最让新人吓一跳的,大概是最后庾凯的梦。梦里她时哭时笑,一会儿又人吃人,林辰和其他演员等又撕又咬。庾凯的表演很抽象,台里的“老人”上去。侯晴晖跑上去,站在她身后扮演树的模样,双手像钟摆上的秒针摆动。一名演员上去,把庾凯像桶一样在地上滚来滚去。刘念又上去,拉着侯晴晖做共振的样子,仿佛两组人之间有神秘的联系。
“这是即兴表演,是为了打破你自己平时对身体的约束。”赵川总结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