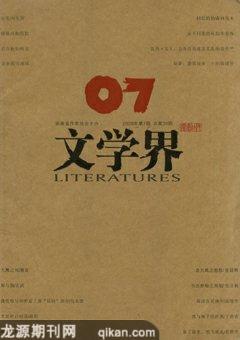念天地之悠悠
曾晨辉
那一年如果我不得那种病,可能也有另一种病降临,照通常的说法,命运吧。
起初,我父母是不屑一顾的,不就是晚上失眠吗?调节一下就会好的。父母认为,失眠不是病,最起码,感冒——必须是重感冒,才算是小病。父母对病的认识就是这样,大病是无法医治的,小病呢,不治它也自然会好。
我父母的态度让我伤心,因为我自己已感到死亡将笼罩我,而父母,竟对此轻描淡写。失眠在黑夜中像个妖精,一点一点地浸入我的灵魂,一些过去从未出现过的人和事,一下子堆满了我的思想。比方说小时候我在乡下见过的一个疯女人,她的笑,她的叫声,她的怪异,刹那间在黑夜中复活了。她后来投水而亡。我又想起了那一脉水,以前,只是想起水的波光和柔美,可自从疯女人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水就响起了她的声音,以及她残梦似的黑眸。反正,我一走进黑夜,整个灵魂就旋转起来,一刻也歇不下来。到了白天,我变得寡言少语,仿佛世界不过是声音和色彩的大混合,其实和我没有关系。我只听到一种声音在唤我:你快要死了,好好多看几眼吧。待我去捕捉那声音,它马上就消逝了,刚安静,它又幽灵似飘来。
我开始从那不着边际的声音回到了自己的身体。我身体内有什么?有病。有一种像核武器一样恐怖的病,无声,又生有千万翅膀,随时飞向每一个毛孔。我倾听身体内的响动,可没有。我更加恐惧,越没有声音,越证明病的险恶。
白天,我围着城里一圈又一圈地走。这座城,我很熟悉,就像熟悉我的母亲。可突然间它就异常陌生了,树、阳光、人,全是陌生的。我问自己:为什么走在这里?我走到哪里去?我隐约记得母亲说过,我生在城里的一条小巷里。我恍恍惚惚走进一条巷子,除了看到阳光在一棵百年老樟上闪动,除了看到野草在青石上低着头,我什么也没得到。我走到了小巷的尽头,那是一栋荒芜的老宅,已无人烟,只有草和一些凄凉的花自由生长。我站在其中,忽然想哭。哭吧,这里没人。我自言自语。我就哭了,哭得像个小崽。我是个小崽,在冷酷的时间面前。哭够了,我就默看那些草。比起我来,草真幸福啊,它们也许不知死过多少个冬天了,可是,又在春天里活过来。它们心中也不知藏着多少苦闷,可是,春天让所有苦闷一次释放。草永远是永恒里的过客,却永远是过客里的永恒。我并不具有草那种寂寞无声的属性,除非有一天我变成了草。这宅子的主人哪去了?这宅子在此多久了?我感到自己就置身于这么一座宅子中间,天是封面,地是封底,时间是窗。如果打开窗,我能看到什么?窗外尽是像我一样不知走向哪的人。或许,窗外是我的影子,我的无法走近的梦幻。我住在一座孤独的宅子中,上下是天和地,时间横在正中,大海般的漫漫。我的心境大概如此。假如一个人活着,无非是存在于这么一座老宅中间;假如一个人死了,又能逃到哪去呢?也存在于天地和时间深处。我身边的草,它们在天地间低着头,在时间里沉默着,生和死,没有人告诉它们,点化它们。它们倒是用生和死来证明时间的存在。时间若没有一件具体的东西来依附它,那时间本身也是死的。
不过,我越往深处想,我越混乱。我天生不是哲学家,在深刻的问题面前,只是个脆弱的小崽。老天即便赐给我二辈子来思考生死,也许我依旧在原地行走。生死这个问题就像天地本身,甚至像宇宙本身,太神秘了,我面对它,是无力的、渺小的。
我从巷子里走出来,什么也没有获得。我走进新华书店,默默寻找病因。书上所说的病太多了,有的我听说过,有的我没听说过。我怀疑自己是恐病症,可又不完全像。很多时候,我只是万念俱灰,觉得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正如种一棵果树,如果不结果,这棵树的意义何在?我明明知道没有意义,却对于生活又有点不心甘。我总是能够察觉到有那么一点光亮在前方闪忽。我这是有根源的。我快三十岁了,除了做梦之外,还是做梦。我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像优秀运动员,金牌就是具体价值的体现;像工人,劳动模范这个称号就代表着价值;像农民,粮食丰收就是一种喜悦。包括我四周的同学、朋友,他们有的留学海外,有的学业有成,有的商场春风得意。我呢?几年前就立志写一部书,希望它给我带来令人意外的收获,既有金钱上的,又有精神上的。现在,书没写成,倒落了一场病。反正,我担心自己书未写成,却会过早的因一场大病而离开这世界。这想法是有点可笑,但它像鬼魂附体,折磨我的心。
那么一点光亮在前方闪忽,这是我的未来吗?这点光亮仿佛一匹永远走在我前面的马,能听到它的奔跑,但看不见它。
说穿了,我还不想此生庸庸碌碌,虽然我父亲常骂我是废物。父亲认为我从小被宠坏了,这责任主要是我母亲应该承担的。父亲常说自己十四岁就当家理事了,连我爷爷都有点惧怕他。我对父亲心怀不满,你也是我爷爷宠坏的,导致你一直在家里很专横。我父亲的专横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他根本就不想讲道理。我记得好像也跟父亲说起过写一本书的梦想。父亲首先是冷笑,然后只说了一句话:站在地上走你的路,幻想是没有用的。父亲后来还给我讲了一件事:上世纪70年代,他在一个山区工作,从河北那边购了一批良种牛,壮实得很。可这些牛习惯了在大平原上行走,一到了这大山里,走起路来东倒西歪的,结果伤亡不少。我父亲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事都要现实一点,不然,就会出问题。父亲还隐含了另一层意思,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做这种牛,现实毕竟不是大平原。
我在心里反感父亲,但我同时也不喜欢自己。第一,我目前没有任何东西向父亲证明我的价值,哪怕有一丁点也好;第二,我为什么遇上这样一位父亲,专横、不讲道理,我见过很多讲道理的长辈,而偏偏父亲不是。
去年,我在单位工作表现颇出色,年终评先进个人时,我把握十足,就凭我这一年的成绩谁又能把我的先进个人抢去呢?结果事与愿违,一位领导在定夺时轻轻评价了我一句:小伙子能力不错,就是嘴皮子管不住自己,喜欢乱说。
这一句话基本上击中我的要害,与父亲对我的评价异曲同工。
但我心里照例不服气,照这个领导的意思,人的嘴巴应该是一口牢笼,是囚禁人的语言功能的。我想。
我依然我行我素,而且,那个领导的评价反而加重了我的逆反心理。这之后,每次领导批评我,我就敢于争辩,甚至一二三列出本人为什么没有过错的理由。我想:我又没什么阴谋,光明磊落,何苦要强迫自己把话压心头呢?
我回到家,对父亲说起此事,父亲看了看我,冷冷的一句:活该。我望着父亲,呆了。
我无人诉说,便将这种矛盾放置在心头。在孤独的时候,做为一个对立面。我质问它:我难道就这样活着,一直活到死去吗?
在黑夜里,我盼着早一点天亮,却又十分害怕明天的来到。明天,时间像大海,我像小船,一样觅不着岸。明天那轮金光四射的太阳,横在我面前,照着我有点紧张的脸。我感到它与今天的太阳没什么二样,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递进。在这轮光圈下,我得行走。按父亲的说法,不是在大平原上行走,是在现实中行走。
我父亲当然不会想到自己的儿子这一向究竟在想什么。他对我的了解过于简单,无非是认为我单纯,没有头脑。他甚至还产生过这样的想法,把我的工作调动一下,调到乡镇去工作,去和农民大伯打交道,让农民大伯来改造我。我不是不喜欢农村,相反,农村对我有一种莫大的引力。我有一个朋友,是一所乡下中学的老师,我常去他那里。乡下开阔、宁静、新鲜。我经常和这个朋友走进山里,坐在树下,不说话,不胡思乱想,就那么空空的坐着。我受不了父亲带有强迫性质的改造。我真的是一块废铁了,你把我放到最好的炼炉里,就能炼成钢么?我仅剩下那么一点梦想了,而你做父亲的,当头一捧就打得我茫然四顾。要改造,我自己改造自己好了。
我倒是想起了父亲的一个朋友。我想去求助他。他是50年代的名牌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某省的组织部工作。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从那个省的组织部调回了,在本县的组织部工作。再后来,又调到了一所中学。他迷恋《易经》,十几年来只收获了一些皮毛,他就转为研究佛学。我以前听他讲过《易经》,玄之又玄,虽听不懂,却也不觉得讨厌。
我想去求助他的愿望是:首先,要他告诉我,我能不能写一部书出来;另外,他修习过易经的,给我看看命运的走向。其实命运这东西有点不可预测,他也未必弄得明白,但只需他从大的方面提醒提醒我,就行了。
他名叫钟玉,我叫他钟老师。他住在学校里面。我来到他家。他一切依旧,读经,呷斋,一身枯瘦,精神却很足。
我一见到他就哭起来,像个小崽。他说哭吧,想哭就哭,泪水可以排除你身上和心上的一些毒素。我在父亲面前从不敢哭,父亲对于哭是有点鄙视的。可我在钟老师面前,就毫无顾忌放声大哭了。我过了很久才平静下来。之后,我向钟老师说了很多,关于命运啦,事业啦,我对父亲的不满啦。我把自己要写一部书的计划也说了出来。钟老师笑着问我:你这部书写的什么?我说写我的经历。他说,你的经历?你的经历太平常了,读书,当兵,当兵回来之后安排工作。我沉默了。钟老师说,书不是不可以写,但不要勉强自己,勉强写书是写不好的。曹雪芹的《红楼梦》流芳百世,可他不是勉强写出来的。金庸的书畅销,但他写的时候绝没有想要畅销。我和你一样,多年前整天念叨着要写一部大书出来,二十几年过去了,我连一篇像样的短文都没有完成。
至于命运,钟老师说,不要轻易相信命运,命运是无法料定的,比如说一棵树,它初生时,谁能预料它今后是歪的还是直的,它到底能在风雨岁月中站立多久?谁也不知道,连那个种树的人都无法知道。种树人种那棵树时,只是一个念头而已。钟老师指着窗外一棵老树说,我并不知道它的来历,所以更不敢去预测它。钟老师说他以前学《易经》时,偶尔给人推测一下,其实那不过是一种游戏,满足人们空虚的心理。
最后,他建议我跟他学学佛,我马上说好。他教了我一种观心的方法,很简单,当杂念袭来时,只是反问自己一句:我现在在想什么?之后,再反问自己一句:我为什么要这样想?很快就会觉得自己的念头十分可笑,像一只小猴子在脑海里跳似的,蛮顽皮,又可笑。尤其在黑夜失眠时,思绪纷飞,就可以观心,每一个梦幻不过是一念罢了,来了就来,去了就去,不必理会它们。
可是,这种观心的方法实在要命,它有的时候简直像牢宠一般。比如有时走在街上,见了如花似玉的女子,她们走路的姿态真诱人,她们的身子好妖娆,像水一样的柔。这念头刚一起,我马上观心。但我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想,就控制不住,许多不良的念头乱箭似射来。难怪钟老师还讲过一种什么观,见了妖艳女子,要把她们想像成一堆白骨。想像成那个又如何呢?难道就真的可以控制自己不去想?我疑惑不解。最难受的是回到家中,见了父亲,那种不满的情绪一下子冒出来,我赶快观心:他是我父亲,我不能产生不满。可是不行,抑制得越厉害,那感觉便十分强烈,容不得我不发作。父亲冷眼看着我,我从小就惧怕他的冷眼,刀子似的,锐利。我在心里说,知道吗?你做为父亲,为什么总是打击我、讥讽我,从不鼓励我?你对我超出了平常意义上的严格,几近冷酷了。此刻,父亲说,你这一向又无所事事?我的不满已上升到极限,说,你怎么知道我无所事事了,我忙着呢。父亲被我激怒了,抓起桌上一只茶杯扔过来。父亲愤怒的时候总是习惯去摸茶杯。我躲开了。茶杯打到墙上,落地,全碎了。好漂亮的茶杯,白瓷,上面有花。这天晚上,我做了个梦,自己坐在一条小船上,突然间,小船碎了,全是一朵一朵的花在闪动,我四周原来是一片大海。
我又回到了黑夜。黑夜中,一个接一个的念头像拳头一样击来,我用观心,拨开这个,那个又来了。我仿佛一个拳击手,拼命地飞舞,念头却更稠更密了。
每一个念头邪魔似的,走向我。一个女人走了过来。我在刑场见过她,她和一个男人合谋杀死了男人的老婆。她笑着,说,跟我走。她的笑妖艳十足,勾魂夺魄的笑。我马上观心。可女人随即变化了,化成了子弹,射向我的额头,二眉中间的印堂穴。女人在我大脑中间笑起来,笑声像秋风,荡去很远,又回来。我大叫了一声,不知是嘴里发出的,还是心里发出的。
我吓得哭了。
我在黑夜里丢了魂,白天,人空如一个无心的石头,去单位上班,回父母家吃饭。父亲终于相信,他觉得我患的不是感冒,至少,是心里感冒了。母亲见我这个样子,不知所措。母亲开始频繁地指责父亲,列举他多年来在家中的冷酷,一桩桩,一件件,总之,我父亲是家里的君主,而且是专制的君主。母亲说,从今天起,为了我的儿子,我必须打倒你。母亲还说,我儿子从六岁起,你就没给他一个好笑脸,仿佛儿子生来欠了你什么。
父亲沉默着,竟没有爆发。他已明白了一点:这多年来,儿子被他约束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奴隶。这比培养出一个废物更糟。我知道,成了精神奴隶的不仅仅是我。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严厉的父亲。他们的教育方式大多是拳头和棍子,他们是我们精神上的笼子。我无法打破这笼子,甚至连向前多走一步都十分困难,唉,我们真不幸。
我的一个朋友说,他们被时代压抑成了这个样子,照理,他们应该对下一代温情一点,可他们像机器生产零件一样,把那种压抑按到了我们身上。朋友说,父亲就是我们的笼子啊。我惊讶,却实在说不出什么。
父亲提出要带我去医院,说全面检查一下身体。我说我没病。父亲怒吼起来:不去也得去!我直面父亲,几乎也是吼了:不去就是不去!我敢直面父亲了,连我自己都感到惊奇。父亲这一次没有去摸茶杯,一脸颓丧。父亲的脸扭向一边,不敢正视我。我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打我姐姐,将我叫到一旁,看。我既惧怕看父亲的脸,又惧怕看姐姐不屈的脸。此刻,父亲惧怕看我的脸了。
但这绝不是我的胜利。我是失败者,父亲也是。父亲从教育我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失败了。
我对父亲说,我想到乡下廖老师家住一段时间。父亲用陌生的眼光看了我一会,点头同意了。
第二天,我请了假,一个人去了乡下。
我的失落和无望,父亲永远不可能明白,只好让朋友来为我解愁了。我坐在去乡下的汽车上,望着马路旁的野坟地,日头西斜。绿草深深的,那些七倒八歪的墓碑,文字已模糊,这里面一定隐着许多富贵荣华的故事,可现在,全掩在绿草深处了。所有曾经挣扎过的魂灵全化作了绿草,这不是哪个人做得了主的,但田陌间的烟火依然旺盛。人们活着也是有理由的,都知道人最终会化作绿草,却为那一点光亮而努力着。
来到乡下廖老师家。廖老师正上完课,在家看书。他除了喜欢收藏邮票、古董,还喜欢佛学。不过,他不像钟老师那样呷斋念佛。他安排我住下,然后,二个人来到校园外的田野,散心。田野的四面横着一脉山,山影淡淡的,一些闲云在此间飘来飘去的。山下有二棵树,松树,斜斜立着。我们走了十来分钟,才到山下。见到这二棵松树,我想起以前做过的一句诗:“为了独立你一生沉默,为了自由你一生独立。”树的境界,应该如此吧?反正,我绝不是一棵独立的树。以前,我认为一棵树必须结果才有意义。此刻觉得,做一棵独立的树就足够了,结不结果,真没什么。
时节正是初夏,万物竞相争俏,百虫欢叫。廖老师住二楼,开了窗,就可以看到田野、山,还有天空飞来飞去的鸟。这里的鸟真自由,飞得无拘无束。昨晚,我读了一则故事,大概也与佛学有关。一个人,挽弓欲射天空一只大雁,忽然,一个念头——念来很要命,他马上想到自己如果是大雁,别人要射怎么办?之后,他开悟了。我站在窗前,恍惚间,觉得自己也是一只鸟,虽没有人射我,但我是一只囚在笼子里的鸟。我高翔天空的青春年华已过去了,永不回来。这没什么,我喃喃念着:没什么,没什么。泪水悄然流了下来。也许,我生命中谈不上有苦难,可我的心灵上有苦难,这苦难又十分渺小,无人知晓。做为渺小的我,面对的是既看不到此岸又看不到彼岸的时间和宇宙。
在时间面前,我的心总是跳,没日没夜地跳。我的梦幻总在行走,没日没夜地行走。何处是岸?我的佛祖,我的菩萨呀,你们可是岸?
晚上,我不能入眠,廖老师就陪着我去田野里散步。我俩向西边的山下走,有几颗星光凝在夜空。来到松树下,他站在左边,我站在右边,像是来参加黑夜里的一个仪式。一颗幽蓝色的星子闪烁在松树旁。我凝眸着星子,猜测着它从茫茫夜间走到我身旁的来历,一片茫然。
宇宙时光中的万物都是有来历的,来来去去,匆匆忙忙,生生灭灭,朝朝息息,总沿着一种生命的轨迹,在闪动。这些生命,无所谓高低贵贱,只是大的自大,小的自小,优的自优,劣的自劣吧。我是小的,这又有什么要紧呢?假如有那么一股力量,将我一下推到夜空更深的地方去,也许我连自己的小都感觉不到了。
最小的原来是和最大的同时存在着,比方说小草与土地,小鸟与天空,星座与宇宙,它们互相变幻着,又互相依附着,既是最古老的起始,又是最年轻的梦。
我的佛祖,我的菩萨呀,你们不是岸,你们只是一条船,一座桥,供尘世间的人行走。
这之后的晚上,我俩就来到树下静立。我是一个缺乏慧根的人,不可能大悟,但这树下给了我一种十分寂定的安详。我仍旧看那颗星子。我心内万象丛生的杂乱突然间没有了,全被这一颗星子定住。定住这一刻,我仿佛从几生几世的梦中醒来,无语面对着自己寂寞的灵魂。
星光灿烂我心里,无语的灿烂。星子亮在最寂静的一角,像时光深处的一角冰山,美丽着,天地久矣,生命久矣,这一头到那一头,还有谁存在?
廖老师问我,你看到了什么?我说,看到了我自己。廖老师望着星子,点了点头。
廖老师三年前也遭遇了一件最痛苦的事情。他女儿六岁,聪明,乖。一天黄昏,他老婆带着女儿在校园内的一口塘边洗菜。洗完菜,他老婆走到家中忙了一会,再出来,女儿不见了,掉进了塘里,小生命夭折了。大概有两年时间,廖老师既不宽恕这个粗心的女人,又不宽恕自己,常常闹得家中不堪言表。他甚至认为老天是无情的魔君,不分善恶,可恨之极。他在田野里和山中乱走一气,唤着女儿的名字。他跑到南岳,想出家。他父亲追到南岳,费尽口舌把他劝了回来。
廖老师说,那段时间,我每晚来到这树下,整晚地发呆。
我能想像他当时的情形,那种心灵的创痛比我要深一些。佛家有云:人生无常,生命在无常面前,太匆匆,太容易消逝,可能连恋一恋的念头还没有产生,生命就过去了,永远地过去了。
钟老师教我观心,无非是启发我不执着于一念,天地无限宽,宇宙那么大,岂是一念能够主宰?即便我写一本还过得去的书出来,在古今中外的书山学海中间,不过一闪,就没了。我的问题不是出在写书上面,而是出在父亲和我的观念上面。
父亲他一方面希望我能干出点事,一方面又不相信我能够干出超乎他想像的事情。我的幻想,在他眼里成了不着边际的空想。而他的约束,在我的心里已成了笼子。
都是那么一念,我和父亲这二十几年来全被这一念捆住了。父亲说过,现实毕竟不是大平原,可他从不来点逆向思维,他的儿子真就是一条没有半分智慧的牛么?既然我这个生命来到这世界,一定有些来历吧。不结果,并不证明生命完全没有意义。这初夏的田野和山野全是旺盛的生命,有的结果,有的不结果,各有各的过程。生命是没有定数的,相对于天地宇宙,自由生长才是生命的灵魂。
星子不见了,留下混沌一片。
我今夜遇着的星,就是昨天的残梦么?我今夜遇着的星,就是明朝的希望么?
就让我自由生长好了,就像草或者树,在我应该绿的地方,绿着,就是此生的福了。
我从乡下回到城里,见了父母,再不说自己的事情,又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如今,我已到了不惑之年,偶尔想起那一场不是病的病,就会心一笑。
无声的天地,是埋葬一切梦幻的圣经。
责任编辑:远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