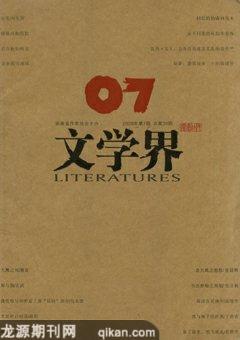仍然活在身边
森林伐木
在我生命里,奶奶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我时时感觉到这点,乃至在我写了很多关于我热爱母亲的诗文后生出一些内疚来,因为写到奶奶的诗文少而又少。奶奶给我的记忆异常清晰,有些几成烙印。
奶奶从我的生命开始后几乎没离开过我的身边,或者说我一直跟着奶奶。最久远能够记起的印象,应该是在伯父家后厢房一间很暗的房子里,奶奶给我起床穿衣服的模糊故事。那时我可能至多不会超过三岁。为了使这个最久远的模糊印象清晰,我在长大后便仔仔细细问过奶奶,我为什么会住到伯父家里去以至在黑暗的后厢房里站在床上,让奶奶一件又一件地给我穿衣服。奶奶进入老年后很喜欢我们打听关于过去的事,因为在奶奶的叙述里,她总能突出自己对我家建设及发展的重要性甚至不可或缺。奶奶告诉我,我父亲在下面公社任干部,常年难回家几次,母亲在大队任妇女主任兼企业负责人,忙得一天难见人影,奶奶便成了家里惟一能时时见到的主人。她不但要负起守护这个家庭的责任,还要为我们兄妹筹办一日三餐的饭菜。奶奶无怨无悔专心守护我家的态度,让距我家约七公里的乡下伯母起了嫉妒,经常地来我家提意见,我的奶奶于是心生愧疚。我的老家本是在伯父的家里,父亲出外工作,在我母亲娘家结婚建房,现在想来有点像入赘的性质。在伯父家里,奶奶本有一间完好的厢房,就是那间光线不是甚好的后厢房。奶奶既有了愧疚,便只好带着我回到伯父家里,便有了我残留的最久远的童年印象——奶奶帮我在床上穿一件又一件衣服的影子。可是奶奶在伯父家根本呆不下去,这除开伯父伯母当时很健壮挑起了家里家外一切事情不让奶奶插手外,就是奶奶在伯父家有客居的感觉,而在我家父母柴米油盐全交奶奶支配,生活全由奶奶做主,奶奶便有主人的感觉。基于这些理由,奶奶两个月后不顾伯父伯母的责怪,态度异常坚决地背着我回到了她时时牵挂的家里。
爷爷在我出世之前就匆匆去逝了,奶奶此后便坚持了她长达三十余年的守寡生涯。没有了爷爷关爱的奶奶在我记忆里非常坚强,独立自主生存下去的方法很是丰富,奶奶的勤劳我至今想来有点像机器运转般地不知辛苦。为了增加家里的收入,家里一般习惯性地养四头猪,一日三餐的饲喂便是奶奶每天必做的工作,每天从土里去打回青菜切碎,拌上红薯碎米一锅煮了,尔后用木桶盛了拌以潲水,很吃力地提了从厨房走向猪屋。为了节省力量,提着的木桶需在前面左右摆动,然后侧着身子高频率地迈动细碎的步子往前走。猪栏约有一米余高,奶奶紧咬牙根提上猪栏的高度,然后放在栏上,手扶着休息十多秒钟后提过猪栏,身子伏在栏上将猪食倒在猪食槽中。我现在还有点责怪父亲当时造猪栏设计的不合理,让奶奶平白地吃了如此多年的苦累。奶奶辛苦的不仅仅是喂饲猪的工作,对于我们兄妹三人的伺候更是吃苦,并且还要受气。有时我放中饭学回家,由于奶奶太忙饭菜还没办好,我担心下午上课迟到,便努力地使性对奶奶发脾气,她便一边用很快地速度洗锅烧火准备炒菜,一边伤心以至愤怒地骂我不知好歹,将她作佣人看,我还当不得猪娃子懂感情,在这样的咒骂里饭菜便端在了桌上。现在想起来,奶奶是家里的枢纽,是凝集家庭的灵魂,但这些在当时被我们全部忽视,在日复一日的日子流逝里,奶奶似乎成了理所当然的照顾我们的家庭妇女,根本没有从责任和感情角度去衡量她无私的奉献精神。
在我们兄妹三人中,奶奶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戴其实是一样的,但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奶奶对我要好些。奶奶有个大竹箱,里面放着她的被子和衣服,成年上着锁;另外还有个大木箱,里面的东西吸引了我整整一个童年,也是成年上着锁。我当时总是殷切关注奶奶到她房里去的时间,这时我便悄悄跟着奶奶身后进去,趁她打开大木箱时,我便伸出小手端开压着一个大瓷坛口的饭碗,瓷坛里面总是盛满了蛋糕、雪枣、动物饼干等各式各样的食品。我欺负奶奶的视线不好,但每次我抓着食品的手在往回缩时,奶奶便轻轻拍一下我的手说句你这个鬼子,好吃货,却也不追究。我便趁机跑出,将食品放在我的玻璃瓶里后,再次跑到奶奶面前要冰糖,奶奶说没有。我说有,在那玻璃瓶里面。奶奶不给,我便爬上奶奶的床,跑到大木箱前去抓玻璃瓶,因为较远整个身子差点都匍伏到箱子里去了,奶奶没法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脑袋后将我扶起,打开玻璃瓶盖拿一粒冰糖给我。这样的特权和耍赖只有我才拥有,兄长和姐姐几乎没有。
我家的成员,在奶奶眼里都如她的私有财产般宝贵,她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将这些财产置于她的羽翼之下。母亲在家里是奶奶惟一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虽然奶奶仍有传统的对媳妇排斥倾向,但母亲对她的尊重和信赖,早就化解了婆媳之间的任何隔阂。在母亲因病逝世时,奶奶悲痛异常,她哭嚎着呼唤母亲的名字,抚摸着母亲的身子,诉说着母亲生前对奶奶的爱护,说黄梅不落青梅落,奶奶祈告上苍让她代替母亲逝去,其悲情使得当时好多在场人众潸然泪下。
我们在奶奶的羽翼下长大,我结婚了,女儿也随即出生,奶奶便将对我们的爱逐渐转移到她曾孙女身上。奶奶在我的关注中渐渐老了,身子日益佝偻便更显矮小,满脸的皱纹和花白的头发,瘦弱的身子时时让我看着便有一种痛楚的感觉,但她仍能在我们外出时,将她的曾孙女抱在怀里,或摇着摇篮,痴痴地守着她心里聊以慰藉的希望逐渐长大。孩子长大了,懂事了,便也和她爸爸一样对奶奶的大木厢充满了好奇,奶奶便用她迟缓的动作打开她的百宝箱,拿出食品来满足我女儿的期盼。
1991年二月初九是个黑暗的日子,八十五岁的年龄使奶奶卧睡在床上,奶奶抓住我的手说志强,奶奶没有力气了,不能动了,要死了,不能管你们了,你们自己要保护好自己。我抚摸着奶奶瘦弱而冰凉的脸,喂她吃饭,可她无声地拒绝了。一切都无法挽留奶奶的生命,奶奶在我的面前永远的合上了她慈祥的眼睛。
对奶奶的回忆是漫长的,当新的生命出现,老的生命便悄然地为新的生命让出空间。当我在这个规律面前对奶奶逝世释然之时,便在奶奶逝世前后并没有过多的表现悲痛。可不知为什么在今天写这些文字时,我却一次又一次地流下眼泪,感觉在有奶奶的日子里我的幸福和快乐都与奶奶有关。奶奶离开我已有十七年之久,但至今她老人家的影像在我脑海栩栩如生,有时甚至如仍活在我身边似的。
责任编辑:远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