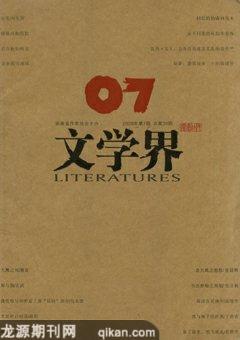黑是死后的灵(外二篇)
胡 玥
死就像旋舞一样轻灵。舞停下的时候,我躺下休息。四个黑色的影子抬着我走出屋子的一角。
街上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街道开始的时候挺宽的,只有四个影子抬着我向南走。后来,街道越来越窄,街道两侧的房屋越来越矮,而影子越来越高越来越长身躯也越来越庞大,我的世界四面都是影子,它们让我与从前我待过的世界完全隔绝了。
之后,影子们不再假装着在地上走,它们开始飘飞,飞使任何一个影子变幻莫测。我看见了影子在空中无限地拉长着自己,我再也分辨不出影子的头和尾,它们的身子,四个,融合成一个,薄、平、扁,软且姿态随意,我听见我说,放下我吧,我这么重,会拖你们的后腿。
我听见影子大笑,影子们说,人死后是没有重量的。
我说,我这是在死后吗?怎么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就像睡觉和做梦。
影子说,没错,生是一场梦,死是梦一场。不同的是,生跨越年,死跨越的是光年……
我们遁入光年,以光的速度飞?
你现在还不行,你被我们裹在胸腔里,是我们带着你飞!
我什么时候可以像你们一样飞?
当你已经忘了你是谁的时候,你自然就会飞了!
我想忘记是一个过程。我必是要走完这个过程才可以知道以后的事。所以我闭上眼,从此缄口。
我眠了有很久。我被影子放进一个小木匣子里静修。小木匣子是密封的,像树上的苹果那么大。但是,我在它的内部,却感觉天地足够大。阴影无处不在,许许多多的人都会沿着阴影走进我的领地,那些阴影在我的眼里是一道阴柔的光线,我喜欢阴影里出现的来来往往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只笑不说话,匆匆地赶地铁和公交车,我在从前忽略的许多的站名复又在这里一一清晰地被人报出来,我侧身躺在自己的阴影里,那是我自己发散出来的阴柔的光,我借着这一片阴柔还可以看到我自己。别人的阴影无法跟我的阴影交叉在一起,我之外,每一片阴影里都有一群人,阴影里有城廓、有街市、有铺面,有电车和人力车交错穿行,动物们随意在街上行走,不发出任何的叫声。有时,我发现我也紧随在他们的身后,跟着他们走到我从没有走过的地方。没有人认得我,我也不认得任何一个从前的旧人,我从前不喜欢动物,对动物们总是视而不见,可是,我越来越多地与动物们待在一起,谁也不嫌弃谁,我们找自己舒服的姿势躺着或是站立,看一个世界和一些人群消失,另有一个世界和一些人群又现,流水一样,没有重返眼前的人物、景象和事物……
渐渐地,什么都不再有,我身体里阴柔的光一点一点地退隐和消散,黑从我的身体向四周弥漫,我就是黑,黑就是我,黑的力量强大,没有什么可以包裹得住它,木头匣子被黑一点一点地咬碎,黑破黑而出,融进更广大的黑。
没有人能够在黑里分辨出黑。
黑是死后的灵,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有。
井的最深幽里有猫的一声叫
不长草的沙砬的旷野上,一口方形的井。
我在十步之外,看见青萍从地心的深处排着长长短短的队列飘浮上来,像伞兵在天空上的飘浮,不同的是,伞兵朝下边落,青萍是朝着上面不落。
一层又一层的青萍,它们聚在井口处,聚到足够厚积,聚到每一层和每一层都天衣合缝了,聚到已经无法再聚了,它们自身形成的一种合力使它们不得不从井口冒出去,有许许多多绿色的小天使从天衣的缝里爬出来,在弹性的空气里翻筋斗云……每一个小天使都有一个细细长长的尾巴,它们在空气里,就像小蝌蚪在水洼里。
一只小猫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趴在井沿儿上用花黑的爪子掬水喝。喝完了,它用掬水的爪子抓一把沙砂掷到井水里,它看水冒气泡玩儿。又抓一把,又掷,耳朵贴着井沿儿,听沙砂在水里走了多远了,沙砂们如泥牛入海,无声无息,猫就一把一把地扔沙砂,这时,井里的水似是忍无可忍了,它们突然地冒出井沿一头高,猫还没反应过来,水就将淘气猫一把抓到水里,将猫呛得几乎背过了气儿,然后,一把将猫甩离开井口,甩到很远。
除了水淋淋的那只猫,沙砂里没有掉落任何的一滴水。
我走到猫戏水的地方,朝着井里看了看,却看不到一滴水的存在。
猫从沙砂上爬起来,走到我的脚边,猫拱起身子,使劲地抖了抖身上的水,我惊异地发现那一粒一粒的水都各有一张变形的脸、还有短短的小手长长的尾巴,它们的小身子一挨到井沿儿就迅速沿着井壁钻进一根又一根不停地扩张不停地闭合着的脉管里。
猫不甘心,它沿着井壁往下追,进到脉管里的水粒子比猫跑得快,猫一时性急一生气一头就扑下去了……
我听见井的最深幽里有猫的一声叫。
天黑之后,一只狗踩着月亮的光影出现在井沿上。一只狗站在井沿上看看月亮又看看井底,然后对着井底一声接一声地吠。
井,仿佛是一口空井,它对一只狗吠不作任何的回应。
月亮转到井的正中间,我看见井的底端瓦明而又透蓝,月亮并没有印在那一片瓦明和透蓝里,在月亮的照耀里,那一片瓦明和透蓝,好像比这一面的天空还要深远。
月亮是突然离开井的。而且是说走就走,没有月亮照耀的井立即陷进一片漆黑。
狗的脑子还在明亮里,狗不明白漆黑是怎么来的。面对漆黑,狗脑子发生了断路,从此陷进漆黑里再也没有能回来。
它不记得从前它在哪儿,因何会站到一口井沿儿上,一只狗在一片漆黑里停止了吠叫。
一只狗失忆而且失声了。
我走过井,一条绿绿的绳子背着我自夜空悄悄溜到井里去,一只睡熟了的猫被提上来,一只狗跟着一条绳子走了。
我不能再回头。因为即使回头,我也看不见摆弄绳子的那只手是谁的,藏在哪儿。
暗夜中凝望一朵花的开放和枯萎
暗夜中凝望一朵花的开放和枯萎。一朵花躺在冰清玉洁里。冰体里的雾气一层一层地裹挟着一朵花。它的萼始终保持着冰冻里的绿和新鲜。花的子房因为冷的剌激一下一下地收缩着自己。在收缩与收缩之间,有一个小小的间隙,花朵在间隙里深呼一口气,然后再深吸一口气。
花朵在收缩和呼、吸之间渐渐地觉醒、渐渐地心智成熟……
花朵让自己的体温始终保持在摄氏零度。它使自己与冰体不分割也不完全相融。它在零度里与它周边的一切冰冷保持不即不离的尺度。尺度里暗含着生机。它在那个尺度之内梦着、舞蹈着……
梦和舞蹈,是花朵天分里的生长资质。它们的梦是舞蹈者的梦,它们的舞蹈是梦者的舞蹈。
若精灵的一对翅膀,谁也无法把花朵的梦和舞蹈分开来。
花朵的精气里含着的是阴阳二气。所以,花朵的梦中心,花朵的蕊里永远有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手牵手旋转着。它们天生丽质,天作之合。
两个小孩子,它们是两个人,它们也是一个。它们渴望长大,渴望羽化,一个化作另一个……
它们还是它们吗?
它们不是了。
它们有温湿的唇,温热的眼眸,唇与唇,眼眸与眼眸,在无限暧昧里合二为一了……
它们,使一朵花离经叛道……
一朵花在离经叛道里痛着、扭曲着、痉挛着……
它从本自冰清玉洁的根态的境缘里,欲态地旋浮,再旋浮……
我看见一朵花在旋浮里的开。
一朵花在旋浮里不得不开。
开是一朵花的死。
没有谁可以拒绝死。
当一朵花开了的时候,一朵花的灵魂已然出窍……
它看见一个女人正带着一个小孩走过那朵花,女人无视花朵的存在,女人只顾回首看管她的小孩子。她的小孩子径直向着那朵花奔去,他在花朵的蕊里找到两颗清泪,一颗里有男孩有女孩,另一颗里有女孩子也有男孩。小孩子既喜欢男孩子也喜欢女孩子……小孩子分不清男孩子和女孩子,他只是把它们当成了一模一样的两面镜子,他在一面镜子里看见的是自己还有自己喜欢的女孩子,他在另一面镜子里看见的是自己喜欢的女孩子还有自己……
小孩子怀抱着两面镜子离开了花朵……
一个男人走过花朵。他回首看了一眼,然后又回首看了一眼:他停下,转身回返到一朵花的面前。这是怎样的一朵花?面带微笑,心怀悲伤。
男人是懂得一朵花的。懂得一朵在爱与性里苦苦挣扎过的花是什么样子……
男人将这样的一朵花献于一个女人的时候,女人莫名地悲伤落泪。
女人并非是感动于男人的献花,女人是从那一朵花看见了她自己:短暂、暧昧、流离失所……
一朵花的最终是被一个男人的手摘下、握着,捧过,再递到一个女人的手里……
一朵花会经由一个女人的手被弃置荒野……
而男人和女人的孩子一天一天在长大。他从一面镜子里看到的是:男人是女人的分裂,他从另一面镜子里看到的是女人是男人的分裂……
两滴清泪,一把花魂。
没有爱,也没有性。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