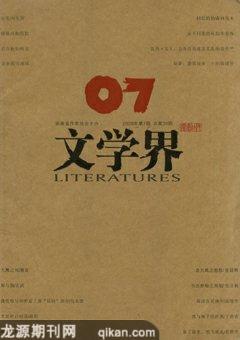我凭借写诗照看了那“活的”部分(外三篇)
马永波
在安妮生命的最后六个月中,她开始定期接受一位年轻牧师的宗教指导。那时,她的宗教探索似乎充满了一种她正在接近终点的感觉。然而,每当她想像这个终结的时候,它不是向上帝的一次转折,而是转向她所说的一位“神圣母亲”的怀抱。在她最后的诗歌中,有一首献给巴巴拉·施瓦茨的,在其中她把死亡想像成一次进入大海的散步:“我希望进入她像一个梦,/沉入我从未拥有的/伟大母亲的怀抱。”
1974年2月21日出版的《死亡日记》被安妮·塞克斯顿戏称为她的遗作。这本书的出版引来了众多个人出场的邀请,当年安妮出行的地方有马里兰、宾夕法尼亚、新泽西(三次)、纽约、康涅狄格、德克萨斯和缅因,并且在波士顿周边地区作了大量的朗诵。她最成功的一次朗诵是3月7日在哈佛文学俱乐部的那次,她的开场白显得含混而沉重,她说:“我愿意把这次朗诵献给一个无名的妇女。世界上存在着很多种类的爱——女人对男人,母亲对孩子,女人对女人,男人对男人,上帝对我们……”这些话仿佛是公开表示对女儿琳达先前拒绝去医院看望塞克斯顿的原谅之情。但是奇怪的是,相信这些话是针对自己的人不仅限于琳达一人,在安妮死后,巴巴拉·施瓦茨听到很多朋友对她说,“你记得安妮在桑德斯剧院的朗诵吗?那是献给我的……”
安妮·塞克斯顿于1974年10 月4日,星期五,结束了她的生命。自杀的日子和方式是经过慎重选择的。10月3日,星期四,她在GOUCHER 学院成功地举行了报酬颇丰的一次诗歌朗读,在波士顿大学按时上完了她的诗歌讲习班的课程。意外的是,全班学生都来机场接机。车子驶进波士顿的一路上,塞克斯顿都在讲述她如何应付她朗诵时穿的红色长裙的纽扣,它们好像随时会从上到下地裂开。她的话让学生们乐不可支。
第二天早晨,路易斯·科南来与她一起吃早餐,在呷咖啡的时候,塞克斯顿时时中断话头,注视着在窗边喂食器里吃食的山雀,它们总是能让她愉快。十点她去坎布里奇,赴她和巴巴拉·施瓦茨例行的约会。她和路易斯温柔地告别。
在她的皮夹里她放了新诗《绿房间》的抄本,是写给施瓦茨的。10月4日是一个重要的周年纪念日:她们九个月前的今天第一次约会。塞克斯顿感激母亲般的施瓦茨在那九个月中毫不吝啬的给与她的一切:“女士,海的女士/在你的子宫中我的心跳动如一个瘾君子。”那个早晨塞克斯顿如此沉静,以至施瓦茨没有直觉到那就是告别,但在她走后,施瓦茨发现了她的香烟和打火机塞在她办公室的菊花后面,她开始有所领会。这个姿态似乎大有深意,因为安妮没有了香烟就不能思考。
塞克斯顿与玛克辛·库明约好中午一起吃饭;她们要修改计划1975年3月出版的《朝向上帝的可怕航行》的校样。她给库明看了《绿房间》。“我们在一起吃了一顿傻呵呵、快活的午餐,我记得自己曾经想,她的状态显得多么好啊,”库明回忆道。一点半,她们修改完了校样。库明那天下午得去取护照,她不久要和丈夫一起去欧洲、以色列和伊朗做长途旅行。她知道安妮害怕她离开,她的出发日期是在安妮的生日之前,每当生日的时候安妮总是需要支持。“是的,她非常需要,”库明后来说。“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被她操纵了。我想我是太爱她了,以至不会有任何被操纵的感觉。有些时候我感觉到她的需要带给我的压力,但是你知道,安妮的付出和她的索取是一样多的。她极其慷慨,付出,可爱。当她准备自杀的时候,她一直保守着这个深沉黑暗的秘密。”库明陪她走到车前,看着她开走。塞克斯顿摇下车窗,喊了几句什么,但是库明没有怎么听清楚。一个最为深思熟虑的告别。
穿过美丽的小阳春天气,安妮驱车回家,树木已经呈现出她常常形容的酸味水果硬糖的颜色。宽敞通风的厨房里一派宁静,她又倒了一杯伏特加,一边打电话订晚上的约会,改变会面时间。此外她似乎没有和任何人说话,也没有写下任何的字条。
她退下手上的戒指,把它们丢在自己的大钱包里,从衣柜里取出母亲的旧毛皮大衣。尽管那是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空气里依然有一种寒意。磨损的绸衬里一定很快地让她的身体暖和起来;死亡将像是一次拥抱,像是在熟悉的怀抱里沉入睡眠。安妮曾经对人说,每次穿上母亲的这件毛皮衣服,她都感觉自己和母亲一样,只是母亲的身材很小,而她却很高大。手里端着新倒的伏特加,塞克斯顿走进车库,把门在身后关上。她爬进她的红色老美洲狮的驾驶座,车是1967年买的,那一年她开始当大学老师。她将车发动,并打开了无线电。
1961年,她曾对心理医生说,“你瞧,我凭借写诗照看了那‘活的部分。”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南京正笼罩在连绵的秋雨之中,仿佛整个江南都在一滴雨中沉没了。那古人所说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即便躲在历史的黄卷中也难逃这烟雨蒙蒙的笼罩。看不到楼台,只有灰色沉闷的高楼,无声的梧桐树周围隐约的黄色灯影。这样的雨让你醒来,却仿佛醒在另一场梦中。屋子里冷得空气似乎都凝固了,我缩在卧室里,关上门,灯在中午就打开了,我也穿上了冬天的衣服。几乎一整天我都把自己裹在两层的棉被中,昏沉沉地,似乎晨昏是一把卷起来的皮尺,连在了一起。傍晚起来,试图弄清楚安妮死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清楚了吗?没有。
安妮曾在回答一份调查中说,感觉自己只能做婊子,让男人感受自己强大的性能量。黑塞在很早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如果做不成诗人就什么都不是。诗人和婊子,看似多么遥远。诗歌,使安妮从一个不能胜任任何社会自我的人成为一个出色的大学教师和著名的明星般的诗人,却终究没有改变命运的指向。我们无法置身于安妮所感受的世界中,我们无法理解她,因为我们和她,根本是在不同的寂静之中。
寒冷还在继续加深。时间催迫着所有的生命。要不了多久,仿佛同时接到命令的士兵,树叶将在一夜间奔赴大地的坟场,万物光秃秃明晃晃地进入几何学的寒冬。
我想起安妮自杀那年的3月7日朗诵会的招贴,身材高挑美如模特的安妮坐在那里,双腿以瑜伽姿势柔软地交叉着,白色的鞋子,黑白花的连衣长裙,微笑着张开双手。招贴上的文字是:Hurry up please/its time
时间突然如白雪涌上来
今天,我坐在这里,我还坐在这里,这意味着窗外景色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所处的这个微渺的位置,伟大的蓝色依然笼罩在万物之上,像一个不变的微笑。如果没有事物形相的变易,我们将感觉不到时间,尽管时间依然在钟表上以精确的刻度存在,但这种与我们主观体验分离的物理时间将是无时间性的,也就是没有意义的。
时间是变化,是运动。时间与季节的变换取得了方向上的一致,于是,从秋天起,落叶的声音将在深夜里铿锵,我们的内心将在自身与外物自然性上的契合中颤抖,期待而颤抖。在秋天金黄的衰败与冬天的荒凉之间,是一片似乎无人涉足的滩涂,我们等待一场雪落下,落下填充这一片渐呈灰色的荒芜。现在,雪已经站住了,站在万物之中,因此我们爱她。
但是时间依然没有被遗忘,因此我们还在继续变老,尽管在宇宙的剧场里我还坐在这个靠窗的位置前,我面对的方向还是同一的方向,但是桌子上的灰尘越来越多了,它们在我体内堆积起来,它们告诉我:万物的内部都是灰尘,万物只有表面是光滑的,其实早已像一个柜橱,被蛾子蛀空了,夏天曾挂满美丽飘逸的衣裳。时间的脚步偶尔还会在寂静午夜的小闹钟上数着我们的白发。
时间既不可遗忘,又不可逆转,它像一支射出的箭,提前把我们钉在未来这棵老树上。似乎这个透明的牢狱再无法坐穿了,所有的犯人早已消失不见。时间的开始也就是历史的开始,历史是变迁的遗迹。历史终结之处,时间才不复存在。自从基督在沙漠经受四十天的魔诱,撒旦就开始在我们人类历史上做手脚,因此,人类的历史只能是罪恶的血腥史。时间以其种种变换的方式侵蚀着我们,使用、磨损着我们,它设立一个界限,甚至使邻近的街道成为我们的禁区,它让我们书架上的书积攒灰尘,让我们伸进去的鼻子发出响亮的呼声。有些门关上再也无法打开,有些书我们从未翻开,也永不会翻开。
于是我们沉醉,醉于爱情,我们抓住爱情的衣角,像孩子一样彼此紧抓住对方的肉体,以为在时间的汹涌海洋上,那是一块坚固可靠的石头,我们可以依附在上面,等待远方的船帆。我们把头埋在彼此的怀抱里,以为风暴从此消失,我们互相许诺永恒。而时间,在暗中嘲笑着爱情,松动着爱情的基础。爱情也在流逝。我们谁也救不了谁。于是我们转而寄托于物,沉醉在美酒之中,或是徜徉林下,泛舟五湖,恍然而醉,怃然而醒,在俯仰自如中体会万物之中那飘渺而不绝的浩然之气,我们试图在万物光滑的面目上印下我们的影子,正如童年我们在夏天炎热的草丛,趴在清凉的井口,我们在看到发暗的深处的井水的同时,也必定看到了我们自己微微荡漾的影子。于是,我们投下一片草叶或一枚手心捂热的卵石,搅乱那影象,然后跑开,又去阳光晒裂的葡萄架下玩耍了。而游戏也在流逝,变得没有趣味。在我们看到邻家姐姐在阴影中亲吻,童年结束了,万物开始与我们分离,我们需得等待什么来再次使我们与万物合一。
意识越是发达的生物,与事物的距离就越大。看,那些安详的动物,从幽暗的森林中漫步走出,仿佛随身携带着整座森林的幽暗气息,它们在阳光下并不与它们所来自的背景分离。它们将存在携带在体内。它们的宁静散发着永恒的气息。所以叶芝才说,“一只垂死的动物既无期望也无恐惧”(《死亡》),而人在等待结束时却在惧怕着一切。因为人已经与存在分离,他在万物中的冒险毫无保护,他反不如动物来得安全。一个刚刚逃脱了死亡的动物,马上就又去吃草游戏,好像马上就遗忘了刚才的奔逃与追逐。它们安于生命和死亡。只有人在惧怕,甚至在死亡尚未来临之前。可是等等,叶芝接着告诉我们,也只有人许多次死去又重新站起,因为他从骨子里了解死亡,因为死亡本是人之创造。也就是说,只有人能真正地死去和真正地永生。
如果没有对时间的意识,衰老将不会开始,但智慧也不会开始,这同样是叶芝教导我们的。古人云,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也是一种智慧,遗忘的智慧,沉醉的智慧。但是否需要进一步追问,自己所沉醉的东西是不是也处于无所不在、漫溢的“逝性”之中?是否在沉醉后的清醒中,星星从醉后的头痛中更清晰地显示出上帝的永恒时间与我们受造物的短暂时间的分别?汉民族历来缺少对终极问题的追问,他们满足于抓住可以抓得住的有形可见之事物,把一生消磨在不无欢乐的局限范围之内。他们颇有些像恋爱中的人,彼此抓住,在人际之间建立起一种貌似恒久的东西,他们的目光从不超出在这人际(社会的基础)之间建立功业以求永恒的态度和意识。而人类所造一切,终归是一场空无。因此,我们对他人的意见格外重视,我们的目光是平的,我们看不到这一切之上笼罩着的天空永恒的蓝色,对我们来说,那不是许诺的微笑,而仅仅是空气和空无。
时间出现在意识之中,最令我们震惊的是在童年,它把我们自身与万物分离,使我们对生命有了认识,对死亡有了认识,尽管是模糊的。我们感觉到分离、撕扯的痛苦。我们的一生都是试图重新回到童年时与万物的亲密温暖的关联。那时,每一棵树、每一座房屋、每一个角落、每一场雨,都是我们人性的刻度,万物如容器,充满了我们的体温。可是突然,我们发觉物就是物,我们的目光无法穿透其光滑封闭的表面。物和我们无关。我们孤零零从万物中站出,站到虚无之中。恐惧由此开始。成年后,我们用在社会上安身立命来遗忘这种断裂,我们彼此安慰,我们用所谓“事业”来遗忘自身。然而,时间如水滴,在午夜我们意识松懈的时刻,滴答地提醒着人生的残酷和生命的短暂。时间给我们生存的完整性滴出了裂痕。遗忘再次成为不可能。我们在透明的牢狱里转着圈子。在我们经历太少的人生中,时间以厌倦的主题进入我们的意识,我们仿佛从来没有活过,生活仿佛从来没有开始。作为经历某个事物的先决条件的时间本身成为意识的内容,经验的匮乏使我们经验这个经验的方式突显出来。这就是自反意识,返观自照。后现代文学中经常出现的元意识,譬如将写作时对写作本身的意识纳入内容,就来自这种真正内容的匮乏,后现代文学也因此成为走向沉默和匮乏的文学。
在常人沉醉于遗忘时间的共在状态中时,总有一些不甘的灵魂在意识到自身和万物俱在流逝中挺身反抗时间对意义价值的毁灭,在矢石交攻中站出自身,把自己像一块石头投出,然后又走到石头落地之处。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鼓吹的向死而生的谋划。叶芝在拜占廷的艺术中找到了永恒,他希望自己成为枝头上歌唱的金鸟,也就是说,他认为只有在艺术创造中人才能永恒。其实这么想的远不止他一个,几乎所有的伟大人物,最终都是在这种创造性行为中追求永恒的踪迹。艾略特把他的永恒奠基在《四个四重奏》之上,他认为虽然我们有限的直接经验不能把握绝对真理,但也只有通过它们,努力使我们的知识完整,才能接近流逝时间中永恒的静止点,重新返回果子永远新鲜的伊甸园。普鲁斯特认为可以用感觉的方式从物中将失去的生命拯救出来,他认为失去的时间寄寓在物质对象之中,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记忆将其释放出来,重新在复活的往事中辨认出自己的容貌,从而摆脱物质的牵缠累赘。里尔克则认为,可见之物只有转化为内心的不可见之物,方才得以永存,在内心中建立起更伟大的廊柱和雕像。于是他说:“群山安息着,星光使群山壮丽无比,然而群山中也闪烁着时光。呵,无家可归的永恒性,夜宿在我野性的心房。”
然而,能够实践创造性行为并将时间凝定在成果之中的人多么寥寥可数,那么,我们这些庸庸凡人当如何自处?这些伟大人物没有明确地给出答复。我们依然悬在深渊之上。对此,我亦无力给出答案。也许皈依宗教,将一切交托给主,是惟一的指望吧。艾略特和奥登最后皈依了,他们肯定也是认为,仅仅依靠创造性的劳动,还不足以战胜时间。他们对人的有限性有着最为谦卑的认识,这是终极的智慧。获救的人永远不会是全部。在我们来说,努力追求知识是一条道路,这是奥古斯丁的方法,通过对知识的追求接近上帝,虽然这些知识不会是永恒的知识,但却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接近上帝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绝不是物理学、文学所给出的局限的实用知识,而是在心灵中伸展开记忆与期望,使“现在”延长成为永恒的现在,使之成为与上帝的永恒的暂时的交汇点。
为第一根白发而吃惊地哭泣,为事物的变迁而吃惊地哭泣,为欢宴易散而暗暗难过,我想这是好的,这总胜过遗忘时间的自欺,这是智慧的开端,虽然我难以给出逃脱时间的切实可行的办法。而智慧总是不断趋近的智慧,不会是一个终点,不会是一次性的解决。就在路途中,我们接近了群山中闪耀的星光,现在它混在白雪冰冷的纯洁之中;同样在路途中,我们接近了自己的内心,我们不再觉得这个沉重的肉身隔在万物与内心之间,我们渐渐轻盈了,我们渐渐由肉体展开为灵魂。我知道人本是无可安慰的,因为我们是分离的独立的个体,我们不再血肉交融。我惟一能做的就是,当你们在黑暗中犹豫的时候,能摸到一双温暖的手,我们彼此看不见,我们却能听到旁边有脚步响在同一个方向上。
他人之死
当死亡不再是发生在你之外的远处的事件时,你本己的死亡像一颗始终含在嘴里舍不得融化的糖果,开始把甜蜜渗透开来,因为你像个孩子把它含得太久太久,以至你已经忘记了它,而遗忘意味着不在,死亡与我们无关。我们总是倾向于把本来属于自己一部分的陌生的东西外化成我们之外的某物,为之命名,从而也将其与我们自己对立起来。如果死亡仅仅是外部的一个确定事件,是从外面伸来的一支剪断命运线的女神之手,死就和我们无关——因为作为生的一个透明的界限,当此在有生之时,死就像一个不断退远的地平线,生之旅人只可无限趋近而不可跨越。而当此在死亡之后,此在之生业已不复存在。此在只有在死亡中才可以明了死和体验死。此在何时死去?生理学生物学的确定只具有测不准性。再加上灵魂的说法,事情就越发地复杂难解了。
只有生才可以死去。从死者广大而幽暗的国度尚没有人带回来消息,因此,以死来探测死之秘密,永远是一种哑默的虚妄的冲动。那不加解释的文化型自杀者,全都没能回来向我们讲述另一种存在的光景。死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我们终有一死,但何时死,没人能够预测。如果死不是一个可以无限退缩的界限,而就是包含在生之中,是使生完整的没有被照亮的另一面,生和死将是可以转化的,正有如果实里包藏着的绿色的种子。而如果种子不死,就不可能有果实的收获。死亡的不可让渡性造就了责任,因此也创造了人的尊严。你看,每一个迎面走来的最卑微的人,都仿佛心怀一个温暖的秘密,在他褴褛的外表下悄悄孕育着。死使生成为不可重复,使生成为一件严肃的事情。死亡是需要独自担当的人生最后的责任。
美国诗人罗伯特·派克曾在《船》一诗中触及到了死亡的神秘。诗中写了父子两人,儿子替父亲穿上航海服,父亲问儿子水流向哪里。“流向大海!”父亲跳上船赶上风头,白鸟像旗帜一样折磨着他灰色的双眼。这时儿子着急了,他呼唤父亲回来:“你不知道你会发现什么!”父亲操着舵驶远了,船后的波浪盲目地颤动,一个绊着一个。风暴平息后,父亲死了。他的灵魂俯视着儿子,儿子问,“父亲,你死时发生了什么?”父亲告诉他所有的水流向哪里,并平静地为他穿上衣服。送父亲赴死之约时,儿子自信水流向大海,而当父亲探询过死亡的秘密之后,该由他来告诉儿子水真正流向了哪里,除此再无言语。
如果说在现代社会,乐生畏死的文化刻意将死亡的真相掩藏起来,把它看作新闻中的灾难和暴力事件,或是托付给医院、养老院和殡葬服务机构,并且我们往往强调死亡的偶然起因,如疾病、意外、年迈等等,这意味着我们希望把死的必然性降低为偶然性。然而,亲人之死在某种程度上对此作出了补偿,它以震惊的方式将死渗透进我们内部,使我们在自己的必死性面前深深地垂下头来。葬礼上的哭泣多是哭泣我们生者的这种命运的确然。我们大可以将人生譬喻为一场这样的葬礼,我们每个人胸前都抱着自己的遗像,而通往墓地的路很长,于是有人就在路边坐下来,有人聚在一起打起了纸牌。亲人之死不再是他人之死的遥远和外在,它让孤独成了我们的邻居,让家中的一个房间始终黑着。
我所读过的最为感人的有关亲人之死的文字,当属黑塞。他在散文《纪念品》中写到了亲人之死使兄弟姐妹更加亲近地联合在一起。是死者使生者重归于好——“我们谈了很多,谁若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父亲的一些特别的小故事,谁就把它们复述一遍,这其间我们还阅读了父亲笔记中的一些片断。我们中不时有人从墙上到处挂着的家庭照片中拿下一桢来加以研究,寻找照片背后的拍摄日期。我们中不时有人不见了,到‘那边去和父亲待一忽儿,我们中不时有人失声哭泣。我的一个妹妹比其他所有的人‘不见的次数都多,父亲的死对她是一个命运的转折点,连她的表面生活也要改变了。我们其他人便围着她,把她置于我们的爱抚中间。”
亲人之死使有些人从此畏惧死亡,或是更加严重地回避死亡,而对于有智者,亲人之死恰恰使他从此不再有所畏惧,正如黑塞所言,因为“直到这时我才完全看到它的真实性和伟大性,它好似我们面前的相对极,它期待我们去完成自己的命运,完成一个生命的圆圈……当我哭泣着吻他的双手,把自己温暖的充满活力的手搁在他那冰冷的额头上时,脑子里倏的一下涌现出了我的童年时代。严冬时,每当孩子们双手冻得冰冷回到家里,父亲总是要我们把小手在他脑门上搁一忽儿,因为他经常整日受剧烈头痛的折磨;而现在我把自己不安和温热的手放在他额上,是汲取他带给我的寒冷。”
1997年春天,母亲因脑溢血猝然离世,也因此面容一如生前,我曾单独在那个冰冷的房间里和她呆了一小会儿,摸了摸她依然有弹性的脸。
对惠特曼的新驳斥
最近撰写为百花文艺出版社主编的“美国生态散文译丛”总序,在整理惠特曼相关资料时发现,这位大诗人在1855年版《草叶集》的序文里曾经写道:“在所有人类之中,伟大的诗人是心气平和的人。”这种心气平和有利于摆正人与环境(与他者、社会、自然)的关系,使人获得“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谦卑态度,从而将佛教中的因陀罗网予以肉身化。万物有如宝珠结成的网,一颗一颗互相辉映,重重叠叠,无穷无尽,组成一个整体,人作为整体的一个环节也都被包含在因陀罗网中,他与万物是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的。
然而,在文艺创作中,这种“心平气和”容易被错误地消解到心满意足、安于现状、见惯不惊、心态平衡、自身具足乃至自给自足等等庸俗层面。这种自身具足实质上不但对创造性行为不利,也是不符合生态文化的根本思想的。
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里戈津在《从混沌到有序》一书中提出了系统的自组织原理,大意为世界万物都是系统的存在,每一存在都是相对稳定的开放系统,一方面它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与其他事物相互作用,从环境中获得物质、能量、信息,维护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系统又有自身的内在结构,是由不同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在稳定的封闭系统和接近平衡的系统中,小的输入产生小的结果。而在非线性关系占支配地位的非平衡系统中,小的输入却有可能产生大的结果。在远离平衡的状态下,非常小的扰动或涨落,可以被放大成巨大的破坏结构的波澜。而这就带来了一切种类的本质的变化过程或革命的变化过程。
文艺创作也可以看成是一个这样的自组织系统,其中人的心理状态和其他要素一样,对系统的有序进化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一个心态平和的人可以是视一切不平等不合理不正常为“正常”的人,是欲望被删削到水平面的人,是对一切都近乎麻木、丧失了敏锐判断力的人,也是一个不再积极进取而满足于消极守成的人。这样的人是不事发现的人,在他来看,“太阳下面没啥新鲜事”。这种“心态平和”是对既定秩序和资源分配的默认,带有一种油滑世故的腔调,只要对自己有利,别的都可以视而不见、高高挂起。在认识论立场上是属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压迫者和既得利益者之列。
在维系与他者、社会的关系方面看,这样的心态是值得提倡的,遏制过度膨胀的自我私己的欲望,能对系统的整体性目的和个体的主体性目的的协调有益。但是,这样的心态对文艺创作却无疑是一种动因上的剥夺。弗洛依德不是早将人的创造能力与心理能量(力比多)联系在一起了吗?
卡夫卡如果没有因为早年被父亲忽略造成的心理紧张到了成年乃至临终也难以消除,他不可能一生保持那么清醒敏锐的洞察力,他不可能以其全部的写作来寻求那把砍断世界之根的斧子。同样,置身于巨大的矛盾冲突中的兰波,强调“诗人要长期地、广泛地、有意识地使自己的全部官能处于反常的状态,以培养自己的幻觉能力,各种形式的爱情、痛苦和疯狂;寻找他自己,在自身耗尽一切毒物,以求吸取它们的精华”,这样才能获得超常的感觉能力,看到常人感觉不到的事物,从而为“未知的发现宣告新的形式”。这种“新的形式”也就是上文提到的“革命的变化”。就拿惠特曼本人来说,他如果没有经过早年坎坷的经历,没有克服晚年瘫痪折磨的痛苦,他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心平气和”。正如没有经过异化的美不是真正的美一样,没有经过苦难磨砺的人生,也不是真正的人生。经历过矛盾斗争之后达到的统一和谐,方能造就伟大的人格和伟大的艺术。当歌德在《流浪者之夜歌》中说“一切的峰顶/沉静”的时候,他已经是完成了这种“伟大的调和”。
责任编辑:远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