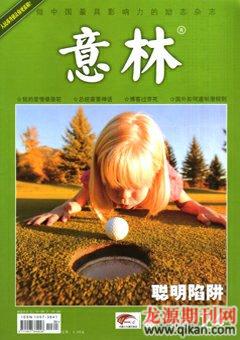一次越洋电话
柳鸣九
儿子在美国英年早逝,撇下了他年轻的妻子与幼小的女儿。那远隔重洋的小孙女实在让他牵肠挂肚,他一直担心一个仅四岁多的小女孩在心理上如何承受这次沉痛的打击。
这一次是悲痛事件后第一次与小孙女通话,他想小心翼翼地避开事件本身却又对小孙女能起到一点安慰的作用,他用小孩能懂的最直白的语言对小孙女说:“你是爷爷最疼爱的小孙女,在这个世界上,爷爷最疼爱的人就是你。”“你最疼爱的是我爸。”小孙女的回答使老祖父心里不禁一揪。他有意识离开悲伤的事远一些,没有想到这个4岁刚出头的小女孩却主动地直触伤痛。她的这一认定是来自她自己的观察?从小远在美国,她实在没有见过几次老祖父与自己父亲相处的情况。是曾经偶尔听她的父亲母亲讲过这个话题?那她的记忆力与人生理解力可就有点使人惊奇了。是她自己为了要讲一句安慰自己那可怜的父亲亡灵的话?怀念他的话?不论怎样,她需要主动地跟电话里的这个老人谈一谈她自己的父亲,因此,她主动触及伤痛,或者是因为,她仍无法摆脱伤痛的阴影……
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有些伤感,有些无奈,有些想要为自己找到一点慰藉:“……他不在了,我见不着他了,他去了天堂……”
话语很简单,但其中的意蕴、内涵、感情以至哲理却像一大股水波向他猛然扑来,使他应接不暇,他迟疑一会儿,好不容易才答上一句:“他在天堂里会保佑你……”
这是年已古稀的他,生平第一次用非无神论的语言说话……
老夫人从美国探亲回京,交给老先生一个纸封,说:“这是小孙女要我带给爷爷的一封信。”老祖父赶快把手头的事都放在一边,急不可待地想打开纸封看看信里是什么内容。那纸封是用一张稍为厚实点的绛色纸折叠而成的,马马虎虎呈一荷包形,一看就是一双笨拙小手折出来的。可是,要打开它可很不容易,折叠处贴了胶条,胶条也是胡乱剪切出来的,很不整齐,粘得更是歪歪斜斜,操作的那双小手显然是生平第一次做这样的手工活,但在折叠处的下方却用另一种颜色笔署了一个名字“EMMA”,字母大大的,清晰突出,特别醒目,那是发信者的芳名。
老祖父惟恐把纸封撕坏,只能细心地去拆除那封口的胶条,但它偏偏粘得特别严实。愈难拆开,老祖父好奇心愈加急切:“粘这么牢,小丫头写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她写了些什么,她没有告诉我们。”老夫人解释说。他终于把胶条拆除,打开了纸封,里面果然有一张小纸片,看来,这便是小孙女给老祖父的重要信函了。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小纸片又是折叠着并用胶条粘贴在绛色的封纸上,虽然又是歪歪斜斜的,但可以看得出来,那位5岁的发信者是极其郑重其事的,老祖父只得又耐心地拆胶条……
最后,终于大功告成,老祖父打开了折叠着的那个小纸片,那上面有拙拙的笔迹,写着这样一句英文:WE LOVE GOD(我们爱主)。而且,取下那张纸片,发现那张绛色封纸的内面,也写着同样的这句话,这就是小孙女给老祖父的家信的全部内容。
老祖父本来猜测这封信是小孙女玩的捉迷藏的游戏,没有想到是这样的内容,一时把老祖父又震撼得半天也平静不下来。眼前这封很特别的信函,正是悲痛事件后母女俩特定精神历程的一个投影,它清楚地显示出这个精神历程是深沉的,而且似乎将是悠久的,无尽期的……
老祖父把信函的内容告诉老伴,老太太也没有想到是这么一句话。她回忆起在美国所见到的小孙女的生活:在其母的带领下,她养成了饭前祷告的习惯:对着桌上食物,她两只胖乎乎的小手合掌,眼睛认真地闭上,嘴里念念有词,遇上她童心轻快的时候,还补充一句:“正好我现在饿了。”
老唯物主义者闻此讯后,久久难以平静……
(冯国伟摘自《文汇报》2008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