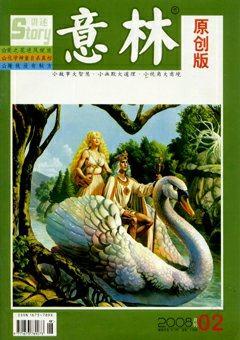念珠之恋
永井隆
译/零 零
在大学工作的第三年,我结婚了。当时助教的月工资是四百日圆。满洲事变期间物价很便宜,尽管如此,四百日圆也很难维持一家人一个月的生计,生活变得很清苦。但是从未听到妻子在我面前有过一丝埋怨,更没添置过一件新衣。即便是外出游玩,也仅是一年有一天在海边度过。我每天工作到深夜才从研究室回家,所有的家事由妻子操持。每月四百日圆的生活,持续了七年。
因为开始着手一项新的研究,我的人生被彻底颠覆。我没有时间去理会除研究以外的其他事情,话也很少说,甚至已经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孩子在旁边哭闹也只是瞪一眼就完事。说了什么,吃了什么,做了什么我毫无意识。从大学回来的路上曾两次遇见妻子,但因为没看见,两次都与她擦身而过。后来妻子说起的时候我无言。在丈夫形同虚设的情况下,妻子用她纤细的手腕儿支撑着整个家庭。
作为对妻子辛苦付出的回报,我只能不断地把自己的论文通过杂志面向众人。对于那些杂志,妻子总是整齐地把它们整理好,然后恭恭敬敬地翻看每页。偶尔,在翻看的同时,眼泪会不自觉地从她眼里流出。站在旁边的我替妻子抱着小儿子,心久久地沉浸在温泉般的暖流里。
我们一家最幸福的时候莫过于星期天的早晨。到了那一天,大家便一起前往天主教堂。我拉着大儿子,妻子拉着小儿子,朝山丘那边红色的天主教堂走去。远远地就能听到教堂传来的清幽的钟声。透过彩色的玻璃,还能看到朝霞绚丽的色彩。我的声音,妻子的声音和孩子们的声音汇在一起,似乎听到了来自天堂的赞美。但这样幸福的日子再也不回来了。
我升为副教授后月工资涨了一百日圆。妻子终于松了一口气。不久后儿子上小学了,四十圆的学费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困难。
就这样过了五年。我因为长期致力于研究室的工作,受到了放射性物质的影响患上了白血病,通过诊断得知剩下的日子不过几年。我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妻子,并和她商量好后期的计划。妻子知道实情后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和我预想的一样。这反而让我很高兴。我的研究也最终在埋头苦干中完成了。妻子也自始至终地对我付出着她全部的情感。病情意料之内地恶化,妻子曾不止一次地背着我到大学上班。
八月八日的早上,妻子和往常一样笑着目送我去上班。我刚走了几步,突然发现便当落在家里了,回去的时候竟看到她在哭泣。
这该是我和妻子的永别了。那个夜里我依旧在教研室里度过。第二天,也就是八月九日。原子弹在我们的头顶爆炸。我也因此受伤了,脑子里一下子想起妻子那张脸。虽然受伤,但還是忙着给重伤者提供救助。
第三天。傍晚的时候我终于回到家里。房子已经化为一片灰烬,我努力地寻找着,终于在厨房里找到了一个黑色的块状物体,旁边残留着一串十字架念珠的链条。
我把妻子放进一只桶内,她甚至还是温热的。我就这么抱着她朝墓碑走去,周围横尸遍野。夕阳照在地上,同样的黑色斑点清晰可见。我以为抱着我的骨灰走上这条路的会是妻子,没想到现在是我。命运总是那么会捉弄人。我的怀里竟然传出妻子干巴巴的声音,我听到了: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图/陈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