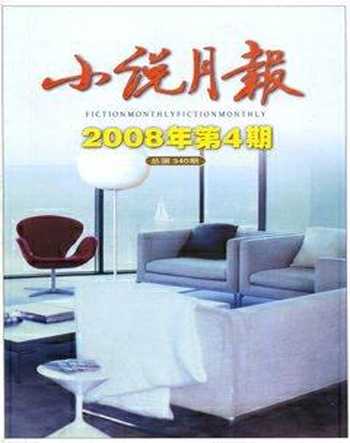人面桃花
艾 玛
1
下了一段时间的雨,往河边去的小路被野草吞没了。锯齿草、香泽兰、野葛藤和黄荆条遍地横生,根本看不出哪里是路。人几天没走,这些贱贱的草啊藤啊就迅速占领了一切可占领的地方。
“就是这里吗?”涔水镇派出所的所長王坪大把警服的领口扯开了,脱下帽子抡着扇。虽只到四月天,因为路不好走,又是下坡,走得都有些热了。
“可不就是这里。那天她也来洗衣服……”说话的女人叫桔子,是镇上崔记米粉店的媳妇,一年前从太青山里嫁到小镇上。桔子拨开众人走上前去,很灵巧地跳到河边的一块大青石上。因为连日的雨,大半块石头都浸到了水里。天气好的时候,一镇的姑娘媳妇都在大青石上淘衣浆衫。过年过节,来淘洗宰杀好的鸡鸭,把不要的下水扔进河里喂鱼。大家说长道短,泼水打闹,往往使得这里热闹异常。
镇上不见了一个女人,叫小美,是浅水湾足疗店的服务员。为了节省自来水费,洗脚店的毛巾都是由服务员拿到河里漂洗。那天轮到小美,去了半天都没有回来,找过去一看,满满一柳条筐毛巾扔在河边的艾蒿丛里。老板黄咬银来报案时,手里还拎着从河边捡回来的小美的一只高跟拖鞋。派出所查了查,发现桔子是最后一个见到她的人。
“她跟你说什么没?”
“我不屑理她!我洗完衣服走的时候,她还蹲在这里发痴。”桔子的话引起了围观者的一阵哄笑。
很快有人证明桔子说的不假。倒闭了的镇机械厂的工人王宝林的娘在河边的高地上开了块麻将桌大小的菜地,碰巧那天她在地里栽辣椒秧,歇息时看见有个红色的影子往坡上移,而青石板那块有团白色的影子,直到她收工回家也没有动。桔子那天穿一件红色毛衣,而不见了的小美穿的正好是件白色西服外套。王宝林娘的脑子不太好了,但眼神还是够用的,穿针引线的活都还能做。
调查到此为止。准确地说这青石板才是最后一个见到小美的家伙。可是王坪大又不能问它,问它也不会说什么。桔子有什么必要害她呢?她做她的娼妇儿,关桔子什么事?就算是桔子把她推到了河里,也该漂起来了,就算是被冲到了下游,也会在下游漂起来,就算是被冲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也会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漂起来。总之,在涔河里淹死的人是一定会漂起来的,可是这半个月的工夫过去了,这河里除了偶尔有被洪水冲断根茎的水草漂起来,什么也没漂起来过。
准是勾搭上么个路过的男人,又到别的么个地方去了。一镇的人都这么说。
镇上的人是放心桔子的。现在的年轻姑娘,有几个像桔子那样勤快、安心、乐意的呢?在涔水镇,人们去米粉店吃米粉的时候,店子里一般都有几大盆油炸干辣椒、酸菜、酸豆角和榨菜丝,任吃任加。每家米粉店的米粉的口感可能有不同,浇头的味道更是千差万别,但是任吃任加的小菜都一样的酸、一样的辣。桔子嫁过来后,崔家摆在店子里的几盆小菜很快就让人吃上了瘾。一样是酸豆角,崔家的酸豆角颜色硬是透着金黄,酸得特别好,辣得也特别好。有时还有一些难得吃到的精致小菜,叫人一尝难忘。就说夏天里田间地头长得挤密的芋头秆子,以前谁吃它?乡下人拿它喂猪!桔子花很少的钱买了来,腌了腌,晒了晒,没事的时候坐在店门口,一边和人说话一边把它撕得细细的。第二天一大早,崔家的米粉店里就会有一盆拌了剁辣椒和太和豆豉的芋头秆,还撒了点葱末,倒上了点茶籽油,看上去有红有绿、有黑有白,吃到嘴里酸酸的、辣辣的,咬一口脆脆的、香香的,米粉都要多卖多少碗!桔子是在日子里用心用力的,涔水镇的人有自己的方法去辨别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桔子就像条又平又直的马路,站在路口一眼就可以望过去老远,桔子能有什么?
桔子的丈夫崔木元却不这么看。这个不太作声的年轻人在千篇一律的生活里也时时怀有吃一堑长一智的戒心,不是出于谨慎,而是来自不彻底的甘心。姆妈在的时候,有一次他从外面回家,穿过安静的店堂走到院子门口,正要推门进去,就听见从里面传来戏谑的笑声:“……石淑啊石淑,昨个半夜是你起来了吧,我听到楼上尿尿的声音……只听声音……嘿嘿,就知道是你……这是公公对儿媳说的话?他们家呀……”桔子正哧哧笑着跟姆妈说着什么,两个人都沉浸在无比的兴奋里,脸上有过节才有的表情。看见崔木元,桔子把头低下去,额前的头发流苏一样地垂下来。就像正走着的一条路陡然间出现了分岔,这条分岔神秘地向不明之处蜿蜒……崔木元顿时觉得桔子就像个深藏不露的探子,表面上看上去是个凡人,其实深谙生活中那些阴暗的秘密。
桔子配合派出所的调查从河边回来,看见自家的店门虚掩,厨房锅冷灶凉。一镇的人谁不是热菜热饭地吃上了呢?桔子有些生气,打开碗橱拿出中午吃剩的饭菜来热。崔木元从外面回来,一手撑在厨房的门框上,也不跟桔子说话,只是用看杀人犯的眼神看她。这让桔子很恼火,锅和锅铲、筷子和碗,碰出了一连串的声响。
是有几件事,让崔木元用别样的眼神来看桔子。冬天里店子清闲起来,崔木元有时会出去找毛二、刘四他们打牌喝酒,他回家晚了点,桔子的眼神就很复杂。有一次她拿了一张报纸给他看,报上一个女人用剪子剪丈夫的事被她用记账用的蓝色圆珠笔画了道道,崔木元觉得她是在警告他。当时她看他的眼神仿佛就在说:“这样的事我也会做得出来哈!”去年下雪的时候,叫小美的女人来店里买米线,她穿一件白色过膝棉衣,哆哆嗦嗦地光着一节腿子,尖尖的一张脸一半藏在竖起的领子里。崔木元接钱时碰到她冰凉的手,蓦地让他想起一个人,他看她的时间长了一些,眼神直了一些,桔子就把手里正给他织的一件毛裤“啪”地一下拍在柜台上。桔子家里,她的爷爷、爷爷的爷爷,都是土匪一样的人。家里的盐罐空了,天一黑就钻到密密的松树林里去,专等从四川贩盐的过路商人,砍翻了往沟壑里一丢,在门前稻田的月口里洗干净手上的血,回家往床上一躺就呼呼睡到天亮。白天里下田插禾,上山狩猎,看上去都老实厚道。桔子的爸爸,换个社会,一样是会做土匪的人,五十多岁的人了,为争水灌禾,还打断过人一根肋条。
还有,桔子怎么早不说那天她见过那个叫小美的女人?非要等派出所的人来找了,才说。这事别人的婆娘都没份,偏就她有份。
崔木元想起这些,就在床上翻过身去,只把一个后背给桔子。
2
小美到哪里去了呢?有一阵子黄咬银想一想这个问题心就突突地跳,有好几次晚上做梦,小美就站在她的床前看着她,头发披散下来遮住半边脸。小美说:“你逼我!我死给你看!”说着小美一头往墙上撞去,黄咬银就在惊吓中醒来。王坪大有一次被黄咬银惊醒了,他打开灯,看见黄咬银怔怔地坐在床上,脖子上的头发都汗湿了。黄咬银把头转向他,怔怔地看了他半天,说我梦见小美死了,浑身是血。黄咬银算是经过一些事的女人,经过了一些事还这样,王坪大很不屑,就说,婆娘家。
王坪大不是天天来黄咬银家过夜,方便来的时候才来,想来的时候才来,这样的情形他也就看见了一两回。黄咬银的房子在小镇西街上,底下两层是洗脚房,上面一层是黄咬银的卧室、卫生间、客厅,还有一间客房。客房是给乡下的黄咬金、黄咬铜准备的,他们不时会捉只活鸡活鸭到镇上来看黄咬银。房子还有一个后院,后院墙改成一溜四间平房,两间是给洗脚的服务员住的,一间是厨房,一间是专门煮洗脚药水和放洗脚木桶用的。服务员住得不宽敞,每间都挤了三四个人,可是后窗下不远处就是涔水河,晚上睡觉了,能听见流水声。小美来这里的时间有大半年了,没人知道她从哪里来,长得细皮嫩肉的,说她十八岁,行,说她二十八岁,也行。身份证上写的是赵小美,1988年生,湖南华容人。黄咬银知道那当不得真,她自己在广州的时候,就不叫黄咬银,身份证上的年龄也比实际小很多。
有一天王宝林的娘来找王坪大,说王宝林已经很久没给家里打电话了,辣椒秧都长了一尺高,还没个音信儿。王坪大问他最后一次打电话是什么时候,有没有说跟什么人在一起?王宝林的娘说不清楚,只是从怀里掏出一张复印下来的汇款单,上面写着:妈,我现在韶關天姿美容美发学校速成班学习,学成我就回来开美发店,怎么都得养活你。宝林。时间是半年前。王坪大把汇款单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叹了口气,说我想办法去函跟那边联系,一有消息就告诉你,你要放心。
王宝林的娘连说放心,我晓得你不会哄我。
快下班的时候,王坪大在山里当乡村医生的妻子金满给他打电话,说这个周末不回来了,寺里有佛事活动。以前孩子小,王坪大可以拿孩子说事,现在孩子到县城上高中,住校了,王坪大听着电话,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妻子说“寺里”比说“家里”还多,王坪大毫无办法。妻子说的寺是指夹山寺,有大量史料证明夹山寺就是闯王李自成埋名终老的地方,香火因此旺得很。王坪大自己也说不清楚,他的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信佛的,他抓捕逃犯时受过几次伤,以前妻是为他担惊受怕,偶尔去烧个香,为他求个平安,近些年来就有些把寺当家了,动不动就佛事佛事的。王坪大就想,老要别人放心,自己的心又该怎么放呢?
到了晚上王坪大就又去了黄咬银家。
睡到半夜,黄咬银又被梦惊醒了。她跳下床,浑身汗津津地立在窗边。窗帘上的滑轨坏了一个,窗帘怎么也无法拉严,始终豁着一道口子。黄咬银就从这道口子里往外看,街对面就是崔记米粉。月亮很大,照得一街的房子都像水洗过一样……小美这样的人哪么都不得自己找着死,黄咬银觉得就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她。过了一会儿黄咬银回到床上,黄咬银轻轻地说,哎……
王坪大睡得呼呼的,俨然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对周围的一切毫不知觉。
黄咬银在床上坐了一会儿,伸手把王坪大的一双脚抱过来放在胸前,从足背的临溪穴一路揉捏下去。王坪大的双足陷在黄咬银绵软的胸前,不一会儿,他就在一阵接一阵的酥麻中醒了过来。
你说,小美,会不会,让桔子推到河里去了?黄咬银把声音压得低低地问,很迟疑地,仿佛是在提及一件令人羞于启齿的事。
月光从窗帘的豁口淌进来,照得屋里影影绰绰,黄咬银披散着头发,显得有些鬼魅。王坪大想怪得很,两个女人都是狠角色,都是日子变成了刀子也趟得过去的主儿,相互间却哪么都对不上眼。他把被子撩到一边,松软地摊开了两手两脚。等黄咬银爬到他身上后,才嗔怪地说:“没的证据,乱讲!”就像一个仁厚的长者,语气里有那么多的慈爱。
早上,崔家的米粉店里总是汇集着这镇上的各色人物,黄咬银爱那样的一种热闹,尽管看到桔子不是件蛮愉快的事,但黄咬银还是常常到崔家的米粉店去吃米粉。日子反正就是那么回事,所有的痛、所有的不舒服都是要像辛辛苦苦赚到的钱一样掖起来的,高兴的事、好的事才可以像粉一样搽到脸上去。
有时黄咬金或者黄咬铜来了,黄咬银也带他们去。除了给他们要碗牛肉的,还要一碗牛杂的。他们回回吃得满头大汗、心满意足,回去后对乡人说上好几天。老一辈的乡人想起黄咬银的三病四灾的父母,就说幸亏哈,幸亏黄家养了个女儿,不然哪么下得了地。黄咬银的父母最后也都是各自睡了一副漆得黑亮的杉木方子,体面地躺到了向阳的坟地里去。这一点,黄咬银自己也安慰得很。
黄咬银从不让这兄弟俩在自己的店子里洗脚。兄弟俩也还是识趣的,连带着他们的妻,他们的儿女,进了院子,带来的鸡鸭、头茬的瓜果蔬菜,有时还有新榨的菜籽油,顺着墙根儿放好了,直接从院子里的简易楼梯爬到三楼去。叫了,才下来,不叫,安安静静一坐就是一整天。回去的时候,倒空的化肥袋重又塞得鼓鼓的,侄儿侄女的换季衣服,割稻时请人帮工要用的芙蓉烟、谷子酒。如果赶上过年宰杀的年猪小了点,腊肉吃完了,还得割上十来斤的鲜肉续上。菜市场的烧饼、娃糕带到乡里,也是劳作间隙时的好吃食儿。黄咬银想起这些年来咬金的房子、咬铜结婚时的花费,想到自己三十多了孑然一身,就一边张罗,一边恨恨地说:“前世欠你们的,前世!”说得大家都讪讪的。碰巧来的是嫂子的话,这嫂子就一伸手拖过来一个孩子,“啪”地一巴掌拍在那孩子的小屁股上:“也就是自己的姑,亲姑!记住点儿哈讨债鬼!”说着动了情,想着彼此日子的不易,挨打的讨债鬼没哭,打人的倒落下泪来。完了黄咬银又把几十元纸币卷成小卷儿,塞到这落泪的人的手里,四只手推来推去地捂到一块儿,彼此都感受到了打断骨连着筋的亲情。
其实有时黄咬银生气,也并不完全是生哥嫂的气。就说她带着家里人去崔家的米粉店里吃米粉吧,别人进了店,桔子打着招呼,扎扎实实地给笑脸。他们进了门,桔子一样是笑啊,但那笑又分明是给别人的,各处绕了一圈,最后才捎上他们。
来了啊?桔子说。通常她只用了一点余光瞟瞟他们,笑脸儿就飞快地迎向了别的人别的地方。
来了。临了黄咬银还不得不答。
小美在的时候,动不动就跑进来说,桔子家里来人了。
黄咬银发现,桔子家的人来了,笃定是要搬只小竹椅儿坐在店子门口的,也不见得和街坊们扯什么。就说桔子她爹,灰布裤子卷到膝盖,黄胶鞋上一样粘着红泥巴,四平八稳地往店前一坐,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叶子,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一对儿箩筐就撂在门边,来往的人谁不得跟他打个招呼?就着箩筐里的春笋、蕨菜扯上两句,没有不爱听的。桔子的爹也是谁都瞧不来的样子,一开口就笑乡邻扯个塑料棚,吃得四季颠倒。有一回他指着别人菜篮里反季节的黄瓜,说没见过日头的东西,我就不吃这种背时的货!街上的人都笑他。
一样是乡里人,偏就他们是那样儿的。爹种田,她种田,嫁了个男人,男人卖米粉,她卖米粉,还不都是靠男人吃饭?一街的人就她那样看人,仿佛别人是妖是怪,她一眼就要把人打回原形。那样的眼神,杀得了人。
3
小美来镇上一段时间后,人们才知道来了个洗脚的丫头叫小美。那一年的秋天来得悄没声息的,往年立秋一过,天就跟漏了似的一天接一天地落雨,一场雨一场凉。这一年不知不觉地,就像猫儿踩过屋脊,像风儿吹落杨花,轻轻的慢慢的,天高了,风凉了,太阳不灼人了,人们意识到夏过了,秋来了。这不,门前的梧桐开始往街面上掉叶子了,乡民们忙着收割水田里的晚稻、旱田里的棉花、玉米,来街上的人少了,街道变得悠长而空旷了。街上的女人就在店门前支起桌子打晃晃(麻将的一种玩法),一坐就是一整天,每一天都长得像涔河的水一样望不到头、望不到尾。
足疗店的姑娘们很少跟街坊们来往,她们要出来也是结伴而行,仿佛是知道自己与别人是不一样的。她们走出门来,个个寡言少语的样子,只是眼神要比一般人活泛很多,像不小心摔到地上的水银,到处滚来滚去。她们中似乎有人还共用一个名字,叫兰菊的,高一阵、矮一阵,又胖一阵,就好像名字只是顶帽子,张三戴得,李四也戴得。黄咬银时不时站在门口数落她们其中的一个:“笨啊,多少遍了,还分不清太溪穴、大敦穴!像我们做正当生意的人,没有两下子你赚么子钱啰!赚喝欠!”听起来她比这一街卖米粉卖百货卖五金的都来得正当,被她数落的人没有一个作声的。有一天她站在门口呵斥一个蹲在树底下喂猫狗的姑娘,姑娘不耐烦了,一扭身进去了,把店门上的帘子推搡得哗哗乱响。黄咬银愣了下,才说:“个小美!”人们才知道那个喂猫狗的姑娘原来叫小美。小美没事就拿了剩饭喂街上的猫狗,弄得一镇的猫儿狗儿都往西街跑。
人们开始说,这小美,长得倒像一个人。就有人跑到北街去对宰杀猪牛卖肉的刘四说,有个小美长得好像你姐春儿呢!刘四把剔肉刀一扔,过来看了一眼,说个卵,眉眼有一滴滴像,身个儿差得远了。
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十七岁的春儿要单薄许多。
春儿上小学时和崔木元一个班,小时候的冬天冻得死人,屋檐上倒挂着一尺长的冰凌。冻不过了,瘦小的春儿会把一双冰凉的小手塞到崔木元的袖筒里取暖……崔木元有时候会想,要是春儿不去深圳的铁厂打工,而是在足疗店,又哪么会得破伤风死呢?一些场景崔木元并没有亲眼见过,但一幕幕仍宛如亲历:春儿举着失去两根手指的右手去找老板,老板说小小事啦,珠江三角洲的断指接起来有两万五千里长啦,去隔壁诊所包一下就没问题啦。
崔木元经常隔着条街看小美喂猫喂狗,一街的哗哗哗的搓麻将的声音,这声音将崔木元与小美漂浮起来,其他的人离得那么远,崔木元的思绪也就跑得那么远。
小美会让崔木元想起春儿,想起从前的一些事,从前那些初春的晚上……轰隆隆的雷声常常叫人无法入睡,好容易等到天蒙蒙亮,戴了斗笠,穿了蓑衣,一路踢着水花跑过歪歪斜斜的小巷去叫春儿……雨使得涔水河充满着无数大小不一高低不同的美妙声响,从稻田、从小树林、从长满盘根草的地上汇来万千条的细流,各自或浅唱或低吟地奔向涔河。满肚子都是鱼卵的鲫鱼逆水而行,它们往往选择稻田的月口往上顶,不时地发出吧嗒吧嗒的声响。崔木元站在齐腰深的水里,用簸箕撮住一条就往岸上扔。鱼在草地上跳跃,春儿咬着嘴唇用力摁住了,折下一条刚长出新叶的柳枝从鱼嘴到鱼鳃里一穿而过。挂在柳枝上的鱼不甘心地甩动尾巴,溅得她脸上都是水,春儿抬手一抹,就会露出特别干净的一张脸……这是崔木元到现在还记得的。
他倒是没想过什么爱情不爱情、幸福不幸福的,事实证明人活着有些东西是不用去想的。因为这些东西有它们自己的命运,有时候它们会像棵南瓜秧,刚钻出土,就被咯咯叫的鸡啄去了,你就是想破脑壳又有什么用呢?
小美不见后,那些猫儿狗儿围着树转了两天,就各自散去,按老法谋生去了。镇上的年轻媳妇给孩子把完屎,“喔哦喔哦”地叫两声,几条街的狗都過去抢食。毕竟是畜牲,谁也不知道惦记。
4
桔子被派出所叫去配合调查后,崔木元有两三天都没和她说话。早上忙起来手碰到手,晚上困觉头挨着头,依然不说话。崔家几代人都做米粉,他们做的牛肉米粉在这方圆几十里是出了名的。崔木元十五岁那年父亲生病死了,他退学回家开始学习挑选大米、泡洗牛肉……
牛肉进店立即用铁钩挂上,分老、嫩、肥、瘦切成一斤左右重的块子,放在清水里浸泡。冬天泡三小时,夏天泡一小时左右,再用清水反复漂洗,挤压,直到水清。
然后捞起,用祖传秘方配制的香药煮熬,所用的香药有二十多种,用纱布包好放在炉锅底部,上面放牛肉,炉锅不加盖,让牛肉的腥味散发出去。
煮熬时汤中有血沫浮起,立即将血沫舀出,同时根据牛肉的肥瘦加放适量的牛油以增鲜味。
牛肉煮到手指能捏烂时便捞起,摊放在器皿内,待冷却后切成小块,以备做油码。
在煮熬了牛肉的汤内加入二分之一的清水,再行烧开,然后收尽浮油,澄清汤汁,使之透明晶莹。
再将清汤舀进另一只炉锅,作为原汤,下粉时加放在米粉内……
一步也不能少,一步也不能错。
崔木元本来就是一个说话很少的人,每天这样子,不免时时从这种日常的劳作里感受到一种无法言喻的损伤,因此他看上去简直有些小镇上的人看不大懂的忧郁。
知子莫若母。姆妈在的时候,时不时会说:“……就是上个大学又哪么样哈!”他原本也是有一些年轻人张狂的想法的。姆妈去世前给他娶了桔子,结实的、乖致的、对生活兴致勃勃的桔子快乐地承担了泡洗牛肉的活计。她的热情从哪里来呢?崔木元有时会觉得她像一条他无意中闯入的隧道,昏暗的灯光只能照亮脚尖前的一点地方,后面有过什么、前面会有什么,通通无法看清。
不说话的日子过得是那么慢,但桔子对自己说:懒得!
这样又过了几天。
这期间崔木元和毛二、刘四他们打了几场晃晃,输了五十多元钱。桔子做了好几十斤的米粉,泡洗了好几十斤的牛肉,还给院墙下种的两棵南瓜秧浇了水。一天下午她端了一盆大米坐到门口去,一边拣米里的石子,一边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米是陈米,今年的早稻刚刚开始晒田,河对岸的稻田通通扒开了月口,肥沃的田水带着被乡民们拔断根茎的鹅毛草流向了涔水河。桔子想起了这时节山里的绿豆菌、烂窝菌,嫩嫩的蕨菜、竹笋、豌豆尖,还有一推门就可以看见的满山坡的白色桔花,眼眶酸酸地就有些想哭了。
“我脏了我的手,一巴掌把她嫁给了河神!”桔子赌着气跟自己说。
“就是把她嫁给河神,河神又未必肯要她!”桔子想着想着又笑了。
过了一会儿,桔子一抬头,看见街对面黄咬银倚在大门框上,一边嗑瓜子,一边笑吟吟地看着自己。
桔子把下巴抬了抬,迎着黄咬银的目光看过去。
两三秒钟的光景,黄咬银就败下阵来,张了张嘴说道:“拣米哈。”
晚上桔子就把圈在院子里养大的一只芦花大公鸡给杀了。崔木元只走到门口,就闻到了鸡肉香,他想这是发什么神经,这鸡报时比睡房里那只万事达钟还准,一年来夫妇俩总是鸡叫三遍起床,从未耽误生意,桔子把它当个宝的。他想问的,鸡吃完了也没说出口。桔子看他吃完饭,把碗一推进了厨房,出来时手上多了把刀,崔木元还未回过神来,桔子就把刀“呯”一下扎在桌子上,刀上净是鸡血,还粘着几根柔软的鸡毛。崔木元吓了一跳,他仰着张没一点儿血色的脸,看着面无表情的桔子说:“怎……怎么,杀夫哈?”桔子撇了撇嘴角,说你还会说话啊!
崔木元松了口气,想真是土匪窝里蹦出来的哈!为这点儿事动刀子!其实他刚进门时就想跟她说话的,一下子没开得了口。下午和毛二他们玩麻将,毛二说昨天赢钱了就去浅水湾洗脚了。毛二笑得极其暧昧。大家就哄他,问他搞没搞,跟哪个搞的,搞得怎么样之类的话。毛二说搞个卵,进去没两分钟婆娘就进去了,最后自己没洗,伺候婆娘洗。大家就笑他怕婆娘。“不过还是有蛮大的收获的。”毛二笑得很诡秘,说:“给我婆娘洗脚的丫头进门时骂骂咧咧的,说什么逼死了人还有脸来。我婆娘就过细地问她。”说到这,毛二笑着闭嘴不说了。大家急了,把住麻将不打,逼着毛二说。过了一会儿,毛二说:“有钱人哪么玩儿你们只怕想破脑壳也想不出!有个在山里开煤矿的老板看中了那个小美,要小美,舔……舔他的脚!小美那个丫头说?菖可以,舔不行,给多少钱都不行。黄咬银就打她,说不让?菖可以,但这么松快的事不干,就是成心砸她的生意。小美撞了一次墙。”几个男人听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崔木元想到这,就说:“小美……”
他刚一开口,桔子就打断了他,说别跟我提那些娼妇儿!以往桔子一说娼妇儿娼妇儿的,崔木元就会说积德哈,人家也是要吃饭。桔子则会说就那么要吃饭!这一次崔木元不吭声了,桔子微笑着,端详了崔木元半天……她想起那天的小美,穿了件白衣服,看上去乖致得很。可笑的是去河边还穿着高跟鞋,摔了一下就坐在地上像个孩子似的哭个没完……娘说得没错,男人喜欢的不是女人的好……想到这里,桔子叹了口气,不紧不慢地说:“你要是不想和我过了一定要直说哈,要过就好好过。”桔子停了停,语气里突然就充满了伤感:“不好好过还不如就拿这刀扎我呢。”桔子看上去都有些哀伤了。崔木元想起这一年多来桔子的勤谨、辛劳,就有些羞赧地低下头,说哪能呢。
5
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人们脱掉夹衣,穿上了单衣,后来又脱了单衣,穿上了短袖。人们先是吃了几次豌豆尖,后来又吃了几顿猪油煮的嫩豌豆,日子一天天过下来,渐渐就把一些事给忘了。
有一天浅水湾足疗店的服务员从墙角的柜子里掏出一个红色拉杆箱,黄咬银歪着头想了半天,才想起是小美的。黄咬银让人拧开箱子上生锈的小锁一看,满箱子花花绿绿的衣服,有小美穿过的,也有她没穿过的。黄咬银在箱子底下还发现了一张照片,小美一手叉在腰上,一手攀着枝开得艳艳的桃花,笑得又神气又娇美。
足疗店里来了走走了来的姑娘多得是,可谁也不会把箱子丢在这里不管。出门在外,箱子跟家有什么分别?黄咬银于是又有一阵子觉得小美就在河边,只要派人去喊,就能回来。
6
大约到了乡下双抢的时候,韶关市公安局给王坪大来了函。王坪大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无名尸体未查到。”
王坪大当时刚在崔记米粉店吃完一碗牛肉粉,他一手擦着汗,一手拿着信函研究了半天。后来王坪大说,那个美国,每年有无数的人失踪,光孩子一年就有八十几万找不见。
涔水镇两万多人,八十除以二……哦哟!周围的人一拍巴掌失声叫了起来,一年不见四十个涔水镇人!四十个涔水镇的人要是都站到涔水河里去,河水只怕会漫到太青山里去。看来那个美国真不是人去的地方哈!
王坪大又说,一个人突然不见了,有时也是件正常的事。长着腿,现在又是自由社会,想去哪去哪,政府也管不了。
可是大家还是不明白,那些人都去哪里了呢?就是把他们都埋了,那也得挖多大的一个坑?一个活人怎么可以说不见就不见了呢?
王坪大最后说,也有这样的人,活着活着突然就不想让人找到了,他(她)换一个地方,活另外的一世人。说这话时他想到了他的妻,不久前已改名慧净,那个叫金满的分担过他许多惊吓、给过他许多温暖的女人,剔亮了佛前的银灯,彻底从他的生活里消失了。
原刊责编 李向荣
【作者简介】艾玛,本名杨群芳,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湖南澧县人。曾做过军校教员、兼职律师,现在中国海洋大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