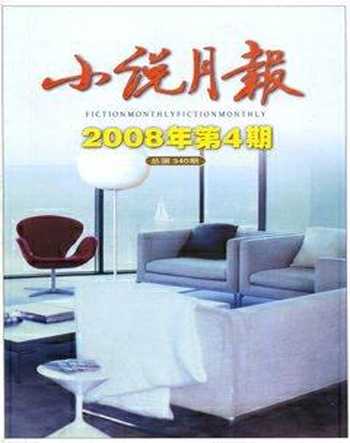VISA卡悬疑
出国、开洋荤,我这个土包子从前连做梦都不敢想,如今毕竟梦想成真了。可是几天折腾下来,我怕了,整天头晕、心悸,根本无心看风景,只盼着快点混到日子,快点打道回府。这洋荤不开也罢,一路上除了后悔就没想过别的。我的反常成了彭局长嘲笑的话柄,他笑我土,说我是“土包子开洋荤”,有福不会享。他一直以为我萎靡不振是时差没倒过来,我有苦说不出,也只好顺着他说,是时差倒得不好。
他倒是很放松,好像根本无须倒时差,他说他很适应西方文明。纪检组长老许也附和他,说他也是“宾至如归”的感觉。在丹麦美人鱼雕塑前,彭局长见我连一张照片也懒得拍,皱着眉头说了一句让我心里犯堵的话:怎么了,整天哭丧个脸,像谁欠你二百吊似的,带你出来开开洋荤,还换不来一个笑脸?
我不得不调整情绪,装笑脸。人家说的何尝不是?
我家祖辈是大山林里放木头的,到了我这一辈,用爷爷的话说,是祖坟冒青气了,出息了我这么一个。其实我这官说起来让人脸红,小小的林场场长,正科级而已,还能叫官?可爷爷说的也在理,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林场场长虽是个芝麻官,可管辖着几百公顷的山林,二百多号林业工人,不说伐木,光每年打下的松子,也有几十吨,一车车原木、山货拉出去,回来的是流水一样的钱啊!
我真没想到,磨盘大的雨点会落到我头上,彭局长带两个人出国考察,就有我一个。这消息一传开,全局上下几万人当中刮了好几天风。有人说,没看出来,徐凤棣这小子是彭局长的心腹、红人!也有人猜测,下一个晋升副局长的人选非我莫属。这都不必去理他,让我闹心的是另一种舆论,说我花了大钱“运动”来的,不会说我花钱“运动”出国,当然是指“运动”当官。
我挺上火,我還从没有过奢望,更没干过这种事。一怒之下,我真想放弃出国机会了,因为开一次洋荤让人家指脊梁骨犯不上。但朋友们都劝我,“何必致气”?多权威的人也堵不住别人的悠悠之口。
车停到了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彭局长和许组长什么都拍,现在又跑到市政厅右面一组青铜雕像前拍照,听导游解说,他们乐得前仰后合。他俩用的都是索尼数码相机,只有我使的是老掉牙的理光傻瓜相机,被他们俩取笑为“一级出土文物”。
这几天,只要他们的索尼相机闪光灯一闪,我心里就忽悠一下子,仿佛不落底。这种有八百万像素的机器,每台四千多元,加上三角架、备用卡、备用电池等零件,两台差不多花去一万。这钱是我出的,我可不是自愿,可我没办法不自愿。外办把出国任务书下达那天,彭局长把我叫去,告诉我这个喜讯,当时许组长也在。他们确实有经验,告诉我要去买几个电源转换插头,北欧四国是两项大圆头、二百二十伏,英国是方头插头,外国旅馆没有开水供应,得买电热壶。我说我马上去买,特地讨好地强调“每样三份”。
中国人热情好客,彭局长又指示要带些小礼品,丝绸围巾、惠山泥人、内画鼻烟壶、景泰蓝瓶瓶罐罐,还有字画。这些琐碎杂务,当然应该由我效劳。我的讨好似乎并没感动谁,他们的表情告诉我,这是天经地义的,你饶什么舌!接着,彭局长像是跟许组长探讨地说:“别忘了带相机,还有摄像机。我原来那套尼康家什倒挺专业,不过太沉了,不方便。”
许组长便附和他,什么年月了,还背几十斤重的玩意儿?新款的数码相机拍、摄两用,内存卡容量大,一个卡能拍一千张,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
彭局长仿佛刚刚被提醒一样,他望着我说,那就去买,一人一台,小徐,你跑跑腿吧。
三个人当中我最年轻,当然由我跑腿。钱呢?钱由哪儿出?局里吗?还是自掏腰包?
我其实够呆的了,这话能问出口吗?我马上发现,彭局长的马脸拉下来了。这时有个电话打进来,彭局长没好气地对着话筒申斥对方:“我说你这人怎么是榆木脑袋呀?你从火星上来的吗?这点小事你都不会变通!”
我心里一抖,怎么有点像骂我呢。我正不自在,许组长悄悄扯了我一把,把我拉到走廊里。
“小徐快来,看看丹麦有没有处女?”彭局长在大声叫我了,我一下子惊醒过来跑过去。
我仰头看塑像,是两个举着喇叭欲吹的人,我问:是号兵吗?
他们几个一听都嘻嘻地笑。他们这才告诉我,这是两个打赌的人,他们面对的这条街叫处女街。二人相约,只要发现这条街上走过来处女,便吹响喇叭。可是这么多年来,他们从没看见过处女,喇叭也始终没有吹响。
他们又笑个不住,我却笑不出来。
他们又到安徒生铜像前去“借灵气”留影了。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买相机的钱该怎么变通,从什么科目里下账呢。
光是买相机的钱,我也许不犯愁,可是二十万的大窟窿,我一想起来就害怕,好像那深不见底的黑洞就在我脚下,我随时有可能栽下去。
好在许组长的话给了我不少安慰。他那天把我拉到走廊,说我太死板,这年月,变通是硬道理,他暗示我,他不相信一个林场会没有小金库。言外之意,是点拨我尽管花。这话从纪检组长嘴里说出来,让我吃惊,也让我放心,给我壮了胆。啥也别说了,出血吧,我敢说我的林场水清无鱼?真的没有小金库?只要纪检组长认真,谁也经不住查。虽然我从没胡来过,可打松子、卖树苗的钱不入大账,给工人分奖金、搞福利,认真说来,也是不合法的,就看上头是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我狠狠心,买了两台数码相机,自己没舍得,也是怕日后说不清。我把十多年前当劳模得的傻瓜相机带上了,连上中学的儿子都嘲笑我“老土”。
明天就要飞往芬兰了,我暗暗希望彭局长累了,赶快回旅馆休息,最怕他向导游这样发问:这里有什么特产?
离开安徒生塑像一上车,彭局长喝一口矿泉水,果然问女导游了,哥本哈根有什么值得买的?
这正对导游的心思,你不问她还要引导你消费呢。顾小姐马上眉飞色舞地推介:不买琥珀,等于没来丹麦。丹麦是全世界唯一出琥珀的地方,透明、轻柔,上等成色的琥珀,在灯光下可见里面有各种小飞虫,简直是活化石,历来为皇家钟爱的饰品。她特别介绍,那家琥珀博物馆,因某国前总理夫人进去挑选过琥珀项链而名声大振。
彭局长立刻精神陡长,他说:快去看看,肯定错不了!许组长也跃跃欲试,说他女儿要结婚,正愁买不到合适礼物呢。
我忙小心翼翼地问顾小姐,这东西贵不贵?我多余问,小时候就听说过,珍珠、翡翠、琥珀、玛瑙,这都是富人用的宝贝呀,便宜得了吗?
照理说,人家买东西,贵不贵与你何干?
但此行我是什么角色我清楚,我是跟包的、账房先生,两位领导只管购物,我呢,管埋单。
我也多余苦恼,周瑜打黄盖,还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走前,许组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徐,彭局长待你不薄啊。这当然是指带我出国这件事。他说我已经让人又羡慕又嫉妒了。他还告诉过我,到明年年初,局领导就出缺了,宫副局长到站,肯定要从局直属处室和各林场一把手里物色人选。更深的话他没多说,他这显然是暗示。暗示什么?难道让我陪同彭局长出国考察,是一个信号吗?想到这里,我的心禁不住怦怦乱跳。
我遇事总不忘去请教我姐夫,他算得上是赤白松林业局的“三朝元老”,他没退休的时候,当过采伐班长,林场场长,营林处长,财务处长,局长办公室主任,又一直是党委委员。他伺候过五六任局长,人人都得意他,又哪一任都没提拔他。人们总是议论他“快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也许就差那么一“哆嗦”,始终没“哆嗦”上去,到点时却“哆嗦”下来了。
他称得上是局里的万事通,料事如神,当官的碰上下不了决心的事,都愿意跑到他那儿讨个主意,一般说来,帮不上忙也添不了乱。
我当然更得靠他了。当我兴冲冲地告诉他,我就要出国去开洋荤时,他挺冷静,皱着眉头闷头抽烟。他不皱眉头都是一脑门儿皱纹,眉头一皱,粗糙的脸更是山核桃皮模样了。
姐夫用挖苦的口气说,你以为你摔个跟头捡了个金元宝了?
听他这口气,我出国不是喜反倒是忧了?这回我可不大服气。
姐夫问我,全局中层干部三四百,你有何德何能,彭局长能挑到你头上?
这也正是我纳闷的。我嘴上却不服,我大小是局劳模、市劳模呀,我们大荒沟林场年年给局里上缴几千万,从来没拖过局里后腿,我又从来没争过什么,我就不该沾点光?
这些,姐夫并不否认。但他分析,我从来没被列入过“后备干部”名单,一直不在领导“视野”之内,所以有这样的好事降临头上,有点让人费解。
他说得我有几分泄气了。当姐夫又续上一只烟时,他忽然舒展眉头大声说,明白了,拿你当钱罐子了!
钱罐子?这是什么意思?
姐夫说,出国的国际旅费、公务费、食宿费、零用钱,这当然都能正常报销了,可非正常消费,比如买东西,谁埋单?你呀!你正合适。局长绝不会从局里报这种账,那等于撅着屁股让人打,蠢到家的官儿才这么干,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由你当账房开销一切,就再好不过了。他知道,各林场都有小金库,上头装聋作哑,已经是给你面子了,领导出国,你出点血,又好走账,不正是报效机会吗?从这个意义上讲,确实是对你最大的信任。信不着的人,你上赶着给他送一座金山去,人家还不敢要呢,谁知道你是不是给人家下套?谁保得住你永远守口如瓶?
听了姐夫这话,我有如醍醐灌顶,想到买数码相机的过程,我还真是扮演了账房先生的角色。
一听有关相机的暗示,姐夫用力地拍大腿,对了,这就对了!证明我的推测丝毫不错。接着他摇头晃脑地替我预测未来:机遇与风险共存。
我有点害怕了,有风险的事我可不敢沾边。
据姐夫分析,不用自掏腰包来取悦局长,这是机会,这机会恐怕是彭局长权衡再三,才“历史性地”落到我头上的,至少可以印证,他信任我,把我视为“自己人”,才“不外”。在国外的半个月里,一旦把彭局长、许组长伺候得舒服、满意,我就真正由局外走入局内,走进了他的“视野”,有极大的可能成为一匹“黑马”,出人意料地坐到副局长的宝座上去。
这前景当然令我心跳了。他所担心的“风险”,他不说我也能猜到,我动用林场资金,尽管是小金库,也总不能瞒过会计、出纳吧?怎么下账?什么名目?明写,等于给彭局长和我自己记下一笔罪过,巧立名目、偷梁换柱的苦果得我一个人尝。当时我的头一下子大了,即将出去“开洋荤”的喜悦顷刻间无影无踪了。
在我几乎想打退堂鼓的时候,姐夫为我谋划,说毕竟是机遇大于风险,成功了,一俊遮百丑。况且,费用的名目也不是不可以变通的,有些看上去不合理的开销,七转八转就合理了。
这不和洗黑钱一样了吗?
姐夫说,这么说也可以。他不准我后退半步,他分析,许组长在我面前提局领导职位出缺的话,绝不是无意间说出的,说不定就是代彭局长放话。姐夫断言,我此行回来,必高升。
我还是半信半疑,局里有資历、有学历的人有的是,闭着眼睛摸一个都比我强,他相中我什么了?别光是利用我,让我埋单,过后把我忘到脖子后头去。
姐夫的推断恰恰相反,他说他早品透了,这位彭局长是武大郎开店,绝对不容许比他水平高的人在他身边晃。在姐夫眼里,我是个老实人,本事不大,没有棱角,甚至没有思想,唯上是从,好摆弄,如果班子里全换上我这样的人,武大郎这店就好开了。
我的心动了,心活了。于是我让会计提了二十万块钱,换成欧元,还不到两万,好像一下子缩水了。我临行前又去请教姐夫,他嘱咐我把欧元分别给彭局长、许组长一部分,其余的要我机动掌握。给他们的,不能搞平均主义,要按二比一的比例分配,就说是零用钱,打个电话、给个小费、打个出租车什么的,还有,领导交往多,给洋人送点礼品也要花钱啊。最后姐夫嘱咐我,每人给了多少,绝不能“穿帮”,不要让他们通气,知道对方得了多少钱,要保持他们各自的尊严,要让他们都感到,你对他最好。
我嘲笑姐夫,你这么足智多谋,怎么直到退休也没爬上去呀?
姐夫叹息连连,他说,他如果是武大郎就好了。正因为他一直抱憾而退,心有不甘,才想助我一臂之力,把他没能实现的美梦,在他小舅子身上变成现实,也尝尝成就感的滋味。
这几天,身在异国,我是在圆姐夫的官场梦吗?
车子停到了灯火辉煌的琥珀博物馆门前,说是博物馆,卖货为主。彭局长和许组长已经进去了,这家店显然是中国人最喜爱光顾的,居然有华裔女孩当服务生,跑前跑后兜售。彭局长正在摆满琥珀首饰的橱窗前指点,眼里的兴奋光焰与亮晶晶的琥珀交相辉映。
我随便看了一下标价,是以丹麦克朗标的,最便宜的是琥珀耳坠,两百多克朗,不到三百元人民币。可彭局长的兴奋点根本不在这儿,他盯着的是手链和项链专柜,一律上着锁,上锁的必定是昂贵的,我懂。我站在他俩身后,拿眼睛余光瞥一眼,心口不禁又是扑通一跳,天哪,一副琥珀手链要两千多克朗,镶金的七千多,一副上好的项链要上万克朗。
我下意识地说了一嘴:这玩意儿没看出啥好,买这东西大头。
这你就外行喽!彭局长显得很内行,他说,琥珀是地壳变迁几亿年形成的,是松树压在地层下,由松脂演化而来的。他从服务生手里接过一颗大项链坠子让我冲灯光看,晶莹剔透的琥珀里有一只栩栩如生的飞蛾,连翅膀的纹理都很清晰。他说,这真是天工造物、鬼斧神工!是不可再生的无价之宝。
他仿佛成了人家的义务推销员,难怪服务生笑眯眯地称赞他“博学、懂行、慧眼识珠”。
彭局长开始挑货了,哪个贵摸哪个,他说,得给老伴和女儿各买一件,女儿有了,没有儿媳妇的,岂不偏心?他还另外拣选了几条,没说是给谁的,我心里恨恨地想:肯定是说不出口的!他早有绯闻,情人或者“二奶”不更得好好打发吗?
许组长也不甘人后,也在精选,和每次一样,数量比局长减半,他很懂得适度和不能僭越的道理。
我的心狂跳不止,手不由得去摸小腹部位。出国前,见我带那么多外币,老婆怕我丢了赔不起,死活给我在裤衩里面缝了个兜,钱就藏在那,用别针别住。老婆说,小偷用刀片割,就会割疼你的肉,你不会不知道。
安全倒安全了,可害得我每次付账都得先上WC,也不好在柜台前当众解裤子呀。彭局长把这当成了笑柄,每到商店,他总是打趣我:看好,WC在哪儿,别没地方掏钱。也难怪他笑我“老土”,你看人家彭局长,就是有风度,付款时,潇洒地将右手伸进西装上衣左面,掏出漂亮的皮尔·卡丹钱夹,两个胖胖的手指头轻轻一捻,便捻出几张钞票,动作娴熟而优雅,仿佛受过专门训练似的。
这一劫看来又躲不过去了,我把右手伸进裤袋,隔着裤子按按,那里早已瘪下去,没有几张百元票面的欧元了。此前在英国,彭局长买了一款劳力士情侣表,就把我的兜快掏空了。这可怎么办?看一眼他俩挑选出来的琥珀,那可是惊人的大数目,我拿什么付账?这不是要丢丑吗?我的冷汗呼一下顺脸淌下来。我本能地意识到,丢丑不丢丑还在其次,弄不好惹得领导不高兴,你既是出来埋单的,干吗不带够了欧元?你这不是扫领导兴,打领导脸吗?到头来,你不但没溜好须,反倒得罪了领导,还白白花了冤枉钱,,赔了夫人又折兵。
但我已经顾不得这些了,得巧妙地提醒局长,我没那么多钱。
不怪人家是局长,他看了我一眼,说,天不热呀,怎么汗流浃背了?怕让你掏腰包了吧?
我忙赔着笑脸,说:局长这说哪儿去了?我来干什么,还不知道吗?我说这话的样子一定很谄媚,很低三下四。但我还是战战兢兢地暗示局长,兜里见底了,怕不给我做主了。我还小声检讨,头一次出国,欧元换少了,实在是没想到外国东西这么贵,没想到外国钱这么不扛花。我只是没敢说“没想到局长的胃口这么大”,这话只能烂在肚子里。
还好,彭局长没火、没恼,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你以为西方是大排档啊!”
他并没有收敛的意思,反而又多挑了一个更贵的琥珀挂件。我的心无力地跳着,我弄不懂彭局长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他从兜里摸出一叠纸巾扔给我,让我擦汗,并且用关切的口吻劝我也挑一件,他埋怨我太土、太抠,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留着下崽呀?怎么也得给老婆买点什么呀,你若嫌贵,我替你出钱。
我心里说,别说好听的了,还不知道谁给你出钱呢!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买一寸,你敢买一丈。可我不能扫局长面子,我一边道谢一边说,我老婆是粗人,从小到大,没抹过胭脂,没涂过口红,更别说戴手镯、项链、金戒指了,顶多戴过做针线活的铜“顶针”。
这话说得彭局长和许组长哈哈大笑,连卖珠宝的女服务生也忍不住背过身去捂着嘴乐了。
在这种相对祥和的气氛下,我壮着胆,附在彭局长耳旁告诉他实底,我可没多少欧元了,顶多五百,待会儿找厕所去数一数。
彭局长摇摇手阻止我上厕所,他从怀里摸出他的皮尔·卡丹钱夹,原来里面插着花花绿绿各种卡,他抽出其中一张,送到服务生面前问,这个可以吗?
服务生拿起卡来一看,立刻微笑着点头,当然,这是双币VISA卡,在国外任何地方都可以消费,也可以支取美元、欧元,是可以透支的。先生这是金卡,消费没有额度限制,先生的信用等级没说的了。
我大为吃惊,彭局长还有这一手?怪不得他这么沉得住气。我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一时不知是什么滋味。彭局长这张双币卡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我不必惴惴不安地面对他们了。可我又不能不惶惶然,离了丹麦要飞往芬兰,然后访问瑞典,还要去挪威,能说这三个国家没特产吗?纵然彭局长不能买VOLVO轿车带回去,其他特产呢?出国前,我藏了个心眼儿,故意少换外币,让这二位不得不在我这有限的“库存”里支取,妈的,谁想到世上还有在国外能消费的VISA卡!更想不到彭局长猴精,他居然备了一张,又是金卡,可以无限制消费,这个无底洞让我眩晕。
彭局长一指许组长挑出的首饰,落落大方地对女服务生说,请一起结了吧。退税单子各开各的。
许组长一边作掏钱状一边说了句:怎么好这样?我看看我的钱够不够。
彭局长制止了他,幽默地说:你回去还我就是了,我又不怕你赖账。
我忘了禁忌,忙表态:尽管买,回去我把钱补齐。大话出口,心里又后悔,你这是打肿脸充胖子呀,回去怎么做假账才能天衣无缝?怎么做才能瞒天过海?我没干过,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万一犯了事儿,人家彭局长可以矢口否认,我能拿出送钱给他的证据吗?况且,我姐夫警告过我,真有那一天,也叫我认倒霉,自吞苦果,不能乱咬,你保了人家,他不倒,感你情,还会有机会“捞”你,你把送殡的也一起埋了,你就一点儿救也没有了。
好可怕呀,放着挺太平的日子不过,我出来开什么洋荤?我有时觉得,自己正一锹一锹地给自己挖陷阱,把毒藥当甜果吃。想想这次倒霉的北欧之旅,真是肠子都悔青了,唯有那一丝朦胧的副局长的憧憬还有一点儿吸引力,不然我几乎挺不住了。
彭局长用责备的口吻回应我说,那可不行,公私得分明啊。
许组长随声附和,是呀,是呀,彭局长公正廉明。
我后悔失言,但心里却骂开,装蒜!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回去我不把这钱还给他,他能饶了我?
我记下了付账的钱数,看着彭局长把VISA金卡又插回了钱夹,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很荒唐、很罪恶的念头:但愿小偷快点把他的VISA卡偷走!我悬着的心才能放下,这无底洞也就算堵上了。
芬兰航空公司的1301航班正在下降高度,被一望无际的赤松和白桦拥抱着的万达机场跑道都看清了,一片灯光闪烁。VISA卡的烦恼暂时丢到一边,新的希望取代了让VISA卡“消失”的计划。
我们极有可能被芬兰边检局扣留在机场不准入境,这对彭局长他们来说,绝对是灾难,我却视为幸事,正好可以借外力提前给我的痛苦经历画上句号。我这人心眼儿小,存不住事儿,整天担心钱花冒了我回去无法交差,又生怕照顾不周得罪了彭局长、许组长,前功尽弃,哪有心思看西洋景,与其说整天忧心忡忡地跟在他们后头购物,不如尽早回去,我也就解脱了。
我不由得又一次偷看了彭局长一眼,他正整理领带,从衬衣口袋里摸出精巧的玳瑁梳子理顺他那保养得很好的头发,一脸的镇定,到底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处变不惊。我看见彭局长把看过的那份《环球时报》丢到了一边,上飞机后,我先看到了《环球时报》上那一则消息,心里忽然产生一种恶狠狠的想法,希望我们这个团倒霉。
原来,三天前芬兰海关的一位官员挡了十位中国官员的驾,声称他们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公款旅游”,这是不能容忍的。于是在边检处扣留十位中国官员二十四小时后,把他们递解出境,送回了中国,够绝的了。
彭局长对这位芬兰官员嗤之以鼻,他说,芬兰人是吃饱了撑的。谁不知道中国是块肥肉?这两年,各国争相把本国当成中国人旅游目的地国。中国人有钱了,带着大把大把的美钞、欧元涌入西方世界,开洋荤倒在其次,疯狂购物成了一道主菜,仿佛西方的货物是不要钱一样,又仿佛中国人个个腰缠万贯,让外国人目瞪口呆。难怪连北欧的商店营业员都会说几句中国话,一副笑脸、媚态招徕中国人生意。有钱就是大爷,这一点,他们也高尚不到哪儿去。
芬兰这位官员居然不喜欢中国人来花钱、消费,傻帽儿!这是我们彭局长的评价。
当他知道我的担心后,平淡地一笑,让我把心放回到肚子里去。他拍了拍紫皮护照,说,咱持的是因私护照,入境理由填的是“商务”,芬兰人怎么知道我们是官员?他说,他早防着这一手了。他确实老谋深算。他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国,绿皮公务护照吃香,外国人通常高看一眼,现在不同了,中国的官一出来,人家都不拿好眼看你,怀疑你是携款潜逃的腐败分子。说罢彭局长哈哈大笑。他的笑声冲垮了我的希望,看来,这洋荤还得开下去,我脚下的无底洞愈发显得幽深不见底。
飞机平稳降落在赫尔辛基万达国际机场跑道上。在飞机滑行到廊桥时,我打开行李箱,先把彭局长的西装上衣取下。我的手触到了西装口袋里的皮尔·卡丹钱夹,我的心不由得动了一下,那是激动,我觉得跟宣布我当选劳模和当林场场长任命令的激动心情很相近。真是不可思议。
我知道我要干出怎样出格的事情,我只能对不起彭局长了,好在他只要及时挂失,不会有什么损失,再申领一张新卡就是了。可对我的好处可大了,等于给我建了一堵防火墙,把局长的消费欲火全挡在了防火墙外!而且我又没有得罪他,怪只能怪“小偷”。
我瞥了一眼彭局长,他刚刚打开手机,正专注地给家里留守领导下指令。他身在国外却心系单位,每天不放弃遥控指挥。
我的心狂跳着,手也发抖,我仿佛真的是窃贼!可我还是成功地在瞬间把局长的VISA卡从钱夹里抽出来了,顺手插进前面坐椅的呕吐袋里,神不知鬼不觉。
我见他披上衣服前还摸了摸钱夹,毕竟没有细看每一张卡,谢天谢地。虽然才下午三点钟,号称“太阳不落之城”的赫尔辛基已是一片浓浓暮色。十二月份的北欧不是“极昼”,恰是长达二十个小时的“极夜”,我却觉得心里亮堂,提心吊胆的开洋荤之旅呈现出一片玫瑰色。
原刊责编 王小王
【作者简介】张笑天,男,山东昌邑人,1939年生于黑龙江。1961年毕业于东北师大历史系。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15部,小说集、剧本集、散文随笔集18部。小说、电影剧本曾多次获奖。小说《前市委书记的白昼和夜晚》获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现在吉林省作家协会任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