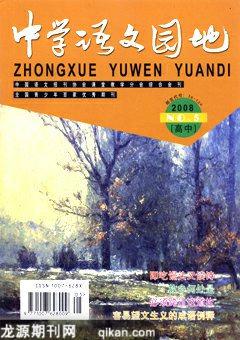寻觅“生命”
方 妤
刘亮程曾获第二届冯牧文学新人奖,他的获奖评语是这样的:“他的语言素淡、明澈,充满欣悦感和表达事物的微妙机理,展现了汉语独特的纯真和瑰丽。”然而当我面对这位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时,令我感到“欣悦感”之外的,还有一种悟透人生的深邃与悲凉。
这位蛰居穷乡僻壤多年,甘受寂寞,执著耕耘在自己“村庄”里的“乡村哲学家”,用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告诉了我们一种叫做“生命”的东西。
那么,究竟什么是生命?按照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的理解,生命固然是有机物进化过程中的一个表现,但人的生命绝不能只以生物性来规定。生命是有限个体从生到死的生活和创造的总和,它植根于人类整体的历史文化中。也就是说,作为一切事物的本源和基础的生命本体,它具有物质和精神的两个层面:生命的物质层面主要指人的生活状态以及本能的欲望;生命的精神层面主要指人为了体现生命的价值,执著地追求生命存在的意义与生命的理想境界。而这两点在《今生今世的证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刘亮程曾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写道:“我恰恰在追怀一种永远不旧的东西,过去千百年仍鲜活如我们古老的血液。旧有两种,一是转眼成旧,一是永不陈旧。我们就是靠这些永不陈旧的东西维系着千年不变的基本生活。”他所提到的“基本生活”正是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在《今生今世的证据》中得到了再现。“那是我曾有过的生活吗?我真的看见过大地深处的大风?更黑,更猛,朝着相反的方向,刮动万物的骨骸和根须。我真的听见过一只大鸟在夜晚的叫声?”这些反问句的使用,表面看似是作者对以往生活的怀疑,其实是对以往生活的再现,是创作主体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感知。一头牛、一只鸟、一堆草、几面土墙,甚至于墙角的烟道和锅头,泥皮上的烟垢和灰,都倾注了所有的生命,使生命回归本色的美丽与尊严,同时也隐含了他对生活状态最本能的欲望——思乡。
在刘亮程的村庄里,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只虫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在他那里,村庄里的一切都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他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养育他成长的那片土地。因此,对他来说,他生活的全部渴望就是“一场一场的风吹倒旧墙,刮破院门,穿过一个人慢慢松开的骨缝,把所有所有的风声留在他的一生中”。
然而,生命作为一种美好的元素,它固然有阳光明媚、鲜花盛开、流水欢歌、小鸟啁啾等值得人们留恋的一面。但由于受到环境、社会、健康等因素的限制,生命在更多的时候是以荒凉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即便是这位如此深爱着自己“村庄”的作家,他用一生的时间在心中构筑自己的“村庄”,而当我们的肉体可以跟随时间身不由己地进入现代时,精神和心灵却有它自己的栖居年代,于是“我们无法迁移它”。也正如他自己在另外一文中所说的,“在我们漫长一生不经意的某一个时期,心灵停留住不走了,定居了,往前走的只是躯体”。于是他开始了对自己生命的一种迷失。“我真的有过一棵自己的大榆树?真的有一根拴牛的榆木桩?它的横杈直端端指着我们家院门,找到它我便找到了回家的路。”需要凭靠榆木桩的指引才能找到自己的家园,这看来是多么悲凉的一件事情,但实际上这也正是刘亮程在向世人描述的一个残酷现实:在现代工业文明时代,我们物质的村庄被蚕食,精神家园也同时沦丧。人们似乎只有凭借以往的东西才能唤起对早已尘封的“家园”的回忆。
在这里,我们看到,刘亮程拒绝现实的同化,企图以独立的姿态保持清醒的存在,不屑于生活本原的恶浊,因此他用回忆以往的方式再现纯粹的传统家园;另一方面,他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根本无法摆脱社会生活的束缚,无法游离于现实之外,于是他只有默默地接受,但是却用了他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宣泄对世俗的厌恶,这也正是对生命意义的深度掘进。
关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不少作家都作过这样或那样的追问。比如鲁迅的《野草》、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斯妤的《橄榄树》等,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生命意义的探究上。或许正是因为生命本身缺乏意义,为生命创造意义便成了作家的唯一选择。
刘亮程也是这么一位作家,他也在寻找一种方式进入世界。
首先,他勾勒出了一个最为纯朴的村庄,“一只早年间日日以清脆嘹亮的鸣叫唤醒人们的大公鸡,一条老死窝中的黑狗,每个午后都照在(已经消失的)门框上的那一缕夕阳……”在这个安静传统的村庄里,人们卑微快乐、接近自然地活着:往墙上抹泥巴、刷白灰,喊着打夯的号子打墙,瘸腿男人紧追不舍……可是当“我们随便把一堵院墙推倒,砍掉那些树,拆毁圈棚和炉灶”时,这些美好的场景只能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对于今天的生活”,它们已变得毫无意义。
对于刘亮程,他当然不允许这些美好的经历成为即将湮没的废墟。于是,他开始了追寻。在追寻的过程中他发现:命运是风向不定的,生活是日新月异的,生命是稍纵即逝的;但总有一些一成不变的东西留在这个世界里,它们构成了“永恒”。而这个“永恒”就是我们永远的故乡。正如他自己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写的那样,“故乡对于我,它不仅是出生地,还是一个人的生存和精神居所。”刘亮程将故乡看成了他生命的全部,唯有抓住它,生命才有根本。因此,刘亮程笔下的“家”已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家”,它是强烈的诗性召唤,是人类心灵最后的归宿,是他在流逝的万物中紧紧抓住的“生”的“证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生。刘亮程以其独特的思维,以自己对人生、命运的理解,以追寻“证据”的方式从容不迫地回忆着一个村庄和自己的生活轨迹。把一个人生命的物质痕迹全部留住是不可能的,但它们都会长久地留存在记忆中,成为人的精神财富。这样,“家园”才不会废失,人生才不会“虚无”,生命才会永恒。
(作者单位:浙江衢州一中 )
附原文:
今生今世的证据
刘亮程
我走的时候,我还不懂得怜惜曾经拥有的事物,我们随便把一堵院墙推倒,砍掉那些树,拆毁圈棚和炉灶,我们想它没用处了。我们搬去的地方会有许多新东西。一切都会再有的,随着日子一天天好转。
我走的时候还不知道向那些熟悉的东西去告别,不知道回过头说一句:草,你要一年年地长下去啊。土墙,你站稳了,千万不能倒啊。房子,你能撑到哪一年就强撑到哪一年,万一你塌了,可千万把破墙圈留下,把朝南的门洞和窗口留下,把墙角的烟道和锅头留下,把破瓦片留下,最好留下一小块泥皮,即使墙皮全脱落光,也在不经意的、风雨冲刷不到的那个墙角上,留下巴掌大的一小块吧,留下泥皮上的烟垢和灰,留下划痕、朽在墙中的木橛和铁钉,这些都是我今生今世的证据啊。
我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曾经的生活有一天会需要证明。
有一天会再没有人能够相信过去。我也会对以往的一切产生怀疑。那是我曾有过的生活吗?我真看见过地深处的大风?更黑,更猛,朝着相反的方向,刮动万物的骨骸和根须。我真听见过一只大鸟在夜晚的叫声?整个村子静静的,只有那只鸟在叫。我真的沿那条黑寂的村巷仓皇奔逃?背后是紧追不舍的瘸腿男人,他的那条好腿一下一下地捣着地。我真的有过一棵自己的大榆树?真的有一根拴牛的榆木桩,它的横杈直端端指着我们家院门,找到它我便找到了回家的路。还有,我真沐浴过那样恒久明亮的月光?它一夜一夜地已经照透墙、树木和道路,把银白的月辉渗浸到事物的背面。在那时候,那些东西不转身便正面背面都领受到月光,我不回头就看见了以往。
现在,谁还能说出一棵草、一根木头的全部真实?谁会看见一场一场的风吹倒旧墙,刮破院门,穿过一个人慢慢松开的骨缝,把所有所有的风声留在他的一生中?
这一切,难道不是一场一场的梦?如果没有那些旧房子和路,没有扬起又落下的尘土,没有与我一同长大仍旧活在村里的人、牲畜,没有还在吹刮着的那一场一场的风,谁会证实以往的生活——即使有它们,一个人内心的生存谁又能见证?
我回到曾经是我的现在已成别人的村庄。只几十年功夫,它变成另一个样子。尽管我早知道它会变成这样——许多年前他们往这些墙上抹泥巴、刷白灰时,我便知道这些白灰和泥皮迟早会脱落得一干二净。他们打那些土墙时我便清楚这些墙最终会回到土里——他们挖墙边的土,一截一截往上打墙,还喊着打夯的号子,让远远近近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在打墙盖房子了。墙打好后每堵墙边都留下一个坑,墙打得越高坑便越大越深。他们也不填它,顶多在坑里栽几棵树,那些坑便一直在墙边等着,一年又一年,那时我就知道一个土坑漫长等待的是什么。
但我却不知道这一切面目全非、行将消失时,一只早年间日日以清脆嘹亮的鸣叫唤醒人们的大红公鸡、一条老死窝中的黑狗、每个午后都照在(已经消失的)门框上的那一缕夕阳……是否也与一粒土一样归于沉寂。还有,在它们中间悄无声息度过童年、少年、青年时光的我,他的快乐、孤独、无人感知的惊恐与激动……对于今天的生活,它们是否变得毫无意义。
当家园废失,我知道所有回家的脚步都已踏踏实实地迈上了虚无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