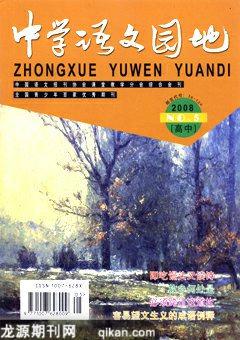巧借溪水 愤说愚贤
姚志忠
在这个世界上,正如没有一个醉鬼会承认自己喝醉一样,也没有哪个愚人会承认自己愚蠢。能自道其醉者,反倒是非常清醒的人;同样,能自嘲其愚者,反倒是十分聪明的人。因为愚蠢并不是一枚光荣的徽章,可以佩在胸前为自己增辉;但愚蠢却可以是一个群体造就的印记,烙在一个不肯随俗者的身上。若是这个人傲然亮出这种印记行走世上,就成为一种对对方无知可鄙的嘲弄,成为一种对对方邪恶可憎的蔑视,成为一种对自己不幸遭际的慨叹,成为一种对世人明辨是非的渴求。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就正是这样一篇“嘻笑之怒,甚乎裂眦”(柳宗元《对贺者》)的作品。
这篇“楚声满纸”的文章,却是以自愧、自嘲的调子开篇的。作品一开头,作者就开始了对贬谪永州后所卜居处的一条溪水的意味深长的命名。溪本名“冉(染)溪”,但到底因何而得名,“土之居者,犹龂龂然”,这种名实难考的现状为重新命名提供了契机。根据自己“以愚触罪”迁谪永州的经历,并参照古代以愚公名谷的先例,最终将这条溪水命名为“愚溪”。溪既名之曰“愚”,则周遭风物无不为“愚”所株连:小丘名曰“愚丘”,泉水名曰“愚泉”,水沟名曰“愚沟”,小岛名曰“愚岛”,又人工制作了“愚堂”、“愚亭”、“愚池”,合称“八愚”,并以诗纪之。愚溪风物其实并不愚,而且“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但山川却受人之累,“以予故,咸以愚辱焉”,故而颇感歉疚。不过通过进一步观察,作者却又发现了溪水“独见辱于愚”的特点:“不可以灌溉”,“大舟不可入”,“不能兴云雨”。一言以蔽之:“无以利世。”于是心中坦然:“虽辱而愚之,可也。”人之愚和溪之愚既然有如此多的契合点,那么因愚人而名愚溪,似乎也就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了。
行文至此,愚溪之名似已无可更改,但却有一个逻辑判断我们绕不过去:愚溪既以愚人而得名,那么“愚人”则是这个判断的大前提了,大前提若是真实的,那么这个结论也就是正确的了,名也正,言也顺。否则,“愚溪”的命名就失之草率与牵强。作者显然料到了这一点,于是搬来了两个“假愚人”与自己这个“真愚人”进行对比,以证明自己是名副其实的愚人。一个是宁武子,他的“愚”可以自我调控,“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论语》)。在包括柳宗元在内的许多人看来,这不光不是愚,而且是“智”的一种体现。一个是颜子,他“终日不违如愚”,是“如愚”,算不得真愚,甚至是一种“大智若愚”。这两个人其实都是“智(或睿)而为愚者”,“愚”显见是其处世为人的一种保护色,而能使用保护色的人本身就是“智”的。作者自己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在“圣明”之世却干出了“蠢事”,以致遭贬谪,受打击,真是笨到家了。在本文的姊妹篇《愚溪对》中,作者在面对溪神的责难时为自己作了这样的答辩,再次指认了自身之愚:“夫明王之时,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迩,伏者宜远。今汝(溪神)之托也,远王都三千余里……唯触罪摈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游汝,闯闯以守汝。”以被“明王”疏远、黜斥作为愚者必须承当的后果来逆推出自己的“愚”。如此一来,命名愚溪的这个大前提,似乎是无可置疑的了,当然愚溪这个名字,应该也是无可更改的了。
但仍有一个疑问:“愚”的标准由谁来定?众人指认这个人愚,这个人就真愚吗?历史上很多的认鹿为马以保性命、指忠为奸阿顺权贵的事不就是在“大多数”人身上发生的吗?以附和者的数量来判断真理本身就是公认的谬误。还有,自认为愚,就愚得不可置疑了吗?宁武子和颜子都曾试图给世人留下“愚”的印象,但这恰好反证出他们的聪明。而且,自认为愚,实在有太多可供咀嚼的复杂内涵与潜台词。如此一来,指认“愚人”和命名“愚溪”的前提又一次变得不可信赖,这就需要更进一步地从事实真相角度去判断了。
作者在第四段里以愚自命的理由是“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那么,所违之理者何?其《封建论》触“家天下”之孽根,逆昏君之龙鳞,为唐室兴旺鼓与呼,却不幸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谓之以愚,不亦冤乎?所悖之事者何?其积极参加王叔文“永贞革新”,期望革除时弊,重振大唐声威,却不幸败于一旦,谪于蛮荒,不亦悲乎?但在常人看来,为官而不会窥伺君主的眉高眼低,出仕而不善安保自己的锦绣前程,当然是愚不可及。就连所知甚深的文坛同道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也不乏对其“愚”的认定:“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似乎也在责怪他逞少年气血之勇,对改革的难度及失败的后果估计不足,所以失败是必然的。以成败论愚智,也是令人愤慨的世俗常法。所以这个“愚”字,既出自众人之俗口,也发自自己的愤心。柳宗元的满腔愤怒,在他的一首名为《冉溪》的诗中表达得更为显豁:“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自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一个以身许国、不为自谋的人,一个强国心切、勇于改革的人,居然横遭“愚”字玷污,天下宁有是理哉?恰如作者在《愚溪对》中借溪神之口所斥责的话:“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
事实上,作者对自己的“贤”与“智”是有着充分的认识和十足的自信的,且不论《封建论》的思想价值和“永贞变法”的历史价值已在后世获得很高定评,仅以《愚溪诗序》中借对溪水的描述来抒发自己怀抱的文字看,作者对自己的人格也作出了很高定位:“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善鉴万类”即是智,代表着对世态的洞悉,对时弊的烛见,对人生的明悟;也代表着目标的高远,志向的宏伟,胸襟的广阔。“清莹秀澈”即是洁,昭示着对私心杂念的摒弃铲除,与混浊现实的势不两立,同蝇营狗苟的一刀两断;也昭示着对自己道德要求的极高标准,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勤于拂拭,对自己为人处世的一日三省。“锵鸣金石”即是勇,不信“沉默是金”,只愿为民疾呼;不想以隐忍混世的和事佬风格换取富贵的长久和仕途的平顺,只想一吐骨鲠,指摘时弊,哪怕逆龙鳞而遭贬谪,忤权贵而遭构陷。如此集“智”、“洁”、“勇”于一身的人,却横被“愚”之恶名,岂非黑白颠倒!这个自称“愚人”的人,用自己的光明磊落,比照出了那些高高在上的自命不凡者的丑陋渺小;用自己的心忧天下,比照出了那些自诩聪明的识时知机者的自私狭隘。不用和柳宗元的“明君”和同僚比,就是和柳宗元在《愚溪诗序》中标举的两个智者的代表——宁武子和颜子比,柳宗元也还有超过他们的地方。宁武子之“愚”,亦即“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显见是明哲保身之“智”,疾风中难显劲草之姿,缺了一份为国捐躯的忠烈,少了一些除暴安良的勇气,是一种圆滑自保之“智”,为精忠报国者所不取。而颜子之“愚”,亦即“终日不违如愚”,实则是守礼自谦之“智”,恭顺中难免模棱之嫌,也就少了一种爱吾师更爱真理的胆识,缺了一点当仁不让的执着,是一种缺乏风骨之“智”,为心怀天下者所不用。他们智则智矣,只是“智”得不够负责任。至于那些迫害和讥讽柳宗元的所谓智者,他们的“智”,或出于捍卫腐朽黑暗的“家天下”的私心,或出于保护既得利益不受损害的私欲,是一种变味扭曲、因私废公之“智”,散发着“宁我负天下之人,休教天下之人负我”的腥膻之气。国家落在这样一群“聪明人”手里,焉得不江河日下,走向衰败?相比之下,柳宗元的确没有以上种种之“智”,有的只是铁肩须担道义、雄心欲挽狂澜的壮志,有的只是国家振兴、舍我其谁的责任感。这难道不是一种“天下为公”的大智吗?可叹的是这种大智却无人理解,无人回应,无人支持,“寂寥而莫我知”,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孤舟蓑苙翁”,以一种倔强的姿态去“独钓寒江雪”;成为一个满朝侧目的“愚者”,带着一身伤痛去守护他的愚溪。所以林纾评《愚溪对》为“愚溪之对,愤词也”,“发其无尽牢骚,泄一腔之悲愤,楚声满纸,读之肃然”,以此语评《愚溪诗序》,也是恰当的。
(作者单位:甘肃岷县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