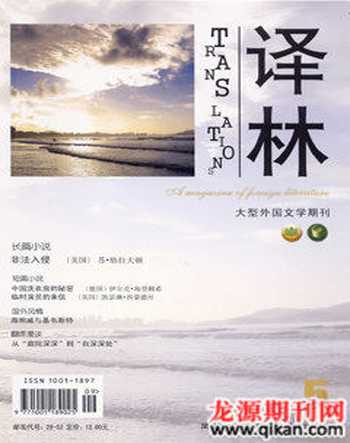朱利安·巴恩斯访谈录
冯海青 译
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1946年生于英格兰的莱斯特郡,自1980年以来,朱利安·巴恩斯就跻身于英国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群之列,他和马丁·艾米斯、伊恩·麦克伊万一道成为当代英国文坛的佼佼者。凭借其《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1984)、《英格兰,英格兰》(England,EnglandВ1998)、《亚瑟与乔治》(Arthur & George,2005),巴恩斯三度冲击布克奖;他还曾获得 “杰弗里·费伯纪念奖”、“福斯特奖”、“古腾堡奖”、“莎士比亚奖”及法国“美第契外国作品奖”(1986)和“费米娜外国小说奖”(1992)。该访谈编译自2006年2月乔治·路易斯(Georgie Lewis)发表于鲍威尔斯网站《访谈》栏目的实地采访,旨在回顾巴恩斯为创作其代表作《福楼拜的鹦鹉》、《亚瑟与乔治》所作的努力,阐明其反对种族歧视,呼吁平等、公正的社会道德主张和坚持艺术大于政治的文艺路线及师承莎士比亚、福楼拜的衣钵。
乔治(以下简称为“乔”):是什么促使你在真实人物的基础上重塑亚瑟·柯南·道尔这个人物的?这应该是你小说创作中的首次尝试吧?
巴恩斯(以下简称为“巴”):不。我在短篇小说中也使用过真实人物;而且,《福楼拜的鹦鹉》中布雷斯维特就属于真实的作家。至于为何要以真实人物作模本是因为我读了足够多但不是太多的材料。我需要足够多的材料来激活想象,而不是太多的材料来阻塞想象。要塑造像柯南·道尔这样有名气的作家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不能套用有关他的所有材料,所以写作中很难的问题就是得不断地决定材料的取舍。
乔:我想你手头的资料更多的是关于柯南的吧?有关伊德尔吉的却很少。
巴:是这样的。目前,帕西人的总数还不足十万。他们曾经是英联邦最受宠的族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德尔吉仅仅因为他的肤色而接连受迫害。在英帝国时代,帕西人被看作是很优秀的种族。事实上,在19世纪晚期,英国议会中曾有两位帕西人议员;第一支来英国的印度板球队是由帕西人组成的。他们备受尊敬的原因部分是因为他们是个商人、律师辈出的阶层,也因为他们的浅色皮肤填补了英国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空当。而乔治的父亲当年差一点就被英国圣公会作为新鲜血液吸纳。乔治遭受迫害与此形成强烈反差。乔治更多的是代表一种困境,而不是个体人。关于柯南·道尔辩护的这件案子的报道中对乔治的描写少之又少,而且各家报纸的报道有不少出入。对于这个人物形象,我得一切从头开始。
乔:你说过在研究几年前发生在法国的德莱福斯案(The Dreyfus Affair)之后,你就着手研究伊德尔吉的案子。从小说中可以看出英国各阶层因为此案而产生的情绪对立并没有法国人因德莱福斯案而造成的阶级分化那样强烈,尽管当时各阶层和宗教团体的立场很明确。英国似乎不像法国那样是个一触即燃的火药桶。你觉得这两起案件有何共同点?
巴:我认为德莱福斯案确实使法国人的政治倾向变得明朗许多。它表露了左右翼的心声,揭示了天主教和犹太教及无教派的对立;它关系到叛国行为以及军队声誉的维护。同时,也表明法国人在政治上是极易分裂和产生强烈对抗的民族。而英国人在政治划分上则相对迟钝些,他们乐于遗忘。不光彩的事情发生了,英国人把它解决了,随之就忘掉;而在法国,他们喜欢不断地将伤疤揭开,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不幸的过去。英国人不会这么做,如果不这样,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会长期处于痛苦的回忆中,因为他们没有享有英格兰人那样平等的权利和待遇。我想这部分原因应归结于国家实力。一个国家实力雄踞全球时,像当年的大英帝国,更热衷于炫耀实力,绝不会接受差异和他者文化的存在,只会蔑视它,而不像那些温善、受剥削、相对落后的国家那样去回顾历史。
乔:我很赞同你的观点。在美国政治这方面,可以说这本书出得正是时机,因为它谈论的是对一个肤色不同,被指控为恐怖主义者实施的不公。不久前,我看到一份美国国防部的声明说,迄今为止,已有一万四千名被拘留者从设在伊拉克的联合监狱获释,而哈利伯顿工程与建筑子公司新近又接受一份为修建更多恐怖分子嫌疑犯拘留所而提供三亿八千五百万资金的合同。你觉得此举和伊德尔吉的案子是否具有可比性?
巴:是的。两者都涉及种族歧视问题。比如说,你坐伦敦地铁时,看到一个长相似阿拉伯人的男子背着个大包,你会不自主地盯上他,尽管他可能正读着《古兰经》。一方面,我们说你为公众安全负责是善意的,但另一方面表现的是你的种族歧视。后来,你可能发现下一波自杀性爆炸者来自东非、哈德斯菲尔德抑或任何地方。事实上,即使我们严查部分人的护照,却发现那些引爆者却是英国本土人,你怎么解释?因此,这本书确实和当今的时事有相互印证之处。访美期间,很多人问我这本书是否是对9·11事件或者7.7事件的回应。尽管它绝对不是关于伦敦7.7事件的小说,因为它的出版日期是七月七日。
乔:你觉得艺术家有责任关注政治事件吗?
巴:我认为艺术家有责任忠于艺术。艺术因艺术家而有所不同。某些情况下,他们不应该变成政治作家;某些情况下,他们为政治而创作,但我不赞同削足适履。总体上,我认为艺术大于政治,艺术涵盖政治,而不可逆推。我的工作不是去告诉人们如何生活,提供给他们一整套道德规范或建议,或者鼓励他们与当局争斗,而是要如实地反映生活,并且用读者喜欢的方式把它讲出来。但有时不可避免地会和现实细节有出入,这时候作家就不必跟从政治导向而折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比如描写男人购物这么简单的事情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他生活在相对自由的美国,有足够的钱,他去一家大型超市;或者他生活在极端缺乏自由的东欧,由于经济滑坡,他尽全力凑够买同样东西的钱。同样的事情却折射出不同的政治影响力。
乔:为了写《福楼拜的鹦鹉》你肯定读过相关日记和书信,写《亚瑟与乔治》时也这样做吗?要想读这些第一手却属于个人隐私的材料,你有何感想?
巴:事实上,我几乎找不到任何柯南·道尔的私人资料。只看过几封信,柯南的后人似乎很不可思议。他们更热衷于尽可能多地赚钱,而且操作很神秘,回绝任何作家借阅资料的请求。我曾通过柯南的一个传记作者和柯南的主要受益人约定好借用资料的事,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后来,我索性抛开那些材料,自己创作出一个柯南·道尔来。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人授予我该人物的创作权,这本书没有被授权。毕竟,它是小说。我知道,实际上柯南写给他母亲的信还保留着,但尚未公开,其实,那时候有人正在编辑准备出版。后来,我读过部分内容,并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乔:你经常说你很推崇福楼拜。为什么说《包法利夫人》是第一部现代小说,你如何定义“现代主义”?
巴:事实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是由巴尔扎克创作的,尽管还有人说《堂吉诃德》是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这些说法都有漏洞。粗略地说,《包法利夫人》将现实主义小说推进到完美境界。不仅如此,此前的小说创作都是边创作边发表,以小说连载形式创作的。而福楼拜是第一个主张小说语言的每个句子能够而且应该像诗一样优美,流传百世,这正是小说的语言标准;其次,在结构上,他主张作家应该有全盘的创作计划,全部的次主题要与主题相呼应。它必须是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机统一体,一台机械,不仅仅是反映生活,而是一台各零部件协调运转的精密机械。更重要的是,他只是如实地描写现代生活的原貌,而不去充当道德教育的角色,所有这一切使《包法利夫人》成为第一部现代主义小说。
乔:你的解释真有说服力!几位当代作家的小说我很喜欢,当然也包括你的,像马丁·艾米斯、伊恩·麦克伊万甚至还有稍年轻些的石黑一雄。还有一些英国作家的作品,我觉得是受你的同时代作家的影响,比如乔纳森·科埃(Jonathan Coe)、鲁珀特·汤姆生(Rupert Thomson)。哪些作家影响了你?你认为你的同辈也受到了那些作家的影响了吗?
巴:这个问题难回答。我可以罗列出我成长中读过的作品作家名单,包括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伊夫林·沃(Evelyn Waugh)、阿道司·赫胥利(Aldous Huxley)、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等,但我总是不很清楚他们对我的创作具体影响在哪里。莎士比亚和福楼拜的确影响了我。你还可以列出一长串有名作家的名字,但作家本人是最后一个看出哪些是从别人那里套用来的。我们这代英国作家的特征是他们关注不同的方向,而且和前辈们关注的方向不同,尽管也有例外,如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或威廉姆·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和其他独树一帜者。马丁·艾米斯坚定地注视美国,而我则锁定欧洲大陆,我的作品充满着法、俄和英国元素。另外,还有拉什迪、石黑一雄和其他一些年少时就移民英国的作家,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并把本土文化带进来。拉什迪曾开玩笑地说:“英帝国文学创作在退步。”但很多人信以为真。我觉得当代英国作家过多地关注其他国家,同时又有些移民作家走进来,因此,英国文学现在相当混杂,我们各自为营搞创作,不属于同一个流派。
(冯海青:山东农业大学外语学院 邮编:27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