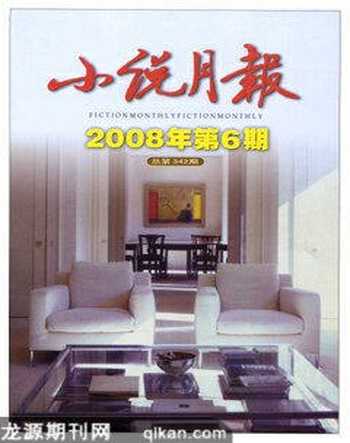延误
阿 成
情况突然出现,我必须马上出发。
过去每次绝早出门,我都会在头一天跟出租车司机定好,早晨6点在小区门前接我。我是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老主顾了,多年来,他一直负责送我出远门,非常守信,非常准时,价钱也合理。不仅如此,只要我在异地(怎么会是异地呢,那儿是我常年居住的城市啊,故乡啊,此地才是异乡呢),事先给他打一个长途电话,他就会准时到机场接我。但这次不凑巧,这个出租车司机已经事先定好了另外一个客人了,这样,我只好临时又找了一个出租车司机送我。
这个出租车司机也是一个东北人——东北人和东北人之间无论他们身置何处,都是有共同语言的。在去机场的路上,我们聊了许多对海岛的看法,我深深地感觉到,他似乎对这里的一切都很适应了。他跟我讲,现在他最不能理解的是,他的父母为什么一直嚷嚷着要回东北老家,而且死活也不愿意在海岛待了。
就在我不胜感慨、频频点头的时候,另一则信息突然像一道闪电一样划过了我的脑海。
我说,据说今天沿海一带有台风,叫什么“圣帕”,而且是14级的狂风。
出租车司机看了看外面说,不能吧。
我说,昨天晚上的“天气预报”报的,我估计还是有的。
说着,我不无担忧地说,就怕我这趟飞机起飞不了哇。
司机又歪着头向车窗外看了看,没说什么。
到了机场,付了车钱,我便提着那个巨大的空的旅行箱走进候机大厅。在换票柜台那儿,我很快发现,前面有一个庞大的来自宁波的旅游团和我同乘一班飞机。这趟航班在中途还要经停宁波和沈阳两站,最后到达哈尔滨。上帝哟,天气预报说,那个名字叫“圣帕”的台风就是在宁波一带登陆,并且就在今天上午。这就相当让人悬心了。天气预报的特点是时准时不准。但愿它今天不准,不然,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时候,值班柜台已经开始换登机牌了。我排在这支庞大的旅行团队的后面。我虽然心存侥幸,但仍然觉得没把握,如果换了票,万一因天气的原因,飞机不能起飞,那我就困在这里了,那可就误了我的大事了。要知道,今天我必须赶到哈尔滨,好在明天去办理那件大事——明天是最后的限期。这件“突然”发生的事,昨天一早我才知道的(这得感谢互联网)。如果明天耽误了,我就将继续停留在今天之前的那种生活状态之中。
这件“突然”发生的事,眼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对这件事情采取了绝对保密的态度——我就是这样性格的一个人。在文学界很多人都具有这种性格。千万不要以为个个都很简单,都是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记得有一位很著名的诗人说我:“阿成,像一颗深水炸弹一样。”尽管诗人的话并不全对,但细想一下,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我对家里的女人说,我必须马上回哈尔滨开一个重要的紧急会议。笑话,我能有什么重要会议?重要会议会找我吗?绝对不会的。但是,再成熟的女人也会相信男人们的这种话,一个男人一生中应当有许多重要会议要开,这很正常,也很自然。再说,很多单位在一年当中得有好几次一惊一乍的事,比如会议通知。
只是,眼下正是旅游旺季,飞机票相当不好买。不过,最终我还是买到了一张,无非就是9折呗,无所谓。
在海岛出发之前,女人快速地买了一大堆的海鲜让我带回哈尔滨去,给我和我女人的那些清贫的、多年来一直靠政府救济金生活的亲属们尝一尝,突然地改善一下他们的生活。其实呢,我认为,没有海鲜的生活也是生活。这何必呢。但是,女人坚持,态度又非常什么,那好,那就带上吧,反正是托运,反正是直航,不用转机。如果选择转机的航班,就会在中途耽误时间,那样海鲜就会坏掉。但是,当昨天晚上看“天气预报”得知东南沿海一带有强台风,而且是14级的时候,我当即决定,不带这些海鲜了。理由是,万一这场台风影响飞机起飞,或者影响在中途降落,那这一大堆海鲜坏掉了,我怎么处理呢?形象肯定非常狼狈吧?家里的女人嘲笑说,不可能,天气预报准不准不说,强台风也不一定非让你赶上。你还是带上吧。我想了想,还是坚持没带,包括两只当地的纯绿色鸭子,这些扯淡的东西一并被留在了海岛上。女人的话有时候可以听,有时就可以不听。有些事可以让女人知道,有些事就不能让女人知道。男人之所以称之为男人,贵在四个字上:固执己见。
我一直磨磨蹭蹭地排在这个旅游团队的最后面(我是有意识这么做的),等着这一大堆(有一百多号人)宁波人办完了手续之后,我才走到柜台前,换了登机牌,并把那只巨大的空箱子也托运了。
换票员吃惊地说,你这只箱子里什么也没有啊!
我说,不,里面有两个迷你小音箱。电脑用的。太大了,只能托运。
换了登机牌之后,我并没有马上去过“安检”。我有一种感觉(当一个人犹豫不决的时候,还是相信自己的感觉吧),总觉得这趟班机会因为天气的缘故不能正常起飞。
大约过了10分钟之后,果然让我不幸言中,机场的电脑屏幕上打出一行套红大字:飞机延误,?菖?菖航班不能按时起飞。我立刻冲到值班柜台前,向值班小姐询问,那么,?菖?菖航班何时能起飞?飞机不能起飞是不是因为台风的缘故?
在值班小姐的旁边站着一位着机场制服的年轻人,看样子他是一个负责人。他说,目前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估计您说得对,有可能是因为台风的缘故这趟航班才延迟了。
我说,那怎么办?我有急事。
他平静地说,对不起,那就得等了,没有别的办法。
我说,你听我说,如果我把票退掉,这个这个,再买一张去北京的机票,然后,再从北京飞往哈尔滨怎么样?
他立刻说,没有问题,立刻就可以给您办。
我说,可我的行李已经托运了呀。
他说,那也没有问题,我可以帮您把行李取出来。
接下来,在这位年轻人的协助下,我退掉了先前的机票,又随着他去了另一个柜台购买了一小时之后飞往北京的机票。
拿到机票之后,我顺便地询问了一下,有没有北京飞往哈尔滨的机票?
服务小姐查看了一下她的电脑,然后说,有。
我说,好。
当我正打算离开的时候,突然想,我应当把北京飞往哈尔滨的机票也一块儿买了,这样不就方便了吗?一定要像一个特工那样把事情做周密了,一环扣一环。
我立刻返回到那个柜台,对服务小姐说,我把北京飞往哈尔滨的机票也一块儿买了吧。
她说,好的。
这位小姐查了一下电脑之后,无奈地告诉我说,对不起先生,北京飞往哈尔滨的机票已经一张也没有了。
我说,这不可能,刚才不是还有吗?
她也有些不解地说,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刚才还有三张呢,怎么转眼工夫一张也没有了呢?
我说,从北京飞往哈尔滨几乎每小时都有一趟班机,怎么会没有了呢?!你再查查。
服务小姐说,先生,不用查,肯定是没有了。你可以到北京去买,估计北京会有票的。
…………
这时候,那个年轻的机场工作人员已经把我的行李找回来了。
他笑着说,你的行李挺空,好像里面什么也没有。
我说,有,有两个电脑小音箱。
于是,我开始重新办理登机手续,过安检。当我走进安检区候机厅之后发现,机场的地勤人员已经开始给宁波的那伙旅客发早餐了。看来,他们这一上午是走不了了。我暗自庆幸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男人嘛,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当机立断是重要的品质。
由于早晨出来得太早,没有吃早饭,我决定到机场餐厅去用餐。
在机场餐厅我要了一碗面条。机场餐费的价格从来都是昂贵的,但是,我们只能面对。这就像个毫无反抗能力的人面对抢劫一样,只能屈服。
机场餐厅里只有两三个人。我选了一个好一点儿的位置坐了下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嘛。我发现,离我不远的那一对男女已经较起劲来了,那个男士戴着一顶条格呢子的前进帽,在这个炎热的海岛上还有人戴这种帽子,真是不可理喻。看来人生太丰富了。
离登机的时间还早,我一边慢慢地吃面,一边观察他们——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嘛。后来,那个女士腾地一下站了起来,气哼哼地走了。那个戴前进帽的男士坐了一小会儿,并朝着我这边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之后,也起身跟了出去。
我当然知道,普通人生活的改变不是在这里,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无论你采用怎样的出格的打扮,都无济于事。这就是生活。
我慢慢腾腾地将一碗面条吃光之后,一看表,差不多快到登机的时间了。很好,看来一切都非常顺利。
上了飞机之后,我前排的座位上根本没有人,于是,我离开自己的座位,选了前面那个三人的空座坐了下来。这样舒服一些——人活着不就是为了舒服一些嘛。
安顿下来不久,飞机就起飞了。估计三个小时以后就能抵达北京。没有问题,哪怕是从北京出发,半夜到哈尔滨也毫无问题。只要我明天一大早,人在哈尔滨就一切没有问题了。我新的人生旅程也将从此拉开序幕了。
飞机稳定地航行在万米高空之上,我拿出了那本书——长篇小说《秘密特工》,这本书我已经看了一半了,讲的是英国军情五处内部出现了鼹鼠的事件。我喜欢看侦探和特工的小说,而且看的时候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作者编造的,我认为作者讲述的都是真实的事件。说心里话,我对当代文学作品中的那些婆婆妈妈的事情并不感兴趣,男人嘛。我觉得读者的口味自然是多种多样的,酸、甜、苦、辣、咸;喜、怒、哀、乐、悲、思、恐,各有所好。中国的男人不喜欢看侦探小说,那是一种缺失。如果诺贝尔文学奖由我来评,我全都评侦探小说。英国女王和我这个布衣一样也喜欢看侦探小说,那她会投谁的票呢?我认为肯定是侦探小说。
严格地说,大事在即,使得我在飞机上的阅读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常常让我从惊心动魄的情节中走神儿。但是,我毕竟是一个经过风刀雪剑,屡遭磨难的人,我已经修炼得对任何好事都持怀疑态度了。我认为太好的事不会轮到我头上。这我都习惯了,不是哀莫大于心死,而是笑嘻嘻地面对这一切,过好自己有滋有味的日子。当然,那些好事不可能对自己一点触动也没有,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仍然怀疑它——因为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嘛。怀疑所有的好事使我变得心安理得。在生活中,我不是在战斗,而是在适应。
非常感谢这本惊心动魄的长篇小说——因为我看得非常细,有的地方我要反复地看一看,直到把它搞清楚为止。是啊,当一个看客有多么的幸福。当我看完了其中的三分之二的时候,飞机已经到达北京了,落地了。
北京属于北方,天气比海岛凉一点,但这个月份彼此也差不多。下了飞机,我迅速地取出行李,然后直奔售票大厅。我发现整个的首都机场有点空,不像平常那样人多得像群众集会似的。我感到事情有点不妙——世间不好的事情,通常能从发空的火车站和机场中感觉到的。
到了售票大厅,我被那张毫无表情的女性的脸告知,连一张飞往哈尔滨的机票也没有了,所有的航班全部满员。
我问,小姐,退票有没有呢?
她站了起来,指着对面的那个柜台说,您要等退票,先到那个柜台去登记。
我又立刻来到退票柜台。退票柜台的那个英俊高大的像军情五处的特工似的工作人员,见我拖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说,不行,先生,因为等退票需要随时有随时走,到时候您再托运行李就来不及了。再说,今天等退票的希望不大,上海方面有一万人因台风的原因,全部滞留在机场不能登机。
我问,是圣帕台风吗?
对,没错。
我说,这么说,我今天走不了啦?
他说,对,飞机是走不了,想想其他的办法吧。
正当我茫然四顾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小伙子走了过来,他小声地问我,要不要票?今天的。
我说,哈尔滨的有吗?
他说,只有头等舱了。
我问,几点的?
他说,下午3点。
我说,好。多少钱一张?
他说,每张加400元。
我说,太高了吧,200吧。
他说,不行。
我说,300。
他坚定地说,不行。
我说,不商量?
他说,不商量。今天票太紧张了,刮台风嘛。
我说,那好吧。
于是,他把我带到大厅的一角,领到那几个鬼鬼祟祟的人面前,跟其中的一个胖子耳语了几句之后,那个胖子立刻掏出手机拨号,估计是联系票。在联系票的过程中,给我的感觉,他很不耐烦。他很不满意地又联系了好几个地方。我隐隐约约觉得票有点儿悬。
果然,他告诉我说,日他大爷的,没了,一张也没有了。今天的票太他妈的抢手了。
我说,那就算了。
接下来,我开始打电话联系火车,得到的回答是,今明两日开往哈尔滨的火车票全部售光。妈的,今天真的是走不了吗?我马上又给哈尔滨的一个飞机售票处打电话,那儿是我的老关系了,我想请他们给我订一张明天一大早儿飞往哈尔滨的机票。对方说,明天早晨最早的一班只有9点钟起飞的。
我说,行。
既然走不了了,剩下的就是联系住处了。这时候,我想起了北京的那个朋友。过去,我经常跟这个朋友开玩笑,总给他打电话说,我就在他家楼下呢。这次,他接到我的电话之后,照例以为我在开玩笑。当我把情况说清楚后,他说,你打车过来吧。
这时候已经是下午2点了,我发现我已经是饥肠辘辘饥饿难当了。按说,到了这个岁数不会因为少一顿饭而搞成这种样子。太可爱了。
走出机场,我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朋友那里。心想,明天绝对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吧?哈尔滨又不靠大海,又不会刮什么台风。但是,雾呢?雨呢?霹雷闪电呢?这都是延迟飞机起飞的因素啊。不过不会的,肯定不会。
出租车往城里开的时候,我隐约感到司机绕路了,但是,一路上我跟司机聊得很好,绕就绕吧。
我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首都机场这么空,几乎没人。
他说,一点儿没错,今儿我们也没啥客,拉不着活儿。听说南方很多飞机都延误了,这边既飞不过去,那边也飞不过来。
我说,怪不得呢。
司机说,这出门呀,有时候顺,有时候就不顺,很正常。人到哪儿都是一个待,着急干吗呀?没用。
我心里想,同志哥,绕道的朋友,老哥哥我有急事啊。
后来我才听说,这场名字叫“圣帕”的台风来得非常猛烈,别说飞机飞不了,连鸟也飞不了了。
我的这位朋友是一个东北哥儿们,在北京搞古董生意。北京人喜欢这个,上当也喜欢。这哥儿们和我十年前就是非常不错的朋友,现在他在北京干得非常成功,人也变得仗义起来。并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为富不仁。他这里几乎成了我的一个私人驿站,而且一切免费。
安顿下来之后,他请我吃饭,给我这个不速之客接风,压惊。他要了一大桌子菜——这是他的作风,还特意给我要了一个海参,让我补一补,说海参有疗心压惊的功效。这个说法非常古怪。
吃过饭之后,我们回到宾馆聊天儿。聊到天黑了的时候,我建议他在宾馆里住算了,因为他在北京也是单身。开始他答应了,后来他接了一个神秘电话,就说:“我他妈的在这儿睡不好。”意思是他必须回去。
我说,那就请便吧。
他说,明天早晨我来送你。
我说,那就不用了。
他说,那成什么事儿了,我这个人做事从来有始有终,明天早晨4点我过来送你,就这么定了。我必须安全地把你从我这儿送走。知道不?
真不知道我身上什么地方暴露了我内心的秘密。
我说,6点钟出发去机场就来得及,你来这么早干吗?逃跑哇!
但是看到他那副坚决的样子,我就没再说什么。
临走,他把客房的房门已经开了一半儿了,又突然站住了,慢慢地回过头来,看着我问,兄弟,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心事?
我立刻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没有,没有,快走吧。
真没有?
真没有,我骗你干吗。
他说,有事你就吱声。不行,就在我这儿躲几天,北京郊区咱也有窝子。安全。
我说,你看你都说到哪儿去了?你这是夸我呢?
他说,你记住,我永远是你最可靠的朋友,有事随时电话联系我,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我说,你都快把我的眼泪说出来了。好,哥们儿,就这么定了。
他走了以后,我开始看宾馆提供的《北京晚报》,我从厚厚的一大沓子报纸中发现,北京也挺叫人闹心的,事情纷杂,乱乱糟糟。大约过了12点之后,我才睡了过去。我刚刚睡着不久就听到了敲门声,一看表,才凌晨3点钟,这小子就来了。
他一进门就说,我给你煮了10个鸡蛋。
我说,你他妈的以为这是在晋察冀边区呢,十送红军哪?
他说,这是绿色鸡蛋,是吃虫子的鸡下的。
…………
因为时间还早,我们就躺在床上聊天儿,天一句,地一句的。聊到差不多到点的时候,我们才离开了这家宾馆,然后在附近找了一个24小时营业的粥铺,吃点儿早餐——这位东北哥儿们照例要了一大堆扯淡的菜。其实,这时候什么也吃不进去了,就是一个浪费。既然要了那也得吃啊。
整个粥铺除了我们二人之外,还有几个年轻的男男女女的凑在一起吃,看一眼,就知道他们是从事非法职业的那一类人。看来,北京的凌晨也挺复杂的。
吃过早餐之后,这位东北朋友把我送上出租车。我临上车的时候他还一脸阴沉地对我说,兄弟,没事儿吧?
我说,没事。
他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到了机场,一切都非常顺利,登上飞机,我又拿出那本侦探小说继续看,一直看到哈尔滨。
到达哈尔滨的时间是中午。一切还来得及。我一边往外走一边打电话,询问对方下午几点开始办公。
接电话的这个男人说,下午2点。你有什么事?
我说,我买的彩票获奖了,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还行,今天是最后一天,我刚坐飞机从外地赶回来……
对方说,你买的是什么彩票?中的是几等奖?
我说,H彩,一等。
一等?哪一期?
哎哟,哪一期是吧?这我得看看。
…………
原刊责编 张启智
【作者简介】阿成,原名王阿成,男,山东博平人。著有长篇小说《咀嚼罪恶》、《扭捏》等六部,中短篇小说集《年关六赋》、《胡天胡的胡骚》等二十余部,散文随笔集《哈尔滨人》、《春风自在扬花》、《胡地风流》、《馋鬼日记》等十余部,电影《一块儿过年》,电视纪录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上、下集)等。其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多国文字。短篇小说《年关六赋》获198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赵一曼女士》获中国作协首届鲁迅文学奖,《秀女》、《丙戌六十年祭》分获本刊第十一、十二届百花奖。现任黑龙江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