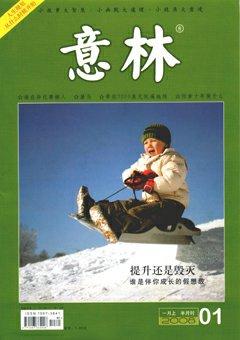“慎终追远”式的温暖
2008-05-14 04:15文怀沙
意林 2008年1期
1986年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编辑在库房整理过去的旧节目时,无意中发现了我在上世纪50年代讲解《诗经》的录音磁带,他如获至宝般地将这盘珍贵的录音编成了节目。但在介绍作者时,却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在别人那里听说文怀沙在“文革”中早已作古,便在文怀沙名字前面加上了“已故”两字。节目播出后不久,立即引起了震动,我在上海的哥哥知道后尤为震惊,这位八旬老人当即赶到电台去质问。
正当这位编辑陷于极度惶恐之时,来自北京的信寄到了这位编辑的手中。在另一封是写给电台领导的信中我不仅将此事看成是一种“慎终追远”式的温暖,向这位编辑和电台表示感谢,还视这个年轻人为我的知己。作为一个活人,却在身前听到了自己的身后之名,这绝对是一件再美妙不过的事。
对于人生,我的彻悟是:人生如赴宴,吃饱喝足了,就舒舒服服地回家去,这是很自然的,有什么不好呢?我的遗嘱非常简单,把骨灰顺着抽水马桶冲下去就行。夫人问:“青山绿水皆可埋骨,为何做此选择?”我说,骨灰与粪便合成有机肥料,可以肥田美地。有人问:“你的儿女将来怎么祭奠你?”我答,他们只要对着大地上的高粱或者玉米鞠躬就行了,那就是我。
(张丽摘自《老人春秋》)
猜你喜欢
中国典型病例大全(2022年13期)2022-05-10
读者(2021年2期)2020-12-23
语数外学习·初中版(2020年3期)2020-09-10
北方音乐(2020年13期)2020-08-28
慈善(2019年1期)2019-03-06
知音海外版(上半月)(2017年7期)2017-07-20
读者(2017年4期)2017-01-20
饮食保健(2016年18期)2016-10-24
文史月刊(2009年9期)2009-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