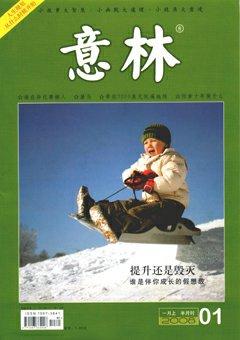内补丁
乔 叶
现在,穿补丁衣服的人几乎已经绝迹了。即使是在偏僻的乡村,补丁也已退化成罕见的奇观。而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在我生活的村庄,补丁衣服处处皆是。补丁一般都是在衣服外面贴上去的,有的方,有的圆,有三角,也有梯形。
虽然是一块小小的补丁,却也可以看出当家主妇的能耐:补丁颜色与衣服颜色搭配得比较协调,针脚也比较细密的,主妇多半心灵手巧,拿出来就会有人夸。而那些粗糙的主妇们,深蓝衣服浅灰补丁,草绿衣服油黑补丁,月白衣服土黄补丁……针脚也大得像赤足赶路的汉子,嚓嚓几步就缭到了头,让人说不得嘴。不过她们也不在意什么,说起来似乎也有道理:“补得再好不也还是补丁?乡下人灰里来土里去,穷讲究干什么?”
有一次,我惊奇地发现,伯父家人的衣服都是没有补丁的。伯父也是农民,家里四个孩子都上学,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也不怎么做新衣。可他们家的人真的都没有穿过补丁衣服。尤其是伯父,他会做水泥活儿,农忙时下地,农闲时上房,衣服应该是很费的,可他的衣服上居然也没有补丁,一块也没有。我就常常纳闷:他们家的衣服是什么料子,怎么就那么耐穿呢?
一次,去他家里玩,看见伯母正在做衣服,才明白了其中的奥妙。伯母当时正做的是伯父的一件冬装,基本已经收尾了。我看见她把衣服翻过来,在袖口、肩头这些易磨的部位上用同样的布料打成了双层。她用的是最小的针,同色的线,在衣服里面一根一根地连着丝挑缝,打好之后,外面是看不出一点儿痕迹的。
伯母告诉我,这是内补丁。
“你干吗不等破了再补呢?”我问。
“等破了的时候,衣服已经下了多遍水,颜色早就旧了,补丁的颜色太新,就会很扎眼,不好看。先把补丁补上,让它跟着衣服一遍遍地淘洗,到时候就一点儿也不显了。”伯母说着笑了,“你伯父的习惯也很好,出门做活儿都是两件外套,一件道儿上穿,一件活儿上穿。”
怪不得。伯母看起来是一个很木讷的人,整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心思——对衣服,也是对孩子们和伯父。而伯父也让我讶异,一直以为他不过是个粗人,没想到却是这样的体贴和疼惜——对衣服,也是对伯母。
伯母亲手织成的那些内补丁让我明白:爱的意义绝不仅是那些甜美的言辞和激情的举止,它可蕴涵和表达的太多了,而它的质量也决不受环境和对象的限制。在何时何地,这都是让人幸福的宝贵财富——即使是在那个满是补丁的年代,即使是在我贫如清水的家乡,即使是在我田野一样质朴的伯父和伯母身上。
这些厚暖的内补丁,这些坚韧的内补丁,这些隐形的内补丁,这些融进我们血液的内补丁,就这样沉默地填充着我们生命的黑洞,让我们不会被风吹冷。
它是我们的心衣。
(好客人摘自《广州日报》图/连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