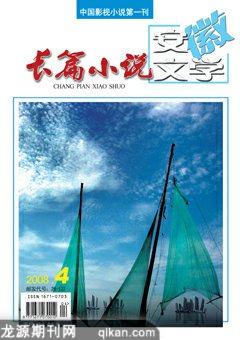游戏(中篇小说)
冷 鬼
一
瞄准。
射!
一颗子弹,又一颗子弹,又又一颗子弹……子弹们流星一般,拉着狗尾巴,你追我赶,前仆后继地穿过一片寸草不生的开阔地,在那一个像乌龟一样缩头缩脑的家伙身上开了花,花开的形状多么像一朵开得很张扬的野菊花。
莫士戈觉得太开心了,开得比野菊花还大。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连续中了多少个10环了,而且已经连过19关了。每天早上,莫士戈由于有慢性肠炎,基本上就得在卫生间的这个“宝座”上坐上半个小时,只能玩手机上的几个游戏项目:射击、赛车、贪食蛇、捉鸡仔等等。如果这一关过了,就会有一个美女作为奖品送给他,且是一个半裸的美女,只不过这半裸的美女是出现在他手机的荧光屏上。眼下第20关,而且战斗进展顺利,美女已经向他微笑着频频招手了。
突然,莫士戈的手机响了,其实是“震动”,即将到手的奖品给“震”没了。
一看“来电”知道是“她”,他心里一“咯噔”,嘴角水纹一样的笑容瞬间被紧张所替代,抬头看了看卫生间的门,虽然门已被他从里面锁了,但他还是不放心:“怎么这个时候来电?”
“你看把你给吓得,想你不行吗?”她笑着说。
“太危险了。”他说。
她仍笑,很好听:“没关系,她不要你我要你。”
“别闹了宝贝,好不好?你讲,什么事?”她喜欢他叫她宝贝。
“也没什么事,就问你‘五·一出不出去旅游,旅游的话找我,我小妹那个旅行社不错。”又笑。
莫士戈也笑了,心想:“这算什么事?非要一大早来电不可吗?这明明是找事说话。”摇了摇头又想:“女人呀!可爱也就可爱在这个地方,烦人也是烦人在这个地方。”
莫士戈拿着严肃说:“别闹了,我回头想想再说,想好了给你一个电话。”说完挂了机,挂了机呼出一口长气。
正好这时敲门声响了,莫士戈好个庆幸自己挂了机,一听却是儿子的声音:“爸爸,快点,老慢牛!”
“好了好了。”莫士戈慌忙大声说。
二
莫士戈在龙河区人大工作,丁凝雪在龙东区人大工作,再加上一个 “全市人大工作联谊会”,不错,他们的戏是从去年的冬天开拍的。
偏偏第二天上班时,就在莫士戈刚刚看完联谊会通讯录后不到十分之一秒钟,一个朋友给他发了一个祝福的短消息,谁知莫名其妙的是,他随手把这个祝福的短消息就转发给了丁凝雪。而丁凝雪呢,竟也偏偏很快就给他回了一个祝福。就这么祝福着祝福着,故事就越来越好看了,一开始他们借用了不少双关语,比如“奥妙无穷”“朦胧浪漫”等等,再后来两人之间就不需要用双关语了。再后来的后来,就到了今天上午的十点钟。莫士戈正准备给老婆打个电话,告诉乡人大来了几个人,自已上午不回家吃饭之事时,丁凝雪的电话来了。
“你早上说回头给的电话呢?”丁凝雪似乎有点生气。
“正打算给你个电话,你的电话就来了。”
“贫!”
“真的,莫士戈何时骗过你,你翻翻历史,看哪一页有莫士戈骗你的记录?”
“敢?”又说,“别绕了,问你‘五·一出不出去旅游呢?”
“出去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出去肯定按你的指示办。”
“离‘五·一还有十来天,如果出去,这两天就得到旅行社提前报名。”
“晚上我和她商量商量,估计要到北京去。”
“嗯,我想和你一块去……”
“好呀,只怕你不敢。”
“我想你了,晚上跳舞去。”不用疑问句。
莫士戈不知道,自己的老婆已经前前后后给他打了10多次电话就是打不进。莫士戈的老婆陶陶是区医院的一名漂亮的护士,夜班上得很累,想叫老公早点回家做饭;如果回不来的话,她想先休息休息,待到正午她就带孩子到她妈妈家去吃,这已成为惯例。然而,不曾想,这电话打得自己浮想联篇,篇篇疑窦,就是睡不着了。
她正欲再次“重拨”,莫士戈的电话打进来了,说:“陶陶,我上午不回家吃饭了,你和莫莫到她姥姥家吃饭吧。”
“嗯。”陶陶心里有气。
莫士戈:“早晨我买了两条鱼,你给咱妈带一条过去。”
“嗯。”陶陶心里有气。
莫士戈:“你怎么了老婆?是不是很累?要不我不在外吃了,回家亲自做饭,你亲自用餐?”莫士戈心里有鬼。
陶陶听了老公这一番暖心的话语,心里舒服多了,又想想:男人吗,整天在外面闯世界,人多,事多,电话自然就多,于是无意地说了一句双关语汇:“算了,算了。”但末了,还是问了一句,“你刚才跟谁通话,怎么这长时间?”
莫士戈心里立刻“咯噔”一下,如同微微遭到了电击,但言语上还得稳:“噢,那是龙源乡人大的一个朋友,想往我们这区人大调,问我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可能性有多大?需要哪些手续……”确实有这么个朋友,也确实这个朋友想调动工作。
莫士戈晚上终于还是没有敢与丁凝雪去跳舞。
三
“五·一”长假,莫士戈带着儿子、外甥、岳父母一行人去了北京。陶陶说北京她去过,今年就不去了,再者医院不放假,请假的话还扣工资。临走时的头一天,莫士戈与陶陶吵了几句嘴。当时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是单位的女同事打来的,说 “五·一”单位安排值日,问莫士戈想在哪一天值日。莫士戈说“五·一”自己要出去,6号回来就7号值日吧,刚想往下说时,话筒就被爱生疑窦的陶陶一把夺了去,两个人撕扯一处,毕竟莫士戈的力气大,最终把电话挂了。接着,依照陶陶的再三要求,莫士戈摁了免提回拨过去,煞有其事地问了问7号那天他将与哪几个人值班,陶陶守紧电话尖着耳朵听了,这才鸣锣收兵。
北京之行,莫士戈心神不宁,他怕陶陶这几天忽然哪根神经一发热,到移动公司去查他的通话记录和短消息记录,因为陶陶知道他的手机密码,当初买手机时是为了表示各自的忠诚才互相告知了对方的手机密码,以随时掌握情况,谁知如今作茧自缚。由于心神不宁,旅游过马路时,有两次他那高高的鼻尖子几乎与飞速行驶的公共汽车的车帮子零距离接触,惹得司机从车里探出头来骂他:“找死吗!”他想回骂:“找你妈!”但公共汽车已经绝尘而去,他强迫自己不去想这些事,旅游就是旅游,何必跟自己过不去。
偏偏北京之行的最后一天上午,6岁的外甥宝宝就不见了。岳父母大人回不过来神似的,原地转了一圈,没有看到人影,脸色立刻就急变了,岳母连呼数声“宝宝”,眼看神魂就要颠倒。莫士戈这时脑子还算清醒,嘱咐自己千万不要乱了方寸。他先劝岳父母大人不要惊慌不要着急,会找到宝宝的。然后就问儿子:“莫莫,你刚才不还手扯着宝宝吗?”
莫莫苦着小脸,手指着西南说:“那边有个风筝挂在了树上,他要去够,我不让,他挣脱了我,谁知他就不见了。”
莫士戈急得像洗桑拿浴似的出汗,控制不住自己地怪儿子:“你为什么不跟他一块去?!”举手欲打儿子,岳父母自是奋勇劝阻,异口同声地说:“不怨莫莫,不怨莫莫。”莫士戈无奈,只好撒手,抬头看那风筝,风筝还在那里挂着晃来晃去,晃得人心里发慌,可就是不见外甥——这可怎么办?若是岳父母大人再急上加愁,病了,“莫士戈呀莫士戈,”莫士戈在心里骂自己,“都是你这个混蛋作孽作的呀!你作了孽就心神不定,你心神不定就丢了小孩……”莫士戈忽然决定,如果外甥能找回来,一家人平平安安地回去,就立马和她斩断情丝,安心守着老婆孩娃过日子,再也不拈花惹草了。
莫士戈的汗刷刷地流,快流得山穷水尽了;儿子莫莫受到责备后眼泪在不停地流,流得莫士戈心里那个烦,可他心里清楚,这不能怪儿子,儿子还小,肩膀还嫩,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负荷。他劝儿子,姥姥也是不停地劝他,儿子的眼泪总算止住了。可人这么多,天坛这么大,上哪儿去找呀?去年北京丢失了26个孩子,今年偏偏他妈的就丢到我们家了!我他妈的算是倒霉透顶了呀!
真是烂眼子肯招灰。
莫士戈撞头找不着硬地,他让岳父母守着原地不要动,自己带着儿子继续找。他们像两只无头的苍蝇到处找,又到处找不到。他骂,不知不觉就骂出了声:“这个狗儿!这个龟儿子!他妈的,以后到哪去都不能带你了,简直是个累赘!你这个狗日的上天了吗?可天上没有,你他妈的入地了吗?可这地……地地……地平面上都是人,就是他妈的没有你……”
随着时间的推移,丢失的可能性也正以几何倍数迅速增长,莫士戈的绝望像气球一样也正在疯狂膨胀,快要接近爆炸了……
正在这时,儿子突然喊了起来:“宝宝,宝宝,宝宝……”
宝宝正从一棵大树后面拉了屎徐徐地站起来,全不知道刚才是如何地急风骤雨。
莫士戈的心“哗”地就解放了,冲天骂出一句:“你他妈的还知道害羞!”又露出笑补充骂了一句:“你他妈的还不知道‘羞字怎么写就知道害羞了。”
下午,他们跟着旅行团登上了返程的火车。刚安顿好老老少少不久,莫士戈收到了陶陶的一个电话,陶陶问:“该回来了吧?”莫士戈说:“已经在火车上了。”陶陶说:“那好,一件事得等你回来抓紧办。”莫士戈的心立刻咯噔起来,问:“什么事?”陶陶说:“算了,回来再讲吧,你们也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说着,陶陶要儿子接电话,娘儿俩在电话里亲热了好一会儿,儿子甜甜的话像五彩的鲜花般铺天盖地地绽放。
“到底是什么事呢?总不会是离婚吧?”一路上,睡在上铺的莫士戈却浮想联翩。
四
原来是儿子演讲的事。
早上一睁眼,莫士戈就想好了上午一定要做两个好吃的菜,献给妻子和儿子,以减轻自己的罪过,什么“清蒸桂鱼”、“猪脑汤”已经呈现在他的脑海里,儿子爱吃土豆丝,那就再来个“土豆丝烧肉”,妻子爱吃青菜,那就再烧个“蘑菇青菜”,当他把这些采购齐并运回家时,已经逼近上班时间了,他立刻又匆忙地骑车向单位而去,签了到他就立刻来到距离自己很近的宣传部办公室,找到宣传科长鲁文山。40多岁的鲁文山正在自己办公桌的座位上,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报,还一边品着茶,悠悠哉哉,神仙一般——江湖人称“鲁神仙”。
莫士戈说:“鲁科长,你好,挺忙的呀?”
鲁文山其实已注意到了来人,但仍装出浑然不知的样子,慌忙站起,说:“哟,是莫主任,你好你好。”握手之后,莫士戈便把烟让上去,鲁文山一看烟还不错,自然就接了,问:“莫主任有什么事吗?”
莫士戈就把儿子要参加读书活动演讲的事说了。
鲁文山说:“哟!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报名就快截止了。”又说:“你儿子在哪个学校?”
莫士戈答:“在二中。”
鲁文山说:“二中?二中已经报过名了。一个学校只能报两名,二中的两名学生‘五·一前就报来了。”忽地想起什么似地又说,“记得你儿子去年在全区得第一,他不是在三中吗?”
莫士戈说:“后来转到了二中。”接着说,“那怎么办?有什么补救办法吗?”
鲁文山摇了摇头说:“没有什么办法,要不,下一年再参加就是了。”
莫士戈心想你鲁神仙说的好轻巧,全不顾我的感受。忽地想起了什么,说:“我儿子在二中是小班,是个初中班。二中不是没有初中都是高中班吗?二中的几位老师就组织个初中班,主要教二中教师的子女读书,当然还有一些非常关系的人把孩子放在这个班里学习。我想,这个班应当不属于二中管理。”
鲁文山听明白了,问:“这个班的校名是什么?”
莫士戈说:“我打电话问过孩子的班主任,班主任说这个班也没有单起什么名字,顺嘴就叫了二中小班,学藉在育英中学。”
鲁文出说:“那你就到育英中学,开个证明,盖个印,把名报来就行了。”
莫士戈听了很高兴,说:“多谢鲁科长。”又问,“演讲稿怎么准备?”
鲁文出说:“哟!那你还得抓紧时间准备稿子呢,下个星期天我们区就要进行比赛,中小学各取男女生的第一名到市里参加下一轮比赛,按照这个规则选拔直到中央;你儿子的稿子你就自己写不就行了吗,你莫主任也是个才子,写这点东西还不是小菜一碟吗。你看你儿子发的有没有《红色之旅》这本书,就是根据这本书写一篇爱国主义的文章,你再参考一下网上的文章不就行了吗。”
莫士戈得到这样的指点,谢声连连地到育英中学去了,很快就取来了报名证明,
之后,莫士戈想了想没有什么事了,就心里说:“这会我得到移动公司去,不能再拖了,万一陶陶先去看,那麻烦可就大了。”
莫士戈匆匆忙忙地来到移动公司,在那个查询电脑里输入自己的手机密码,电脑毫不客气铁面无私地告诉他:已在2007年5月8日8点45分查询过。
而现在,9点45分。
莫士戈立时傻了眼,头脑“嗡”地一声就大了。
五
儿子不在家,想必已经被陶陶送到姥姥家了,看来陶陶已经作好了战前准备。
莫士戈腆着脸捧着笑问:“怎么还没有做饭?”
陶陶坐在那里,沉着脸不出声。
莫士戈向其它屋里看了看又问:“莫莫怎么还没回来?”
陶陶仍然一言不发。
莫士戈上身前倾45度向着陶陶说:“陶陶,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吗?”
好!这话像打火机,正好点燃了陶陶心中的炸药包,陶陶用眼睛狠狠地刺着莫士戈,导火索在“哧哧”燃烧着。突然,陶陶把手机清单狠狠地砸向莫士戈的脸,清单随即散落一地,一条子一条子的,长长的,似乎比长城还要长;而且还狰狞地拧动着,如同花蛇一般。莫士戈再也不问来问去了,一言不发,等待暴风雨的洗礼。
陶陶咬着牙拍着心说,“这这这!这不舒服!”又说,“你还是人吗!你与那个臭婊子丁凝雪都干了什么?!”
莫士戈装着若无其事,于是必须振振有词:“陶陶,你怎么这个样子?我可以对天发誓,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都是正常的朋友关系。”
陶陶嘲弄道,“都是正常的朋友关系?听口气好像已经有了心里准备。”又说,“我什么样子?我样子不好,你找她去好了,你找那个臭婊子去好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我们不过了!”
看着陶陶痛苦不堪的情状,莫士戈心里亦是十分难受,他赶忙过去要抱住陶陶,不曾想,陶陶抬手给了他一耳光。
莫士戈的火一下子给打了出来,随手把一个茶杯摔在地上,吼了一声:“你还有完没完?!”
“没完没完,我就和你没完!”陶陶的火气更大,火苗快舔着头顶楼板了,她也随手摔了一个茶杯,“啪”地一声,更是惊天动地。
莫士戈一看这境况,知道自己不能硬着来了,就软了口气说:“陶陶,我们之间确实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外乎唱唱歌,跳跳舞,都是正常的异性交往……”
陶陶不容他说完,质疑道:“正常的异性交往?鬼才相信?!”指着地上的电话清单,又说,“这有时一叙就是半夜、一夜,孤男寡女,彻夜长谈,说到天上去,问问天相信不相信?!”
莫士戈拿出很诚恳的表情和口气说:“你可以随便,或者任意想象甚至曲解我们的谈话,但我可以举着良心说,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这一点我问心无愧。”其实,他心里别提多愧疚了,可他又想想,若和盘托出,只怕事情更糟,对陶陶的打击更大,所以只能亏着良心说了。
陶陶说:“你编,你就编吧!我回来告诉她老公,我看你还编不编?”
莫士戈就怕陶陶用这一招,急忙道:“陶陶,我说的全都是实话,我没有骗你,我心里只有你,我永远只爱你一个,我与她叙话时我也说过很爱自己的妻子和儿子,我们之间决不能做出任何一点越轨的事。”莫士戈是对丁凝雪说过“很爱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的话,可后一句他没有说过。不过,莫士戈对妻子的感情也确实很重,毕竟是10多年的夫妻了,毕竟是情投意合的伴侣。可男人,这个雄性动物,在这个花花世界里,对雌性总是有种潜在的猎取欲;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是他们常有的表现。一锅一锅,他们恨不得锅锅都被自己吃了。
陶陶不作声,莫士戈又说:“你要是告诉他老公,他老公肯定也不会冷静的,虽然我们没有做什么丑事,可你想想你作为一个女人都这样,他老公必然会做出一些愚蠢的举动,一旦搞得沸沸扬扬,我还怎么在这个社会上混?还必然会影响到我的工作。”莫士戈换口气继续游说:“再说,你不同意我们有来往,我们以后不来往不就行了吗?”又说:“陶陶,你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经常通话并发短消息,尤其是有时在电话里一叙就是半夜,我现在想想,这是有点过了,这是我的错。我得承认,我有时有点心猿意马,可我还是管住了自己,我毕竟没有越过那条线,我以后重新梳理梳理自己,尽量不与女人接触,即使接触,一定把握好度,让老婆永远放心……”这一番话陶陶听了受用了一点,但也只是一点而已,待莫士戈停下来的时候,她语气虽稍有缓和,但仍是字字如铁,不留情面,“你现在知道怕她老公闹了,现在知道要脸面了,那你当初干什么去了?”又说,“你说的话我能相信多少?你说你没有做什么丑事,可孤证难立;原来你说什么我信什么,可现在这种诚信度给你破坏了……”陶陶也是很爱莫士戈的,也不想家庭破裂,气也消了一部分,说这些的目的一是发泄,另一方面是给自己的老公上紧箍咒,免得以后再惹是生非。但由于事情的突然,对她的刺激也不小,脾气阴睛不定,时好时坏,有时发着狠要把这事告诉人家的老公,有时又答应不告了;有时激动得非要与莫士戈离婚不可,有时又说原谅了老公……总之,这一番闹,闹得中午饭没吃成,闹得下午班没上成,直闹得儿子莫莫欢欢跳跳地放学回来,才暂告一段落。
六
眼看儿子的演讲比赛越来越近了,可莫士戈还没有把演讲稿拿出来。话说回来,他又哪来的心情写演讲稿,心灵已经被陶陶捣得七零八碎。他开始失眠了,他第一次尝到失眠对身心的摧残,第一次尝到痛苦是什么滋味,他感言:黄连的苦与这种痛苦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那是小蚂蚁与大象相比。但是陶陶还没善罢甘休,还在导演着这种痛苦的继续,还在拉大小蚂蚁与大象的差距,她也是思之又思,认为暂时决不能宽容莫士戈,一定要让莫士戈从骨髓里感受到偷情的痛疼,俗话说:恶病还需猛药治。惩罚不到位,老病会复发。昨晚,陶陶又走出了一招,出乎意料地把莫莫的姥姥找来,岳母也是没有客气,狠狠地刮了刮莫士戈的脸,莫士戈的脸青一阵紫一阵,汗都被岳母用语言一滴子一滴子地刮了下来,血也快被刮出来了。怎么办呢?莫士戈没办法,心里想自己作的孽只有自己承受了。
问题是光承受还不行,还得带罪立功。陶陶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儿子的演讲拿不到好名次,就拿他莫士戈是问。因为去年儿子的表现就非常好,斩将夺魁,到市里也取得了很优秀的成绩,最后参加了全国的中小学夏令营活动,把夫妻俩骄傲得在家门口几乎迷失了方向。去年在这个时候,儿子的演讲可以说基本准备就绪;今年可好,到现在演讲稿还没有着落,再有6天比赛就开始了,这可把两口子急坏了。而陶陶呢,自然是把这一切都归罪于“莫士戈在这个时候出的这个破事”。可莫士戈呢,他又能去怪谁呢?他只能怪老天爷“屋漏偏逢连阴雨”。最后,莫士戈不得不请一位作家给儿子写了一篇演讲稿,之后又马不停蹄地请人辅导。
还好儿子在全区的演讲比赛中,力挫群英,光荣地把第一名拿了回家。
第二天,莫士戈接到宣传部鲁文山的电话,要他下午五点带儿子到宣传部会议室,几个部长想听听孩子的演讲,大家再会诊会诊,让孩子再提高提高。莫士戈听明白了:鲁文山的意思就是为这个星期天市里的比赛争取更好的成绩。
然而,下午莫士戈如约带着儿子来到宣传部时,心里却犯了嘀咕。因为按照比赛规则,前面已经讲过的:参加市里比赛的选手心须是区里的小学组的男、女生第一名和中学组的男、女生的第一名,而眼前出现的小学组的男、女生第一名没错,中学组却来了三个学生:女生第一名,男生第一、二名。
莫士戈把鲁神仙“请”到室外,陪着小心问是怎么回事?鲁神仙心里知道莫士戈要问这个问题,他吐了一个烟圈讪讪笑着说:“有时也有个例的,再看看一、二名谁更合适些。”
莫士戈的脸一下子就变了,心想:“其他的你怎么没有让第二名来,偏偏我儿子这你让第二名来,我这些天本来就不顺,你倒好,你这不是落井下石,疮上撒盐吗?”但他没有说出这些话,他说出的话是:“噢,是这样的,那还请鲁科长多多关照,我儿子毕竟是第一名。”
鲁神仙说:“我知道我知道,还是先让领导听听孩子的演讲吧。”
两人各揣着自己的心进了会议室。
不一会儿,几个孩子都演讲了一遍。几个领导针对每个孩子的演讲分别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并又对各个演讲稿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看看天色将晚,宣传部领导又挽留大家共进晚餐。晚餐进行得看上去还算十分融洽,笑声叠着菜和酒在人们的口腔里进进出出,如同蚂蚁搬家。可莫士戈的心里的“?”像肥皂泡一样不停地往外冒,但他还得强颜欢笑十分殷勤而谦恭地把酒敬着各位,尤其是领导和那个他看上去现在让他有点烦的鲁神仙。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其他的孩子家长也在欢笑着敬酒,这场面山让心情不好的莫士戈心情更不好,所以酒敬了几番后他就有了酒意,思想被酒精泡的也异常活跃起来。但他克制着自己,强迫自己今天且不可做出什么不得体的举动来。不过,他寻思着,最好跟部长说点什么。恰好这时部长起身,估计去洗手间。一分钟后,莫士戈就把自己提了起来,并使自己移动双脚也来到洗手间。莫士戈问部长好,部长也客气地以礼回应。莫士戈看看部长即将方便完毕,心想得说了,于是就说部长怎么第二名也来了?部长和蔼地说噢,那个第二名……也可以来嘛。莫士戈又小心地说不是只去第一名吗?部长不知没听清莫士戈的话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竟说了句是只去一名的。说着,部长洗了手就走了出去。
莫士戈一头的雾水。
七
说着说着就到了星期三。莫士戈早早地就醒了,觉得身上好难受,一下床有点头重脚轻。莫士戈想这是感冒了;又想现在怎么可以生病呢?现在因病休息陶陶又该嘲讽是玩情人累的了。于是心中不禁有点酸痛感,自言道:这人呀,是不能犯错误的,犯了错误连生病的权利都给剥夺了。
莫士戈不得不早早地又来到宣传部,鲁文山刚泡好茶,茶香正四溢着;烟也刚燃上,袅袅娜娜的,飘飘忽忽的。鲁文山尖着嘴吐出一个烟圈,烟圈圆圆地像个小车轮,滚滚地向玻璃窗上撞去,撞得烟雾缭绕;然后又探着头尖着嘴去喝茶,茶很热,他不得不蜻蜓点水似的又缩回了头,这个时候,莫士戈热情洋溢地跨了进来,热情洋溢地打上招呼,热情洋溢地递上香烟。
二人坐定后,莫士戈自然要把自己的疑问再次抛出来,鲁神仙就“绕”,最后看“绕”不过去了,就说了些实话:“第二名的辅导老师和家长不知哪里得来的消息,说你儿子是替别的学校,对,是替那个民办中学‘育英中学演讲。”莫士戈就插话:“我儿子的学籍在育英中学,不存在替不替这一说。”鲁神仙只管说自己的:“那老师又说育英中学没有订《红色之旅》读本,没有订《红色之旅》,按照规定就没有资格参赛。”莫士戈心想:“知道了,‘鬼出在这个地方。”又思:“这算什么狗屁理由,你当初怎么就同意我来为儿子报名了,现在又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肯定是你鲁文仙收了人家的礼,嘴短了。”但变成声音时却是这样的:“可我儿子那个班订了《红色之旅》,若不信,可以调查的;再说,他们怎么会知道育英中学没有定《红色之旅》这本书?”这后一个“?”就有点重了,弦外之音:有可能就是你鲁文山泄了密。
其实,这还真让莫士戈猜个正着。这鲁文山与第二名有点拐弯亲戚,实情透给了人家,人家看到了希望,就立马给鲁文山送了两条烟。
鲁文山焉能听不出莫士戈的弦外之音,心中翻波涛,脸上无风云,说:“你儿子那个班订没订《红色之旅》我不知道,可人家辅导老师打听得知了那个育英中学没有订,人家因此自然就要争取。”
莫士戈一听这口气,就知道这“神仙”是铁了心向第二名说话了,再加上多日来的不顺,心中的火气就“突突”地朝外冒,他强按压住自己,但是言语里还是多少夹杂着火星子:“我儿子那个班订了《红色之旅》这是事实,他的学籍在育英中学,他也只能以育英中学的学生身份参赛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至于育英中学其他班没有订那本书,这与孩子有什么关系?这既不是孩子的错,也不是我们家长的错,这个错凭什么由幼小的孩子来承担?再退一步说,哪里有这种规定:讲学生不订《红色之旅》,就剥夺学生参加‘读书活动的权利?如果国家教委或国家宣传部作出了这样的规定,我们就认了,但是我想是绝不会作出这种不明智的规定的,要不然,我们还可以上网,在网上讨论讨论这件事,看看广大人民群众的说法是什么样的。”莫士戈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虽是有些激动,但心里畅快了些,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鲁文山竟笑了,他这“笑”把莫士戈弄得心里很不受用。鲁文山说:“莫主任,你可别跟我急,那边学生的家长和老师有这种反应,我们就得慢慢处理。当然,我理解你的心情,谁都想为自己的孩子寻找一个更好的锻炼机会,但我们得按规则办,每一个游戏,都有它的游戏规则,是不是莫主任?你也是个聪明人,我不用多说你也都明白。”
莫士戈一边听,一边就气不打一处来,心想:“你还跟我捉迷藏,你还要慢慢来,你把我糊弄过了这个星期天你就不慢慢来了。”又想,你还跟我谈游戏规则,这游戏规则就是你小子给破坏了的,你他妈的真不是好东西。但嘴里却说,,“鲁科长,你眼里也揉不进沙子,我儿子参赛是符合规则要求的,还请你多多关照。”
鲁文山想:“你他妈的莫士戈算是什么东西,你还给我施加压力,你以为你是谁?你说符合规则就符合规则啦?你还要什么上网讨论,那你就讨论吧,你讨论又能咬我的蛋?嘴里说,“莫主任,你放心,我们会公正地处理这件事的,不都是为了孩子吗?最起码,我们在孩子面前是要公正的,不能让我们的未来受了委屈。”
“冠冕堂皇!”鲁文山还没说完,这四个字就一下子跳进了莫士戈的脑海里。莫士戈还要说点什么,这时来了人,鲁文山忙与那人打招呼,莫士戈也就告辞而去。
来到自己的办公室,莫士戈就给陶陶打了汇报电话,陶陶一听,说:“问题大了。”又说:“你就是好激动,你肯定把这些天的气也带给鲁科长了。”莫士戈说:“我自认为没有,我都是压着性子说的。”陶陶说:“我现在不与你抬杠,问题是这事怎么办?”
莫士戈说:“怎么办?不惜一切也得办!”
陶陶说:“看看,又激动了吧。”
莫士戈说:“不是激动,这事办不好,儿子的心灵肯定要受到很大的打击,而且我们这为人父母的脸面也没有地方放。”
陶陶听了,不由就想起了莫士戈的“破事”,寻思你莫士戈还知道要脸面?但又一想算了吧,现在儿子的事迫在眉睫,哪急抓哪吧。
八
计划跟不上变化。陶陶急了,来到莫士戈的办公室,莫士戈也急了,因为已经星期四了,也就是大后天市里的演讲比赛就开始了,而儿子的事还在空中悬着……“悬而未决,心如猫拽。”两人被“猫”拽得心里异常躁乱。
陶陶往后甩了一下自己的长发,说:“我给部长打电话。”说着就向老公要了部长的手机号码,开始拨号,然而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
莫士戈像猫等鱼似的等结果,问:“部长怎么说?”
陶陶的情绪并没有高起来,说:“部长说这事他知道了,会按照规则和程序办的。”
莫士戈:“没有了?”
陶陶:“没有了。”
两人一筹莫展。
正在这时,莫士戈的手机响了,是鲁文山打来的。鲁文山的声音有点尖,说:“要确保你儿子去市里参赛的话,你最好跟育英中学校长说一下,让他学校订《红色之旅》。”莫士戈这次没有控制住自己,火一下子就从心里蹿了出来,他打断鲁文山的话说:“我本事真大!我根本就不知道育英中学校长姓啥名谁,是高是矮,是男是女。再说,我也没有这个义务!”
鲁文山不愧为“神仙”,并不恼,说:“你别激动莫主任,还有一个办法,你向市委宣传部要求,多争取一个名额。”
莫士戈心想你鲁文山真不是人,是人都讲不出这样混账的话来。然而,莫士戈此时却平静下来,声音柔中有刚地说:“市委宣传部我也不认识人,再说要名额也该是你宣传部去要,或者第二名去要,不该我第一名去要。”鲁文山修炼得很好,一丝不苟地说:“你还是去争取吧,否则的话,即使把你儿子的名字报上去,恐怕也是要作废掉的。”莫士戈被他这话说的一时吃不太准,想了想说:“鲁科长,要不你就与市里说,说区里比赛,这两个孩子并列第一名,所以才一齐报上去的,请市里通融一下。”鲁文山说:“不行,只能去一个,两个都报上去,两个都作废,规则就是这样定的,而且我们也已经向市委宣传部这样反应了,没用。”莫士戈本以为自己刚才的建议是一个不错的灵感闪现,不曾想即刻被鲁神仙枪毙了。现在怎么办呢?还是不能与鲁文山搞僵,就迂回着说:“鲁科长,本来我们俩的关系还可以,都在一个楼上班,我还是很佩服你的,还请你多关照,刚才我言语上有冒犯的地方,还请谅解,我以后设宴请你。”说完,莫士戈就觉得自己的话特别肉麻、别扭。
鲁文山说:“设宴倒不必要,最后谁去市里比赛还是让领导拍板吧。”
夫妻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言以对。陶陶埋怨道:“你不是天天吹牛朋友遍天下吗,这会该出来了吧。”
莫士戈愁着脸,极不情愿似地说:“有是倒有一个,只是不合适。”
陶陶急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凡能用得着都用上。”
莫士戈说:“我说出来了只怕你生气。”
陶陶说:“我生什么气,高兴还来不及呢。”
莫士戈说:“那我就说了——丁凝雪。”
“什么?!”陶陶一下子从沙发上站起来,眼光针一般地扎着莫士戈,气恼地说,“莫莫不参加比赛我也不找她!”
莫士戈说:“看看,看看,你讲你不生气,你这不是生气是干什么?”
陶陶说:“你是想气死我!”
莫士戈说:“我绝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想把事情办好。毛主席在战争时期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呢,再说,我和她之间真没有什么事情。”
陶陶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无奈何地坐下来,说:“她不是在龙东区人大吗,找她有什么用?”
莫士戈说:“据我所知,她的妹夫在市委宣传部工作,而且就是宣传科的科长。”
陶陶叹了一口气,说:“我算是倒霉。”
下午,一到上班时间,莫士戈估约着丁凝雪也该到了单位,就把电话打进去,丁凝雪吃惊地接了话,说这事我会给你办好的,末了问莫士戈这边情况怎样,莫士戈说看来要平复下去需要一段时间。丁凝雪说你千万千万不要让她给我老公打电话,那样我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事,现在我整天地提心吊胆,深怕老公有什么异常反应。莫士戈说我会尽量尽量地说服陶陶的,决不让她再做什么傻事。二人没有多说,很快挂了电话。
不一会儿,陶陶报来喜讯:“鲁科长说领导研究决定上报第一名参赛,而且正在发传真上报呢。”莫士戈说好呀好呀,那边(他尽量不使用丁凝雪的名字)也答应帮忙了。陶陶说你现在在哪里?莫士戈说在办公室,之后问陶陶来不来。陶陶说不去了,也得上班。
然而,到下午5点钟,丁凝雪打来电话说市委宣传部还没有见到莫莫的名单。莫士戈说怎么可能呢?大概3点钟的时间陶陶说我们这宣传部正在发传真,该早到了。丁凝雪说没有,说她妹夫翻了几遍,其他各县市区的名单都报了上来,就是不见莫莫的名字。莫士戈说是我们龙河区的4个参赛选手都没有报,还是单单少了莫莫的名字。丁凝雪说这我还没有弄清楚,不过目前是没有你儿子的名字。莫士戈的心一下子又悬了起来,说你让你妹夫再仔细查查看到底是咋回事。
莫士戈又把电话打给陶陶,问:“你亲眼看到他们发传真了吗?”然后把丁凝雪话的意思说了一遍。
陶陶在家里正准备晚饭,接了电话说:“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他们发传真,可他鲁科长也不敢这样随便说的吧。”
莫士戈思索着说:“但愿不要再节外生枝。”
丁凝雪又打来电话,说你们龙河区还没有报。
九
早早地上了班,莫士戈首先来到宣传部,宣传部的门还在锁着,他又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喝了一会儿茶,吸了一会儿烟,想了一会儿自己犯的错误,就又来到了宣传部。这次,他看到了鲁神仙,鲁神仙正在向茶杯里冲开水。莫士戈就要开口说话,鲁神仙已经用眼睛的余光扫过了莫士戈,说:“你后天带儿子到市里参加比赛吧。”看了一眼莫士戈就再也不看了。
莫士戈被高兴顶得也顾不得别人的不礼貌了,疲疲的身体也一下来了精神,连说了几个“谢谢”就往外走,正好碰上部长,部长说你要让孩子再精心准备准备。莫士戈激动得又连说几个“一定的”,一边不由就生出了十分的敬意,寻思:“看来,部长还是坚持原则的。”
莫士戈带着喜色来到自己的办公室时,丁凝雪的电话也跟着进来了,说“你们区的名单才刚刚报过去,有你儿子的。”
莫士戈说:“谢谢,谢谢。”
丁凝雪说:“谢什么呀谢。”又说:“听我妹夫说,好像你那个宣传科长在使坏,拐弯抹角地告诉他,说某某一个学生,其实也就是你儿子莫莫,是在替别的学校参赛。”又说:“你再做做你那个宣传部的工作,怕有人抵得紧,有时临登台比赛前还有被取消参赛资格的;我妹夫这边你放心,该做的他会好好做的。”
莫士戈愤愤地说:“我怕谁抵得紧?我本来就是真的我怕谁?要不是他鲁神仙在里面捣鬼,事情何至于这么复杂?我又何至于这么费心?再说,部领导还是立正竿子的,何怕之有?!”又补充道:“你让你妹夫不要信了小人的谗言,只要他立场坚定,这船就翻不了。”
丁凝雪说:“你还是谨慎点好,小心无大错。”
莫士戈也缓了口气说:“是的。”又说:“凝雪,谢谢你的帮助和关心。”
丁凝雪没有顺他的话,而是叫了一声:“士戈……”
莫士戈心里就酸酸的,说:“凝雪,你还好吧。”
丁凝雪忧伤地说:“还好,就是心里有点疼,而且这心总还是放不下去。”
莫士戈劝道:“再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些。”
丁凝雪说:“你呢?你们这两天又生气了吗?”
莫士戈说:“这两天还好,只怕儿子演讲一结束,她又会把兵力调过来。”
丁凝雪幽幽地说:“你以后就好好地待她吧,想想我们也不年轻了,而日子还有好长一段要过。”
莫士戈说:“你多多保重。”
丁凝雪说:“你也保重……”说着,忍不住地想流泪。
时间过得真慢呀!
1号,2号,3号……
11号登台了。
莫士戈悬着的心逐渐回落,马上儿子就可以登台比赛了,待儿子演讲一结束管他洪水滔天,你鲁神仙即使把天捣个洞我也不在乎了,再说鲁神仙又岂能把天捣个洞?借你一个头你也不会生出这么大的本事来!
11号演讲结束了。
莫士戈用力地给11号鼓着掌,不是11号演讲得好,而是11号演讲结束了。
主持人走到台中央,然而主持人却没有宣布“莫莫”上台演讲,而是请了一个领导走上台来,莫士戈的心一下子又提了起来,提速之快,匪夷所思。
莫士戈集中精力,全神贯注,他要一字不落地听听领导讲什么,他已经有了下一步打算:如果现在取消儿子的比赛资格,那他一定一定要据理力争,讲明事实真相,这样还不行的话,那他就请求领导一定同意儿子上台演讲一次,让评委给打打分,看看儿子这次演讲到底怎么样,检阅检阅也算是没有白来一趟就足够了,可以妥协答应不让儿子参与竞争去省里比赛的名额。
领导没有走到台中央,而是站在了台边就说:“说一个事。”
莫士戈的心已经从肚子里掏了出来,放在了手里拎着。
领导说:“我们这个比赛是全程录相的,有拍照的同志,有上洗手间的同志,还有一部分不知要干什么的同志,总是很随意地走来走去,这样会影响录相效果的,请大家配合一下,不要乱走动,不要大声说话,谢谢,深表感谢!”然后他走了下来,比赛继续进行。
莫士戈像牛一样很响亮地呼出了一口长气,心这才又放回到了肚子里。
儿子登台了,莫士戈微笑而慈祥地看着儿子,幸福得像久病的人突然一下彻底痊愈一般。
儿子的分数非常高,目前高居第一。
莫士戈和陶陶拚命地鼓掌。
儿子这个第一的好位置一直保持到整个比赛结束。
下个星期天,儿子就可以作为市里的学生代表,参加省里《红色之旅》读书活动的演讲比赛了。
陶陶竟当场抱着儿子哭了,儿子被哭得莫名其妙,迷惑地看着爸爸,眼睛里也不禁泪潸潸了。莫士戈抚摸着儿子的头,说:“你妈妈是高兴得哭了,这就叫热泪盈眶。”
儿子这才像白云一样轻快地笑了。
莫士戈又拥了拥陶陶,而自己心里却想:“我莫士戈才真应该大哭一场呢。”
十
陶陶终于还是把电话打给了丁凝雪的老公。
陶陶早已像侦探一样,把丁凝雪老公的情况弄清个大慨。丁凝雪的老公早多少年就下了海,在外边做生意,经常是10天半月不在家,钱也没见赚多少,花姑娘倒是玩了不少。可男人就这个德性,允许自己在外面拈花惹草吃喝嫖赌,却不能容许自己的老婆有出轨行为。
老公不忠,让陶陶的大脑始终都没有停歇过。可既已如此,又能怎么样呢?离婚吧,这哪是一件容易的事,离婚了自己以后就会幸福吗?对儿子的打击又是多么地沉重,对双方的老人又是多么地痛心,老的老小的小,实在是让陶陶割舍不下;再者,莫士戈总的来说还算是不错的男人,所以离婚这条路陶陶现在还是不愿意走。不离吧,不离就得彻底斩断他们的情丝,让他们觉着刻骨铭心的疼,而让丁凝雪觉着刻骨铭心疼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这事告诉她的老公。可,对她的老公说哪些东西,说多少,陶陶又着实地思考了一番。说多了,说重了,他万一找人把莫士戈打个残废什么的,自己的后半生就更不好过了;说轻了,又怕丁凝雪老公不当一回事,二人以后还有可能死灰复燃。
陶陶掂来倒去地想,把头都想疼了,就在她想好说什么时,也巧,莫士戈当晚不在家吃饭。陶陶很有心计地来到另一个区的公用电话亭,毫不犹豫地拨了丁凝雪老公的电话。陶陶拨的时候,心里很紧张,心跳得很厉害,可偏偏第一次拨打:占线。等了一会儿,陶陶又拨,结果还是占线。陶陶此时紧张得竟有点犹豫了,但深吸一口气后,她对自己说:“不!”她鼓起勇气第三次拨打,通了。对方“喂喂喂”三声后,她才抚着心跳接了电话,轻轻地说:“请问,你是丁凝雪的老公吗?”对方说:“是,是的,有什么事吗?”这时她立刻就改了口气,恨恨地说:“管好你自己的女人!别让她去破坏别人的家庭!”然后她停了下来,等待对方的反应。对方显然激动了,说:“你是谁?你是谁?”陶陶这时把电话挂了。
对方自然是丈二和尚,陶陶要的也就是这个效果,就在第二天的下午,莫士戈正在办公室与人侃天侃地时,丁凝雪的电话打过来了。丁凝雪心里既苦又气,说:“你老婆,她到底想干什么?到现在还盯住不放!”莫士戈一听这话,知道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的头就开始大起来,头发也不禁竖起来了。但他此时还是先把自己的苦与痛压下来,好言好语地劝着丁凝雪,要丁凝雪消消气,越是这样越是要注意身体,要顶得住,千万什么都不要承认,什么都不能交待。丁凝雪说我承认什么,他有什么资格管我!他早就背叛我了,不知背叛了多少次,我才不怕他,他要打我就和他打,他要打狠了,我就叫我的两个哥哥跟他打,大不了与他离婚!莫士戈说你到移动公司把手机密码改了。丁凝雪说他不知道我的手机密码。莫士戈缓了口气愧疚地说:“都怪我,是我对不起你,让你受苦了。”丁凝雪听了鼻子不禁一酸,刚才很女英雄的话没有了,泪水就顺着声音传了过来,传得莫士戈也鼻子酸酸的,泪也在眼眶里行走。但他没有让泪水走出来,而是仰了仰头让泪水又走了进去,说:“凝雪,别哭了,我回去再好好地劝劝陶陶。”为了让丁凝雪能舒服些,莫士戈又说:“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她,她这样也太过分了!”丁凝雪止住哭声,说:“算了,你们还是好好地谈谈,她是无辜的,我们都是女人,我理解她心中的苦,再说我估计她以后也不会再打什么电话了。”
莫士戈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叹了口气说:“凝雪,是我不好,你以后要多多善待自己。”
丁凝雪说:“我以后很可能会与他离婚。”
莫士戈,张了张嘴,可什么也没说出来。丁凝雪说:“代我向陶陶说声‘对不起,是我伤害了……”说着,嗓子又禁不住的沙沙起来,就挂了电话。
莫士戈听着手机里的盲音,不禁闭上双眼。
第二天早晨醒来,莫士戈感觉头木腾腾的,身子软软的,他的慢性肠炎又严重了,他又早早地坐进了卫生间,习惯性地摸出手机准备玩游戏,可当他打开手机时,竟一点兴趣也没有了。
他坐在那里很疲惫,肚子还一阵一阵的疼,像有一只手在里面揪来揪去;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杂草丛生似的,昨天的事竟一时也懒得去理了。他燃上一支烟,吸了一口,苦苦的。这时,不知怎么了,烟雾里竟依稀冒出鲁神仙那很柔和的脸面来,他这才忽然记起,再过两天,不,是三天,他又要和陶陶一齐带着儿子到省里去演讲比赛了。
作者简介冷鬼,原名冷治武,1970年生,大学学历。1992年开始文学创作。在《清明》、《安徽文学》、《文学报》、《百花园》、《检察日报》、《辽河》、《微型小说选刊》等报刊发表作品100余万字。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阜阳市作协副主席,阜南县作协主席,阜南县文联主席,阜南县政协常委。
责任编辑 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