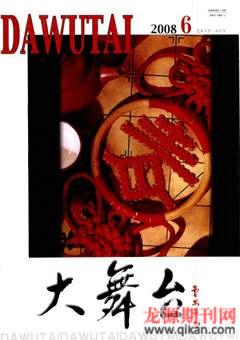民族地区民间工艺中的亲情之美
吴 昶
【摘要】恩施家椅的设计构思奇特,不仅体现了民间设计制造者的匠心独运,更显现出中华民族育儿习俗中“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目前,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家椅制作技艺已处于濒危的困境,对其技艺传承环节的保护,意义十分重要。
【关键词】恩施家椅 亲情之美 技艺传承
马凌诺斯基曾在他的《文化论》中说:若我们随意取一件器物,而加以想象分析,就是说想设法去规定它的文化的同一性,我们只有把它放在社会制度的文化布局中去说明它所处的地位。[1]在中国南方许多盛产竹类的地区,竹器成为人们传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竹器的设计与制作是一门古老而又传统的民间技艺。恩施自治州是一个土家族苗族少数民族聚居地,那里盛产各种竹器,其中有一种叫家椅的小背篓,既有实用价值,又饱含着人类的亲情之审美价值。
一、家椅释名
恩施家椅,又称“凉椅背篓”,是背篓的一种变体,专用于背负尚处在哺乳期的婴幼儿,其主要特征为:主体骨架材料多为整段竹管制成(也有少数家椅是木质榫卯结构的),主体部分的竹质骨架不剖不编,只以切口榫接,多为直腹、平口带弧弯型背靠。主体以背篓特有的双肩系子(背带)相连,以便能固定在成人背部。
家椅的“家”从字面意思讲,也可写作“枷”,因其为竹木材料制成框架格档,起着限制婴孩活动范围的作用,然而从其限制功能的本来目的而言,它却完全不同于古代用以惩罚囚徒的“枷”,而是表达着双亲对于婴幼儿的一种呵护,是家庭温暖的一种缩影。尚无正常行为能力的婴幼儿,往往喜欢到处爬,又缺乏安全意识。成人所认为平常的火塘、水池、地窖、沟坎等地方,对于婴幼儿而言却是十分危险的;婴幼儿也有可能因碰触、误食不洁净的东西而生病,这些潜在的危险对于劳作繁忙时的成人而言是必须要考虑的。家椅是父母用来在山地环境中背负小孩行走,或因临时忙于劳作来不及照顾时为小孩提供的一种坐具。因此,这种具有约束功能的育儿用具从本质上而言既满足了山区家庭育儿活动的需要,也体现出了山区手工艺文化中的亲情之美。
目前,恩施及周边地区的家椅大致可分四脚单座家椅、五脚单座家椅和四脚双座家椅三种样式,主体部分多为水竹材质。单座家椅较为常见,只能承载一个婴孩;双座家椅比较少见,主要用是为喜得孪生宝宝的家庭订制的。
二、亲情之美在设计构思中的体现
格尔茨曾引用S·兰格的话说:“凭借我们(人类)的思维和想象,我们不仅有了感情而且有了感情生活”。[2]他还特地补充道:“一个孩子……在用‘心感受爱抚之前用皮肤感受爱抚。不仅思想,还有情感也是文化的造物”,[3]传统的民间手工艺设计并非只有实用功能,而无情感表达,或者二者互不兼容,实际上从设计构思的角度而言,这两方面的因素是密不可分的,家椅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首先,恩施家椅的形制本身就是一种爱的符号,它表达的是一种精致的温情。
一方面,家椅是为婴幼儿量身定做,因而形态小巧玲珑。由于普通竹材过于粗大,只能剖成篾片才可制作,然而篾片的断口比较锋利,容易划伤小孩子的娇嫩皮肤,而水竹的成体细小,用它的整段竹管制作的家椅则能有效避免这一问题;另一方面,水竹表面光滑,质料细密、结实,制成榫卯结构,有利于小孩在炎热的夏天能够透气、凉爽,更舒适。
其次,家椅在社会文化功能上充满了关于爱的艺术意义,这种艺术意义主要体现于三个群体:手工艺文化的创造者——篾匠(成年男性)、文化的应用者——婴幼儿的父母亲以及爱的受益者——婴幼儿,而家椅正是这三个群体之间情感交流的具体物质呈现形式。与我们所理解的艺术品有所区别的是,家椅之美无涉于主流社会和公共空间的展示,而只存在于各个山区家庭的微观单元之内和具体生活的应用情境之中,是生活内容之一。家椅不是一种仅供观看、欣赏之物,它的天然材质所造就的舒适感和耐用的品质只有婴幼儿才能体会得到,但是小孩子毕竟还在呀呀学语,无法言说这种坐具(对于婴幼儿而言是坐具)的好处,但父母们却能够从与孩子的沟通交流中体会到他们的愉悦。
来自男性(篾匠、父亲,有时两者合二为一)与来自母亲的爱在家椅上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前者体现在设计制作和购买行为方面;后者体现在使用文化方面。
家椅的设计制作者——篾匠是一群匠心独运的人。虽然在很多时候,技术常常被误解为谋生手段的代名词,但在这些制造家椅的工匠们身上却彰显出他们在技术之中凝结的智慧与爱的表达:
篾匠基本上都是成年男性,然而他们却能设身处地从婴幼儿被呵护的需要出发,进行换位思考,他们按照孩子的身体发育特征进行人体工程学意义上的设计构思,制作出各式各样的家椅——譬如在材质选用方面,要满足婴幼儿凉快舒适,不生疮痱的生理需求。

在制做工艺上确保其安全,既要非常结实,不易崩坏,又要非常光滑,不伤婴幼儿的娇嫩皮肤,因而采用嵌合榫接的方式,这种设计虽然麻烦,但却比常用的背篓剖篾编织工艺要好。
此外在细节处理上,如背靠部分用炙烤而不用拼接的工艺,可以增加舒适感,又在婴幼儿手可触及的前方添加了玩具杠这样的益智、娱乐设施。这样一件作品的创意构思中,无疑使父母对儿女的亲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恩施黄泥塘乡的篾匠毛贤才说:“家椅的做法跟其它背篓很不一样,主要是用榫接、“迂”(竹器制艺之一种,即在火上边炙烤边用力弯曲,使之定型后不再抻直,当地人称之为“迂”)、穿线(在竹管上钻小孔,并以麻线缚之)等方法,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才漂亮,小娃娃坐进去才舒服。”
家椅的这些细节之处既体现出技术功能背后亲情之美的创造动力,又体现出篾匠们在处处体现实用之美的艺术情趣。即使家椅的受益者婴幼儿并非篾匠自己的孩子,篾匠仍然以非常细腻的心境去制造一个个家椅。在以机器取代手工和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现代制造业兴起以来,我们往往习惯把“美”和“用”作为两个彼此相区别的概念指标,来审视和评价我们生活中的各种人造器物,但在为数不多的、尚在延续的乡土传统中,“美”与“用”却经常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家椅的舒适感本身就是一种美,又是一种用,它独特的整体质感既体现出篾匠对竹子材料性质的深刻了解,又体现出他们对人,尤其是婴幼儿的温馨爱意。
虽然,恩施家椅常常以商品的形式传播到周边,但它们的制作者们长期以来所得到的只是些许微薄的回报,但他们存在于传统价值观尚未完全消逝的土家族、苗族、侗族村落之中,把自己的身心融于生活的乐趣,因此所做的活计并非不单是为了养家糊口,而且也是通过造物之美验证着人的智慧。柳宗悦曾指出:“美的境界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把美普及到所有的大众生活中。不要把美限制在特殊的场合或特别的器物之上,而应该使美回归到最平凡的器物之中。”[4]家椅的设计、制造者独到的匠心体现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中华民族古老美德。
三、制作技艺的传承与保护
虽然恩施家椅一直受到当地城乡用户们的广泛欢迎,但其传承保护问题实际上并不容乐观,根据笔者调查,家椅制作工艺主要分布在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其周边地区水竹资源较为丰富的广大农村地区,如恩施、宣恩、咸丰等市县。以恩施市为例,近些年来,健在的、能够制作家椅的篾匠人群每个乡几乎不到3人,主要集中在恩施市的芭蕉乡、盛家坝乡一带,他们大多以务农为主,兼做篾匠营生,这项古老技艺的传承方式本身既缺乏稳定性,又面临着现代化生活方式带来的强大冲击力。目前就其传承活动的保护工作而言,既有不利之处,也有有利之处。
从不利的方面而言,由于家椅造匠只是篾匠群体之中的凤毛麟角,而且他们的技艺传承方式往往既非家传,亦非师传,而多采取的是一种以“自学”和“瞄眼学”为特征的不稳定型非正式传承方式。[5]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日渐明显,新生儿的比例在逐年下降,因此家椅的销售市场也正在逐年萎缩;加之如今的年轻人愿意从事这项工作并能胜任者非常少(根据笔者在恩施市芭蕉、盛家坝两乡的调查统计情况表明,在目前十万多村镇居民中,能够制作家椅者不到10人),因而其所面临的困境用“濒危”二字来形容是毫不夸张的。

但从有利方面而言,作为商品而受到地方人群的普遍欢迎,且由于家椅本身为榫卯结构,制作工具简单易学,熟稔篾艺和藤编的农村手工艺人只要能够获得足够的实物模型和相关数据,大多都比较易掌握,因此当前此项民间手工艺的传承并未陷入绝境。
根据以上情况,笔者认为:恩施家椅的相关保护工作应当采取多种方式进行,一方面借助旅游业开发的机遇,扩大其影响力,帮助他们提升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潜力;另一方面,依靠各县、乡文化部门,为手工艺传承人提供必要的经济支助,对愿意从事该项手工技艺学习的年轻人予以奖励,并形成对应的县、乡级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在当前,只有充分调动这两方面的积极因素,家椅手工技艺和家椅文化才可能良好地延存下去。
注释:
[1](英国)马凌诺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第2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
[2](美国)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阐释》[M],韩莉译,第100页,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11.
[3] (美国)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阐释》[M],韩莉译,第10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11.
[4](日本)柳宗悦《工艺文化》[M],徐艺乙译,第18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
[5]吴昶“试析湘、鄂、黔民族民间手工艺传承方式的基本类型”,《中国艺术人类学论坛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132页,北京,2008.11.1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2008年度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当代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土家族工艺美术研究”(编号2008y249);湖北民族学院2007年度科学研究项目“湖北民间竹艺-恩施家椅的文化内涵”( 项目编号:MYQ2007028)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