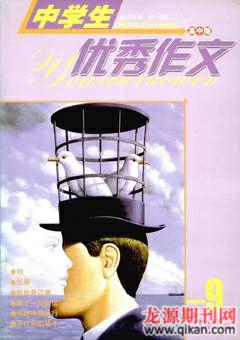“烘云托月”技法例说
邱德保 蒋 兰
“烘云托月”,意即作者想画的是月亮,却不直接去描绘月亮,而是通过云彩来烘托月亮。它源于绘画技法。作为写作技巧,是喻指行文从侧面加以渲染以衬托所记叙的主要的人和物,使记叙的主体更加突出。常用的烘云托月的表现手法有以下几种:
用日常摆设物件烘托人物。《红楼梦》中的秦可卿,对揭露贾府中大小主子荒淫腐朽的面目,有着重要作用。作者对秦可卿本人的风流习性和非礼行径,虽未作正面描述,却以她卧房中的摆设作侧面烘托。秦可卿房中陈设的件件“古董”,都与史传中某个香艳的故事相牵连。这是一个用夸张笔调所构成的典型环境,烘托出秦可卿的风流性格,让读者从中看到她的生活剪影。
用景物烘托人物独特心境或崇高形象。如鲁迅的《药》:“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的静……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这是一幅由枯草昏鸦构成的冷色调图景,十分有力地烘托出作者当时抑郁沉痛的心情。景物还可烘托人物崇高形象。如王愿坚的《七根火柴》,开篇描摹茫茫草地气候多变、暴雨时作、遍地潮湿、酷寒难耐的特点,突出了火的重要、火柴的珍贵,而在“要是有一堆火,有一杯热水,也许能活下去”的境遇下,无名战士却舍不得用一根火柴,将生命置之度外,把七根火柴托付战友带给部队。这里对自然环境描写,从侧面烘托了人物忠于革命事业的精神境界。
用次要人物烘托主要人物。如《左忠毅公逸事》中有一处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主要人物左光斗,一个是陪衬人物史可法。文中许多笔墨落笔于史可法,而衬托了左光斗。描写史可法忠于职守,“每有警,则数月不就寝,使将士更休,而自坐帷幕外”。“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铿然有声”。这着重表现了史可法身先士卒、吃苦耐劳的精神,更表现了史可法的老师左光斗的影响之大。越是描写史可法,越是衬托左光斗的形象。两相辉映,收到水涨船高的艺术效果。
用虚幻情景映衬社会现实。如法国小说家亨·特罗亚的《最好的顾客》,作者笔下的主人公巴罗丹,没有亲人,孤苦伶仃,为避免死后柩车穿街而过无花圈无鲜花的凄凉的结局,他给自己造出所有的亲人来,买许多花圈表示为失去他这样的父亲、祖父、兄弟、儿子、伯伯、表兄、女婿、丈夫等等而感到痛苦,他在假造的同情中求得虚幻的亲友之爱,以此聊以自慰。由此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老年人晚景凄凉的社会现实。巴罗丹老人的幻想之极也正是他的凄凉之极。这种手法的运用使文章的感染力和批判力大为增加。
用人物外部情景烘托内心感情。如朱自清的《背影》,作者集中笔墨写父亲的背影,细致地描写了父亲背影的外部特征,其目的是为了表达作为儿子的真实感情。父亲为了替儿子买桔子要爬到月台上去,父亲是个胖子,穿戴臃肿,而月台较高这就给他添了许多困难。父亲背影的动人之处,就在于他克服困难所作的这种努力。先是“蹒跚地”过铁道,爬月台时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向上“缩”,肥胖的身子“倾”,这些具有感染力的外部形象的突出刻画,烘托了作者内心对父亲的深深的感激与挚爱之情。
用梦境映衬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写道:“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脚著谢公履,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诗中传达出使人摆脱束缚追求自由的那种急迫感以及暂时摆脱重荷的轻快感。这些梦境都是李白不甘于文学弄臣的地位,终遭谗毁被放逐京城的感受,从而映衬出李白傲视权贵的思想感情。
用实景物来烘托虚景物。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全文对潭水着墨并不多,但是写石绘鱼,突出了潭水。写小潭“全石以为底”,靠近岸边有奇形怪状的各种石头,石上满是“青树翠蔓”,在微风里“蒙络摇缀,参差披拂”,还有游鱼在“日光下彻”时,“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游记以玲珑的石、青葱的树、轻灵的鱼衬托了一泓清水,生动而真切,形神兼备。若离开这许多衬托景物,单纯地写潭水清澈,就没有韵味了。
总之,用“烘云托月”的技法描写人和物能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使作品呈含蓄委婉之美,能使主体形象更加显豁突出。值得注意的是,运用这种写法主次要分明,若陪衬过分,造成喧宾夺主,结果将适得其反;陪衬不足,不提供一个恰如其分的参照物,主体的思想意义及其艺术价值也就不可能充分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