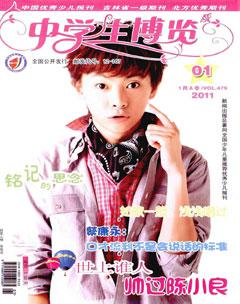失去感动的孩子
唐 汶
我的孩子今年12岁,在一所最好的初中就读。她乖巧懂事,学业优秀,经常在班级考试排前几名,即使全年级1200人中也能进入前20名。也许她早就意识到,可以拿这个来安慰与她相距千里、一年只能看她两三次的父亲。如果偶尔有一次考试失败,会让她十分内疚。畸形而偏颇的教育让她意识到她的存在是靠那些成绩实现的,同时成绩也是她对父母辛苦的直接报答。
孩子十分懂事,似乎知道我们家境一般,所以很少伸手索要玩具、零食之类的东西,在这方面表现出罕见的节制。每次我回到家里,因为停留的时间很短,孩子又有各种各样的课,所以沟通交流的机会很少。而且每次交流都相当简短,所以我只能通过花钱给她买心爱的礼物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愧疚,同时让她感受一个父亲极为可怜而笨拙的爱。可她总是拒绝——她虽没有体会,但却知道我挣钱不容易。每当想起陪孩子在蛋糕店品尝蛋糕或是吃冰激凌的情景,我就既心酸又甜蜜,但那样的次数都寥寥无几。
家人很担心地对我说,这孩子极难被感动。她过于理智,很少像别的孩子那样自然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其实这一点我早就注意到。她沉默内向,小时候就喜欢一个人一整天闷声不响地摆弄积木,见到生人极为羞怯。她似乎过早地拥有成人般乏味的理智,个人生活极有规律,几点起床,几点出门,几点睡觉,时间似乎不差分毫,即使偶尔喜欢的娱乐,只要与作息时间冲突,她都会毫无留恋地舍弃。我一直担心她失去一个女孩子天生的生动敏感的心——尽管她的喜好和习惯正是一般家长所希望的。
长期的优秀让她对自己熟视无睹,即使像电子琴过八级或某科成绩名列全年级第一时,她都没有产生丝毫兴奋。她的音乐老师曾说,上课时极少听见这孩子弹错乐音,当然,她的天分并非出奇地高,大多来自她勤奋的习惯和自尊心,凡是她做的事总是做到难以想象的出色。
一次,她熟练地弹给我听《新疆组曲》,那是一首难度极高的乐曲。我被她难以想象的熟练的指法所震撼,不禁叹息:我的女儿实在太过优秀了!可是,再一看她的神情,我的兴奋顿时消失了:这孩子表情淡然,竟没有被自己所弹奏出的悦耳乐曲打动。
她当时的神情让我想起自己当年自学古典吉他时的情形。每天中午,我都躲在教学楼的一处楼梯里,反复不停地弹奏《卡尔卡西教程》中的练习曲,而此刻其他的学生都在午睡——那是一个多么惬意的时刻,可我却用来对付那些枯燥的练习曲。最为可悲的是,我很少真正融入乐音之中,很难从中得到乐趣。没有感动的学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不觉得自己弹的曲子很动听?”
“有什么好听的?简直难听死了。”孩子说。我无语,心中无限悲哀。
每次我离家而去,就意味着至少长达6个月的分别,可我的孩子依旧平静地在台灯下做自己的功课,看不出有什么留恋。当我走出家门时,她站在客厅里,脸上不肯流露出任何离别的感伤,只是礼貌性淡淡地说:“爸爸……再见。”每当这一刻,我的心头就掠过一丝寂寞和孤独,却什么也说不出。这一切大部分是我一手造成的——来自我对家庭的淡漠。这一刻,我深切地感受到爱的残缺、生活的残缺。
编辑/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