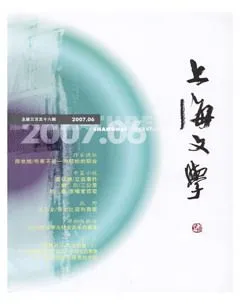作家不是一种轻松的职业
很感谢会议给我这样一个安排,与大家一起来探讨文学发展的问题。
我的认识有限,难免错误,在座的有很多人事实上比我强。我的发言,就是为了让大家来指出我的错误。这也是一种学习、交流的方式吧。
首先讲一下我对作家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理解。这个问题,在这些年,我觉得,无论社会还是我们自身,都多少发生了一些迷惘。大前年我去新疆,在喀什我住的那个宾馆的老总是上海老三届,他看过我早期小说,向我提出疑问,说,世旭呀,我感觉像你这一代作家,历史使命好像已经完成了,现在大家都只关心身体狂欢,身体写作。你觉得你那类写作还有价值吗?他对我很同情,我很感谢他。但我当时有两个感觉,一是时代变迁非常快,大浪淘沙,一部分人应该离开这个地方了,因为有许多新人崛起了,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好事;但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大概也流失了一些不该流失的东西。我坚信,有很多东西,它会具有永恒的价值。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新时期以来的创作。文革结束以后,文艺界开始复苏,戏剧如《于无声处》、《枫叶红了的时候》等等,引起很大的轰动。很短的小说像《伤痕》,也引起全国性的轰动。那个时候,整个中国刚刚从一场浩劫中解放出来,所有的人,对文艺作品充满着渴望,就像久旱盼雨露一样。痛定思痛之后,很快出现了对改革的呼唤。随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引起了全国的激动,就是大家希望能够尽快拯救我们国家面临崩溃的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那时候一个好作品出来,大家就一涌而上,小说是这样的,电影、戏剧也是这样。但是,改革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改革阻力很大,这种阻力除了来自不同的立场、观念和利害,还来自一个非常沉重的东西,就是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它积淀了许多非常不利于改革的东西。于是,很多作家开始寻根,揭示国民劣根性。这是沿着鲁迅的路子走的。随着社会生活,包括文化生活的日益开放,到了80年代中、后期,小说的声音开始变得微弱。小说开始表现出一种危机感,一些很著名的作家开始惊呼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作家不再像今天的明星那样,大家追捧。有些人从小说本身来找原因,出现了所谓文体革命,先锋派小说,就是努力探求艺术表现形式。许多走得很远的作家的作品,大家根本看不懂。字都是简体汉字,也不生僻,但读完以后,不知所云。尽管我们可以认为,任何创新都是有意义的。但随着这种变化越来越走向极端,想仅仅在形式上找到小说出路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
记得当时,一方面是出于对自己的一种恐慌:我还应不应该写下去呢?根本没办法写了,小说也读不懂。另一方面,也产生一种对立情绪。那个夏天,我从单位借了一堆书,都是关于文艺、美学理论方面的,一大堆,坐在家里,地上浇上水,光着膀子,从下午两点,写到晚上十一点多钟。写出了我的第一篇文论:《当代小说在哪里迷失》。这个题目有点狠,有点文革的气味。首先就设定了中国当代小说已经迷失,定了一个前提。文章要探讨的只是在哪里迷失。我写了一大堆,洋洋万言,核心是我认为,作家放弃了它应该承担起来的时代和社会的责任。文学疏远了社会,社会也就疏远了文学。
文章写完以后,我得到一种宣泄的感觉,马上送到省里的一个理论刊物。刊物主编是个非常谨慎的人,觉得一个小刊物对中国文坛指指点点有点不妥。我把稿子拿回来,想了想,干脆寄给了中国社科院的《文学评论》。不久就收到了用稿通知,他们专门开了一个栏目,叫“作家论坛”。现在来看这篇文章,还是有偏颇的,很浮躁。文学发展的走向在它还没有完成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的时候,你妄加议论,是难免片面的。事实上,从90年代开始,文学很快就出现了现实主义的回归。一大批像池莉的《烦恼人生》这样的新写实小说,重新把人们的日常生活,纳入文学表现的领域。一直发展到今天。前面一段对小说形式的探索,则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表现能力。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许多作家写出了很好的作品。他们把自己的眼光和笔触真正深入到民间,深入到了社会底层。使自己的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与广大人群的生存和命运息息相关。怎么会不感人?事实仍在证明,小说离开它的使命感,离开它的责任感,特别是离开它的现实感,是不会有前途的。你把文字弄到天花乱坠的程度,又能如何呢?
甲骨文上就有了“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如果从那个时候算起,我们的文学史多么漫长,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有过多少伟大的作品?出现过多少伟大的作家?今天,我们有什么理由来从事写作?我们的优势在哪里?那就是,所有伟大的前人不知道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他们不知道我们今天的生存状况,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作家最有优势的财富。这种财富,就是我们今天工作的支撑。我们读了《古文观止》,我们还需要写散文吗?方方面面,它都写到了,而且都写到了极致。但它没有写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他们都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写作的生存空间。所以,我们离开社会,离开我们对现实的把握,我们存在的价值是非常可疑的。这就是为什么巴尔扎克会说:“人物——当他充分地反映自己的时代,才有充分的生命力。”
综观文学史,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文学史上有两类人是最显眼的,一类人就是在艺术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把一种艺术形式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推到一个辉煌的高度;一类人就是在高度的艺术性的基础上有着特别深刻的人民性。李白和杜甫,就很典型。李白被称作“诗仙”,出尘,豪迈,放达,超凡脱俗,汪洋恣肆,气象万千,他的诗歌成就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峰。但是,让我感动至深的,是杜甫。杜甫被称作“诗圣”,神圣的“圣”,“圣人”,就是智慧品德最高的那个人。为什么呢?就因为他写诗不止是认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语不惊人死不休”,更因为他关心国家命运,同情民生疾苦,那么苍凉,那么沉郁。他在“安史之乱”中写《三吏》、《三别》,他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他自己最后也很悲惨地死在贫病交加中。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些善良、深沉、充满了伟大爱心的作家。“仙”和“圣”,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人间。“仙”让人神往,“圣”让人崇敬。
今年三月我去云南参加全国作协全委会,会议结束后去了泸沽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青年诗人,叫鲁诺迪基,普米族人,是县财政局长,很细的眼睛,鹰钩鼻子,脸色黝黑,大块头。他跟我说,你们汉族作家写不写都无所谓,反正有一大帮一大帮的书在出。但像我们普米族,只有三万人,如果我们这三万人中没有一个人搞文学,没有一个人的许出名,这个普米族就等于在中华民族文学的大家庭中不存在。我说,鲁若迪基,你了不得,承担这么大一个使命,等于把一个民族文化的责任全部放在一个人的肩上。他是云南财校毕业的,在校时就写了很多诗,那时候,他雄心勃勃,说,山里的路,就像一条鞭子,我要举着这条鞭子,把我们的大山赶向平原。充满了豪气。但是后来,他回到家乡,对社会和生活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就有了沉重。他后来写的诗里面有一首叫《光棍村》,这首诗写得很朴素。诗里写道:乡长打了个报告给县长,说为什么成为光棍村?就是因为没有水,县长听见,很着急,就赶快弄了一笔钱,去给他们把水管架上了,水管架上了,光棍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但是,女人们并没有回来,春节的时候,回来了几个女人,过了春节,又带走了一帮妹子,一帮刚刚长大的女孩子。他写了山里与山外,不同的民族之间,不同的经济区域之间,巨大的差异。他同时也写了山里人的一种强烈的愿望,仅仅解决温饱是不够的,需要更多。你能满足吗?你能做到吗?这是一个非常苦涩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一个诗人在应该发出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发出了这个声音,他指出了这样一种现实,他充分表达了自己这样一种关切与同情,这就是一个诗人应有的品质。
为了宣传这位普米族诗人,我回来写了篇文章到处送,我不是骗稿费,我就是觉得,这样的诗人很值得尊敬。
关心社会生活,关心历史进步,关心民族命运,这是文艺家的天然使命。离开这些,你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家,但很难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等于说我们伟大。但是,有一个非常崇高的目标,那么你的路就会走得更远。这话好像是高尔摹说过的。我们咬牙切齿、殚精竭虑地写作,从最表面看,目标可以说是去拿奖,因为评奖也是一种价值判断。但一个艺术作品,它真正的内在价值是什么?这里应该有一个公认标准。文艺作品的价值,是有客观标准的。它的最高裁判是历史和人民。
媒体上经常提到“三贴近”,我很拥护。我认为“三贴近”的核心是“贴近群众”。离开了贴近群众,其他两个“贴近”都是空的。群众不认可的“现实”和“生活”只能是拙劣的胡编乱造的伪现实,伪生活。这样的“现实”和这样的“生活”远离了它的本质,群众当然不会买账。如果某一个人说好就给奖,说不好就枪毙,那就没有客观标准。没有客观标准,就很难谈论艺术。那就会冒出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滥竽充数的、根本不入流的伪作家、伪学者、伪艺术,弄得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小人得志,庸才横行,真正有才华的作家、艺术家报国无门。
标准就是度量衡。一公斤就是一公斤,一公尺就是一公尺。艺术的度量衡当然要复杂一些,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一千个读者可以读出一千个哈姆雷特,一百个人可以读出一百种《红楼梦》,有这个问题。但是,公认的标准是存在的。我是写小说的,这里举小说名著为例。对古往今来的名著,学者们早就提出过明确的标准:
第一个就是它应该是读者最多的。可能在当时它不一定很走俏,但是,它经久不衰的影响力量和漫长的时间,汇集了最多的读者。当时,它可能不是很出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越来越多的人必须要去读它,历史上有大量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首届是1901年评的,到现在有一百多年了。当时很多人提出,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应该拿这个奖。但是,沙俄政府对这事非常不高兴,他们向瑞典政府施加压力,说,你不能让这个人评奖,让这个人评奖我们不高兴。那时候,瑞典很弱小,俄罗斯是一个大帝国。沙皇说了话,他当然就不敢给了,就给了别人。从此,托尔斯泰再也没有获这个奖。但是,一百年过去,托尔斯泰没有获诺贝尔奖,不是托尔斯泰的耻辱和不幸。它成了大家质疑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的一个最重要的依据。不给托尔斯泰评奖,成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耻辱和不幸。为什么呢?托尔斯泰的作品谁能不读?你可以不读原著,但你会去看电影。俄罗斯拍完了,美国拍,还不满意,法国、意大利又联合拍。名著,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会汇聚最多的读者。
第二个,名著是通俗的,不是专业作家为专业人员写的书,而是为大众写的书,不是多数人读不懂的,弄了半天很稀奇,但不明白在说什么。早期的朦胧诗出来,北岛、舒婷的诗很好读。“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夜”,完全是人生社会格言,谁不懂啊?到后来走得很远啦,读不懂了。有位大诗人形容说,我看这些诗,就是用一只手,蒙着个茶杯,让你猜里面是什么东西,其实里面什么也没有。当然,这样说也许有一点极端。但真正的艺术,是人们容易接收并且一下就能够深入人心的东西。那一年我应邀参加广东一位作者的长篇小说研讨会,这个作品有一点让我特别受启发,就是他用了一个非常传统的章回体叙述方式。这种方式,通过他对生活的非常真切的表现,焕发了生命力。这使我想起两个人的话,就在发言中引用了,一个是英国作家麦克米伦的话,他谈到传统时,这样说,传统并不意味着活着的死亡,而意味着死去了的还活着。另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作家冯梦龙,《三言二拍》的作者,他有两句话,我牢牢记着,觉得可以作为我写作的座右铭。他说:“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你说的话很通俗,就能传得很远,假如我今天在这里故作高深,咬文嚼字,许多人就会索然无味、甚至反感。“语”就是你的表达,“风”就是世道人心,就是人性人情,你关注世道人心,关注人性人情,你才会动人。否则,你写一些与谁也不相干的事情,你自己的那点杯水风波,能感动谁呀?爱情当然可以感动人。要是写得像《牡丹亭》那样的,像《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的,在一种铁幕专制下面,张扬人性,当然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但你老是“身体写作”,老是十个八个情人,一个一个怎么干,绝对的自恋自慰,写多了,谁会老盯着呢?
第三就是它不会因为时代的替换而被遗忘,时代发生变化,它就被遗忘了。伟大的作品,永远不会随着思想原则、舆论的变迁而过时,并且成为推动人类文明最主要的力量。它是不过时的。如果你写得很浅薄,今天搞旧城改造,你就写拆迁怎么有魄力,明天说亮化好,你就写马路应该是光的河流,这根本就不能叫文艺作品。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有篇小说写一个农民成了万元户,吃得很饱,撑出了胃病,送到医院抢救,以此来歌颂改革开放。这哪是文学?艺术的精髓在于,它应当远远高于个人生活的范围,成为人类精神和心灵的代言——这话好像是荣格说的。我们凭着“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走遍全球,都能找到我们中国人的感情。在中国的皇帝当中,有一个乾隆皇帝,很有作为,他特别喜欢写诗,老是写诗歌颂自己的文治武功,写了很多,因为他是皇帝,他的诗集也出得非常漂亮,非常豪华。可今天,有几个人能背得出他的什么诗呢?我去年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拍电视片,到处看到他的诗,但看过就忘了。倒是那个很倒霉的皇帝,南唐李后主,成了阶下囚,亡国奴,他写的“小楼一夜又东风”、“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大家都记住了。亡国之君,他让我们感到历史的一段不堪回首的惨痛。
当然,真正伟大的作品,应当成为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一种力量。我们中国有许多伟大的题材,比如长征。但是,去年中国作协组织重走长征路,作家徐海祥在发言时说,他觉得到目前为止,中国作家写的长征,都很难说达到了理想的高度。这似乎有些遗憾。倒是美国人索尔兹伯里,把长征写得不错。他不是简单去写当时所处的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而是写一支从人民当中产生出来的武装力量,在非常恶劣的政治环境、军事环境和自然环境面前,战胜人类完全不可想像的艰难困苦,走出自己的道路,走出一个光明的前途。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写过《毁灭》,写一支游击队在转移过程当中被毁灭,也是很震动人心的。但是它显然不如长征那么宏伟,充满了史诗感。长征能震撼人类,震撼全世界各国的军队。有哪支军队,经历过这样巨大的艰难困苦,能够生存,能够走到胜利,最终推翻一个政权?这是一支军队的胜利,也是人类生命力的一次胜利。一个作家,具有这样一个高度,他的作品同时也就变得伟大。
第四点就是,名著是言近旨远的。它的语言听起来和我们大家说话一样,但蕴含的意义是非常深刻的。它的每一页都应该比一般的书的整部的内涵都要丰富,都要深刻。它的一页就能当别人的一本书。而且,当你反复去阅读的时候,你总会觉得,你还是没有穷尽它的意义。我读鲁迅的作品就是这样的感觉。《孔乙己》只有二千四百字,却画出了整整一代被封建文化毒害的旧文人的灵魂;《阿Q正传》读一百遍一百遍的感受都不会一样,它解剖的是整个中国人的文化根性,所有人都能时时处处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第五个就是,它应该富有启发性和教育性,无论你完全不同意,或者彻底否认它的观点。作为个人,你完全可以不同意它的想法,觉得它的某种观点不能接受,但它对人类整个文化,整个思想的进步,它作出了重大贡献。最近,北京在演《九三年》。这是法国伟大作家雨果的作品。雨果是我最崇拜的作家之一,他写了很多书,像《海上劳工》、《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都拍过电影的,都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雨果写作的构思是非常宏伟的。他写《巴黎圣母院》,探讨人与宗教的关系;写《悲惨世界》,探讨人与社会的关系;写《海上劳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作家对自己一生的创作构想非常宏伟,非常弘大。我最爱读的,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九三年》。
《九三年》写什么呢?(略)法国大革命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事,但雨果选择这样一件事来描写。那么我想,雨果本人并不想对法国大革命的价值作出划断,他想要表现的是人类生活的价值观,人性的极致时候的光辉。他高高举起人道主义的旗帜。当然,我们可以不同意它的人道观。我们根本不能赞成把敌人放掉,甚至把敌人头子放掉。这绝对是犯罪。这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根本不能接受。我们也绝对不会同意那个放跑了敌人的人,和那个因为以革命的名义杀死了放跑了敌人的人而后自杀的人。我们都不会同意。但是,人类会原谅。当人类有一天没有战争的时候,有一天大家都觉得应该相亲相爱的时候,人类会为所有这一切杀戮感到羞愧。这是人类最终的愿望。人类永远在追求最高最美好哪怕是达不到的东西。我们常讲作家的终极关怀,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种关怀。1980年在北京学习的时候,有一个人说,我们很多理想是达不到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提出来。比如,自由、平等、博爱。社会怎么可能有绝对的自由呢?怎么可能有绝对的平等呢?怎么可能有绝对的博爱呢?但这是世界给人类的命题。他给你一个目标,你向这个目标前进,你永远也达不到,你以为它在十公里以外,到了十公里,它又到二十公里以外去了。它在引领着我们。使人类日益高尚起来,美好起来。作家应该是人类的良心。“一战”的时候,托尔斯泰给德国和俄国的皇帝写信,说,你忏悔吧!当然,说了也没用,但发出了人类良知的声音!它永远在启发人类的理性。没有这样的认知和这样的声音,人类就只能在没有理性的泥坑里打滚。
艺术所追求的精神,应该是人类精神的至高点艺术表现不等同于政治判断。艺术有许多它自身的目标。更多的,我认为是人类终极的价值判断。
第六点,名著应该论及人类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我们人类始终解决不了的问题。很多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那么,我们通过艺术方式去表现它,使整个人类感到,我们是有充分智慧的。我们的智慧是不会被生活所摧毁的。像生与死,爱与恨,这样的问题,人类永远都解决不了。解决小了,就要不停地去探讨它。
了解文学名著的这样一些特点,对我们领悟艺术的本质特点,追求艺术的最高境界,我想应该是柯益的,多少可以使我们不至于对艺术作品作过于浅薄的甚至庸俗的理解。文艺当然是可以用来作宣传的。鲁迅讲过这样一句话,艺术可以有宣传作用,但宣传不一定是艺术。有句话不知道对不对,但我认为它多少有些道理:要使宣传艺术化,而不是使艺术宣传化。把艺术弄得很浅薄直露,弄得像标语口号一样,恐怕不是好办法。
这里我想特别谈到多样性的问题。谈到多样性,我常常喜欢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如果我们不能指望紫罗兰和玫瑰花发出同样的芳香,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人类生活中最丰富的东西——精神产品只有一个形态呢?这里包含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就是,艺术,你的手段越多越好,表现得越丰富越好。不是越来越单一。只管题材吃不吃香,不管艺术过不过硬,走文革时期“题材决定论”的老路,我以为最终是走不通的。
我们常常讲“主旋律”和“多样化”,但常常把这两者分开来,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好像“主旋律”就是讲政治,就是重大主题;“多样化”则是讲艺术,是雕虫小技。这种认识,是有片面性的。事实上主旋律和多样化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就是说,主旋律要有多样化的艺术表现;而多样化则努力地表现主旋律。什么是主旋律,我以为就是前面讲的时代性,人民性,以及由此体现的人类终极关怀。文艺创作归根结底,是文艺家根据一定的价值观、人生观对现实的经验世界加以艺术化的改造,从而创造出有别于此在现实世界的精神乌托邦。这其中当然不乏现实经验世界的人生图景,同时也包含了文艺家文化、艺术的承诺,并寄寓了文艺家对超于现实之上的人类世界的终极关怀。此在的经验世界是文艺作品描述的对象,彼岸的终极关怀是文艺家精神的依托之所。
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作家不是一个轻松的职业。一个作家要实现上述目标之万一,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
古人讲立德、立言、立人。孔夫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鲁迅也说,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水管里出来的都是水。这些话在事实上有点极端。因为许多很好的人,忠厚勤恳的人,他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大艺术家。但是一个好的艺术家,一个完美的艺术家,应该是一个德性很好的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个正派正直的人。尤其是写作,你个人的品质,很容易赋予到你的作品中去,文如其人。一个阴险狡诈的人,文章可能写得很讨巧,文采斐然,但就是没有那种真正能撼动人心的真善美的情感。德性不好,有艺术表现能力,最终还是不能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人生最大的成功是人格的成功,人与人最后的比较,是人格的比较。小人再有成就,别人还是看不起。
作家还是个寂寞的命,得有定力,板凳坐得十年冷。不甘于寂寞,坐不住,自己都会觉得很糟糕。禅宗六祖惠能听两个和尚争论风动,幡动。惠能说,风没有动,幡也没有动,是你的心在动。苏东坡与佛印和尚常常开心斗嘴,有一次,他们两个分别住在长江两边,佛印让人给苏东坡带信,问他在干什么?苏东坡回了一封信,说,我在这里认真读书,谁都动摇不了我,并附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八风吹不动”。佛印看完以后,再带一个口信去,说东坡先生真是了不得,请过江一叙。苏东坡大喜,马上就过去了。刚刚一上岸,佛印就哈哈大笑,说,你不是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一个口信,就劳你过了江呢?
古代许多这样的故事,充分教我们沉静,教我们沉得住气。一个真正献身艺术的人,不要总巴不得天下风光占尽,什么好事都少不了自己,成天从一个会跑到另一个会,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出头露面,恨不得天天上电视上报纸。这有什么意思?我有一个观点,不一定对,现在许多人在说写作被边缘化了,我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对写作是好事。真正有志于写作的人不仅不必抱怨边缘化,还应该主动寻求边缘化,使自己有一个安静独立的内部和外部写作环境。作家应该让自己的作品说话,作家最大的光荣是人家知道你的作品但不一定知道你的名字。反过来,有些人人家只知道他的名字却不知道他都有些什么作品,那才是作家最大的悲哀。我们与其整天为9556385ebf66b92eeec2202a592084ad9201433af7def0f7d9d1fc8c6eea5c23自己争这争那,争那些艺术之外的东西,争那些身外的东西,不如多拿出些像样的东西。一个好作品是需要埋头苦干,潜心打造的,甚至要耗尽作家毕生的心血,甚至需要好几代人不断的积累。《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产生在明清,但它们故事的雏形早就在民间口耳相传了。中国艺术从来都讲究“十年磨一剑”,所以留下了许多经典,成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宝库的财富。我们现在无论作家还是领导都很急,总想一年二年就出一部世界名著,心情和愿望可以理解,但如果离开了创作规律,再好的愿望也只能是欲速不达。
最可笑的是企图经由“炒作”来制造名著。从网上看到,有个大学专门开了“炒作学”,说如今是“注意力经济”时代,或者说是“眼球经济”时代,不炒作,不吸引别人的眼球,就没人知道,就只能被埋没。我始终不相信。文学这一行跟搞企业的不一样,企业一个产品出来,必须拼命做广告。文艺本身就有宣传作用,你写的东西如果没有影响,连自己也宣传不了,那本身就是一种失败!请别误解,我不是说自己已有什么或将有什么值得宣扬的成绩,恰恰相反,我知道自己是狗肉包子端不上席面,避免丢人现眼。看到有些同行劳神费力、挖空心思找人捧场,给自己的名字加上种种吓人的头衔,心里很是同情。金子埋在土里终归是金子,灰尘扬到天上不还是灰尘?“渊生珠而草木润”,这句话好像是荀子说的,真正的好东西价值自现,别人不会看不见的。
拿这个奖拿那个奖,弄个什么荣誉称号,之类,这些要不要想呢?要想呀。荣誉感也是一种人生的动力呀。但是,不必想太多。想得太多,就有可能偏离艺术。忠于艺术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斯坦尼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他告诉他的学生,“爱心中的艺术,而不是艺术中的自己。”你全身心的投入到艺术当中去,你为了你追求的艺术目标,不惜一切献出自己,这是最重要的。王安忆有一部文论著作叫《神圣祭坛》,就是作家要把自己作为牺牲供在文学这个神圣的祭坛上,她正是这样做的,所以她既取得了巨大的创作成就也赢得了文坛莫大的尊敬。忠于艺术,这是必须的一个前提。艺术应该是纯粹的,艺术应该是崇高的,艺术应该是神圣的。掺进了杂念,掺进了邪念,艺术就会大打折扣。前面讲到的一些不成功的作品的例子,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杂念造成的。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一个人的生命和一个人的创造力是有限的。好在文学是一种薪火相传的事业。总会有更强大的后来者不断涌现。网上把我这种人叫做“前浪”,“前浪”就是要赶快让“后浪”压过去。自然有自然的规律,社会有社会的规律,生命有生命的规律。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我曾经很希望自己能为文学做一点像样些的工作,现在看来年轻时的愿望很难实现了,江郎才尽,力不能逮了。因此特别羡慕新人的成就。
让我们一起来为文学的繁荣奋斗吧!
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作者在江西省文联获奖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录音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