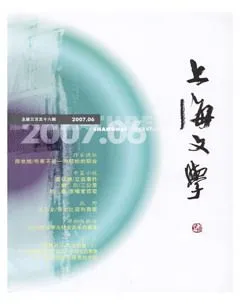在小说弥留之际
时间:2007.2.6
地点:上海青松城大酒店1430号房间
聊天者:苏童 陈村
陈村:随便瞎聊。聊到可以写出一万字就行了。今天吃饭的时候在想,我对一个问题很感兴趣,我会碰到一些写小说有障碍的,就是你觉得哪些地方很擅长,很会写,哪些地方不大会写。作家们不怎么说自己哪些地方写起来要头痛的。就像我这种人,人物一多我很头痛。写小说,我弄出三四个人蛮好的,要是弄出十三四个人我就太头昏了。像一个导演啊在舞台上就不知道让那些演员干什么。每个人都应干事儿嘛,你不能让一个演员站上去就不动了,总要给他一点任务,那么人一多我就犯糊涂。还有一个呢就是远不如你了,你是很少见的能够写男又写女的。一般男人写男人女人写女人。女人写出来的男人也不好。哎,但是你很奇怪能写出男人也能写出女人。我看到写女人头也痛。
苏童:这头一个问题其实要分开来说,首先与年龄有关,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确实血气方刚,从来没有感觉到小说会有写不下去的时刻,所谓障碍几乎是不存在的。
陈村:那个时候从来是不怕,也没去想“应该”怎么写。
苏童:那个时候是天不怕地不怕,主要是鲁莽的写作冲动决定了一篇篇小说的开始,其实对小说最后的面目是没有预期的,也没有过多精细的设计。小说的人物,基本上是由叙述者决定,他遇到谁,谁就粉墨登场,叙述者不需要了,那人物有可能突然消失。现在看那时候的作品,一方面对人物是弱化处理,另一方面,对自己塑造人物的能力,也是没什么自省的。所以盲目自信,开了头就可以写下去,唯一的破坏性的举动就是这一页稿纸觉得涂改太多了,我就把它撕掉。那个时候都是稿纸么。
陈村:我也是,改得看不清楚了重写。我最怕抄稿子。
苏童:那个时候我是部分重写。写不下去的记忆,这是几乎没有的。即使有的写到中途你觉得,唉,不是这个味道,哪不对头,那先放在一边也有,但是这种现象不是太多。有时候这个稿子就是说扔了就扔了。有时候过了一阵找来再看,发现一个角度,或者拉一个人物出来,一下子感觉小说又获得活力了,可以推进了,那么又会写下去。我有几篇小说就是这样。好像《南方的堕落》就是这样的。扔掉了很长时间,那年1989年正好我女儿出生。我太太产假满月了,满了要去上班了,我回去要尽一点义务啊。那个时候我在南京。请了几个月产假回苏州去摇孩子。孩子睡觉我就在那边写,就是把以前一个扔掉的稿子接起来写,但是这个例子很特别。现在看起来,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一旦扔下,再拿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有可能叙述方向错了,这个一错就错到底了,一条道走到黑,是无法修正的吧?只好等待收获错误,收获意外了。
陈村:写长篇的时候要维持统一的叙述语调,有时候还靠信心。写着写着会觉得这样写下去对吗?
苏童:一部长篇小说自然要依赖所谓大构思,对长篇的信心其实就是对“大”的信心,“大”不排斥精巧和细腻的叙述,叙述是有技术含量的,姑且把叙述叫做“小”,但是再美好的叙述也可能会被这个“大”构思歧视的,不是叙述背叛构思,就是构思否定叙述,长篇的辩证法就是这大和小的辩证法。长篇的麻烦,就在于“小”做成“大”的麻烦。如果写不下去,那就是你发现“小”越来越小,不能垒起“大”了。最终无所适从,最终你不知道是大出了问题,还是小出了问题,干脆不管了,什么大和小,也许没什么长篇的辩证法,只有一个直觉的引导。
陈村:所谓舒服不舒服。
苏童:对,就是舒服不舒服。我有一个毛病,就是不能忍受连篇累牍的对话,哪怕对话的功效再好。在我的所有的小说当中,长篇小说当中,我不能忍受人物之间超过一页的长时间的对话。这个是毛病。就是不觉得小说可以这样子。用这么长的篇幅去对话,让叙述一边站着。
陈村:写两个人的对话。
苏童:写两个人的对话,篇幅也严格控制。这肯定是我的偏见。没有什么依据。就像我到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怕用双引号。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到现在也不想改。人到中年以后自己对自己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现在会写不下去,要勇于承认障碍,学会对待这种障碍。写不下去往往有一些原因,很多时候,倒并不是因为对人物的前途故事的走向感到茫然,而恰好是路途太多,你不知道哪条路是最好的。
陈村:歧路亡羊。
苏童:对,就是这么一个感觉。或者说是因为头绪太多了,缠线了,突然觉得每一个头绪都有可能精彩,那么也就不知道哪个是最精彩的。具体说,你自己营造一个故事,一个人物,结果使他们造反,在挑战你的控制。你就惨了,似乎有亡国之痛,一切似乎一下走得很远了。是你的一部分,却不在你控制之中了。
陈村:一放出去就出去了。
苏童:对!他脱缰了,你本来以为是可以驾驭这匹马。他妈的,一个不小心,怎么了,是个野马!你收不回来,这时候会造成你的问题,你突然要停下来了。
陈村:短的呢容易掩饰这些。
苏童:对,这些困境在短篇小说里头不太容易出现,因为短篇小说,首先我要的不多。要的不多,是一个局限,也是一个自由。它就是一唱三叹。所谓的叹是余音绕梁,你只要负责唱好。一唱,就那一唱。因为毕竟是那一唱,基本上不容易跑调。
陈村:它容易控制。
苏童:短篇把你压缩在某一个平静安宁的轨道上。我觉得习惯了那种文字运动,如果说短篇也是一种运动的话。事故不会太多,享受就比较多。
陈村:那么觉得什么地方比较难写?
苏童:一堆人物搅在一起写,最难,但是举个例子,如果人物是铁,如果能有一种磁石一样的场景,人物就都自然聚拢了,一个个在一起比拼性格。当然你要说写一堆人物的,我觉得最完美的小说就是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是人物组合集体出动,一个最成功的范本。因为这个故事也很简单,但是用母亲的棺材做了磁石,家庭成员们就都被吸了上来,很自然搅合在一起。
一个家庭的人物组合在当时是蛮吸引人的。用人物命名来做一个章节,而且每个人物就是这样展开,连环的,素描般的。
陈村:它的命运呢其实是有一点脱轨的。但是它也不走远。
苏童:像这样的作品有时候你要做一个很漫长的构思。有时候小说很顺畅,其实是你本身的构思天衣无缝。就是没什么漏洞,它不会进水,它不会渗水。就像福克纳的构思永远能繁能简,《弥留》要写很多人物,但是他的故事的推进的力量其实非常单纯,就是要给母亲去送葬,众人的一段旅程。这个线索这样扯出来,行云流水,围绕着这个线索,人物就一涌而上了。
陈村:而且要求还很高,因没什么故事,如果说你人物写不好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苏童:对。我们现在的兴趣,无论如何转变,不能离开人物。我一直在说我在后退。这个跟进步、退步、先锋、古典什么的是无关的。我说的退是叙述上的后撤,撤回古典阵营,扛起一面人物的大旗再说,就是说你对人物的依赖程度,有时候基本上是一个生命之水。我觉得像我也好外面我们这帮同行也好,在写到一定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强烈的意识,就是为自己的人物担忧。这个人物可能不可能是一个新的,或者是有意义的,有文学史意义的经典形象。第一要会做这个审阅、盘算或者是觉得推敲我写的人物到底……
陈村:到底有意思吗?
苏童:对,意思大不大。尤其当你要写一个长篇小说更是在这样。世界上这么多人,你却还要找人,这个人物在你周围,只是隐蔽起来了,所以对你来说永远是在找一个失踪者。问题就是在于找的时间或者是找的方向。找,就是推门,黑房间“啪”那么一推。进去都是黑房间,没有灯,你要把他揪出来,打扮好了,才有灯光,别人也好,你也好,才可以判断,这个人物是不是大家需要的失踪者。
陈村:像马原讲得蛮有意思的。马原讲他写小说呢,他说第一句话非常要紧,他说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它第一句话出来,第二句话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跟着一圈一圈的倒下。
苏童:对。对第一句话的依赖其实是对节奏的依赖,怎么说呢,是对一种基调的依赖。
陈村:基调,非常好。
苏童:是基调。
陈村:有时候会非常不一样。如果你一开始写的一句话错的,写着写着就会越来越不舒服。
苏童:我觉得以前的古典作家不在乎的,上来就是某某年几月几号,某某人在某地点干什么。现在的作家,我发觉对第一句话的依赖程度有点疯狂。就像现在最火的帕慕克,第一句话都很讲究,都特别特别的讲究。
陈村:第一句话第一个场景出来的时候好像都赋予它更多的。
苏童:对。第一句话我觉得就是找调,调一下找到了,他才能有信心这样写下去。
陈村:以前是啊,像刚才讲的那个《我弥留之际》,我开头看了好多页,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苏童:但是到最后我们发现其实是可以概括的。其实到最后是一个背叛。从爱到背叛,从哀悼到遗忘,冠冕堂皇。父亲最后是去娶了一个新媳妇,所有的孩子送走死去的母亲,迎接了一个陌生的母亲。这个我觉得是整个构思,他到最后很牛的这个。你看这个小说从结构上来说典型的是树枝式的。这个事件,那口棺材,其实真的是一个树干,这个树干不需要很关心嘛。只要很简单的送棺路线,事情自然发生。然后旁边就是那些树枝,就是那些孩子和丈夫。最后树枝树叶抛下树干,背叛了树。
陈村:我想问的是,我们换个场景讲,比如说红军长征,我们写长征的那么多作品,写的都是怎么过大渡河啊过泸定桥啊强占腊子口啊,都是一路的艰难险阻,有点像《西游记》里面那种九九八十一难。打过去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在我们所描写的路途当中,这么漫长的路途当中很少看到一些鲜明的形象出现,人是虚的。我们用一些总体的概括而不是用个体的描绘来讲一个事情。福克纳的作品中,其实像一个由头一样,就是说给他一个好像虚假的出发,就叫你完成这个主线的任务。就像足球场上有一个球一样。没球大家乱奔你觉得大家很荒诞啊。有球,那么他们就走过去了。
苏童:对。众多人物在一部小说当中均衡塑造,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耗脑筋,但是《弥留》恰好是第一步走好。用单纯的一个事件做一个树干,然后把所有的故事人物挂在树枝上。这种很简单的结构方式,产生了一个很震撼的作品。
陈村:有一些小说比较虚一点没它那么实。像《红楼梦》那样,《红楼梦》贾宝玉好像是要跟谁谈恋爱一样,其实不是这个东西。
苏童:曹雪芹这个小说牛的是从虚到实。现代小说的笔法它引导人们从实到虚,是不是?然后这个小说就是倒过来,我就觉得大家之所以这么多年来赞美《红楼梦》,确实是一个无法逾越的经典。
陈村:而且它在两界的措施非常自然。
苏童:但是你也不能说曹雪芹的此前此后,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没有第二部么。所以像这样的小说想法,怎么说呢,有可能一个飞来峰,飞来的一个想法,你也很难说他的出手就是牛逼成这样,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像一个当代作家一样,他要写第一部然后第二部第三部。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写,因为我们看《三言二拍》的那种事。当然我们不能说像《三言二拍》没意思。但是《三言二拍》确实就是一个世俗生活,就是用世俗的腔调和世俗的态度去对待所有的关于世俗生活的,就是这样的。所谓高低之处就在于此。
陈村:就是在《三言两拍》中最后最多有点道德训诫。
苏童:那时候最虚的境界就是鬼怪玄灵。但是这个《红楼梦》的境界是讲出路的,是自觉的灵魂探索。它从一开始就是暗示了关于生死问题。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研究曹雪芹作为一个职业小说家他的心情,或者说当他坐下来写的时候的心情。是一种作家的心情还就是一个普通人的心情。这个是需要研究的,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心情才导致他写了这么一部非常牛的《红楼梦》,还是我们说的有这样一个身世的一个普通人的心情,记录自己的人生,结果弄出来这么一个警世之作。所以像王朔老师说:一不小心写了一个《红楼梦》。我老觉得是曹雪芹一不小心写了《红楼梦》。
陈村:一开始,也许是一个真的事情,有根的,也许不便写要把它模糊了。
苏童:对,很怀疑当时,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他在开始写这个八十回的时候,他到底是把自己看作谁,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作家那么神圣的价值体系在他心里。他到底是要干什么,他是写着好玩的,还是要传世的,还是因为我们以前说的有感而发。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他精心谋划出来的东西。
陈村:它不是一个推理出来的一个东西。
苏童:对。
陈村:我们评论家论文经常是推理出来的,因为这样所以那样。写小说的时候常常不是推理。因为小说它是不可以用形式逻辑将它推理了的。我们还不大明白人的逻辑,小说也就难以逻辑。这个人因为杀了人所以要逃跑。逃跑呢现在交通发达所以他跑得很快,但是警察很多,所以又把他抓住。因为所以。这个推理出来的小说变成木乃伊小说了。它里边必定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和因果,有符合我们人的处境的符合人的天性的一种东西。小说中有些好,就比如你写那个叫《妻妾成群》,你那个《妻妾成群》后来拍电影。对这个两面我不讲优劣。其实一个是很干的电影,一个是很湿的小说。你那个小说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里面的感觉是湿漉漉的,有一种晦暗的,在墙角上长一点青苔啊或者是什么的那种情景,江南的。在这个小说里面我觉得做得比你后来的《我的帝王生涯》都要好,就是说,它里面似乎可以看到一种活的东西在滋生。
苏童:它看得见。
陈村:很润的就是,不是说我要去把它……
苏童:因为它阅读的愉悦带来的很少,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我也要求看得见。但小说在看得见之外更多的要想得透,想得通,想得到。这个是想。小说因为跟哲学跟这个别的什么东西不一样。
陈村:它本来就是写具体生活、形象的。
苏童:对对。小说不要把它弄得那么高,把它无限地高端化。小说是一个什么东西,回归传统来说,我们都知道。以前的话本是干什么的,它就是完全给民间的消遣品么。完全是针对民间的。从来没有说达官贵人文人雅士是小说的服务对象。
陈村:而且写了小说还不敢署名。
苏童:当然这个我们是中国小说的那种源头,那么西方小说一开始也是有非常大的舆论和娱乐功能的,是吧?你比方说法国小说它当时的所谓所有的骑士小说浪漫小说。这个东西它完全就是消遣品,小说只是在发展过程当中异化了,变成我们如今理解的小说,显示它比较强大的功能。从某种意义说是意外。
陈村:我曾经写过一段文字,我就说其实从讲故事来说呢,《十日谈》啊《三言两拍》就够了。那时的手段技巧,对表述一个故事来讲就足够了。
苏童:从小说的世俗性上来说这个已经做到。我们当然后面都是在重复。
陈村:就像我们现在喝茶的杯子。我们这个杯子呢其实它的功能也蛮好的。它没什么太不好看也很有光泽,可用,它工艺已到一定水平了。但是做杯子的人是不甘心这样的。我们就是做杯子的人。就是你总要想耍点花招,还要有些变化,或者说多一点点东西,所以呢一代一代的人在小说的叙述上花了很多的力气,想逼近“人”,所以变成了现在这样子。
苏童:换句话说我们家具永远是家具。当然我们现在说明式家具多么的好多么的大气,清式家具多么的雕琢。这也是一个时代贴给另一个时代的标签,但它家具永远是家具。就像我们现在一样的,对小说我想差不多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一直比较反对这个,反对把小说的教化功能跟别的各种功能无限的提升,然后给小说施加压力,给作家施加压力。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合理。
陈村:在这个里面有些困难就来自于那个所谓的俗的雅的,我加工到什么地步才是对了?当然小说有很多写法,也可以把它写成不一样,比如某一类人看到这语言很喜欢,另一类人看到故事喜欢,像那个《基督山伯爵》,觉得那个故事很过瘾。
苏童:小说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是个人见解。我一直比较相信,真正的作家其实你的终极目标就是面对一个读者,就是一个刹那一个相遇而已。我们不要把它细分了。那个布鲁姆,写西方正典的那个。我看他对经典的解释说得非常好。他说经典就是也不可能让你变得更好,也不可能让你变得更坏,下面一句话就妙了微妙了,他说就是让你更好地知道如何来利用和品尝一个人的孤独。他说经典教会你这个。这个话我觉得是有道理。他完全否定了所谓对某一部经典小说无限的要求,他最后落实到一个人对一个人。而且甚至落实到孤独上面。有大量的文本可以说明。卡夫卡,你现在读卡夫卡,我们现在给他生发出无限的后现代派的意义。其实这就是一个孤独到顶的一个人的文本。
陈村:而且那个也就是说,一个好好的作者在跟你谈的时候,他谈的必是一个人的感受。
苏童:对对。最后经典的意义很明显,还是从个人到个人。这个空间其实非常非常之狭窄。远远没有我们现在所描述的那么一种宏大意义,其实并不存在那种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话说得特别好。
陈村:我技术上讲,觉得写过那么多年小说,大家用心一点,从技术上讲都没许多困难。你要编一个故事两个人物,把这个故事编圆了,这个大家都会做。但有一种我们不能掌握看不见的东西。说大师吧不讲我们。大师也不是说一篇比一篇写得好。按理说他经验更多啊,他手法更纯熟,他知道更多东西,他应该在下篇更好吧。但就没有。下篇跟那个刘翔跑一样的,你不能指望他每次都破记录。
苏童:福克纳的《圣殿》就写得完全像是报纸上的。有时候也正常,一个大作家给小报写,也是艺术探险,成功不成功是另一回事。我觉得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在他一生保持积极向上,有时消极和积极是混淆的。所以有时候我很理解你这几年不写作,因为写到后来畏惧越来越多。畏惧越来越多,是一方面,还有你自己各种各样生活当中实际原因。我觉得还有一个最令人憔悴的,就是写到后来你会觉得空虚。
陈村:问自己,你为什么要去写它呢?
苏童:会有这个空虚。然后这样的一个空虚还会造成自我质询,你写这一部或者好多年前这一部,哦,这个短篇我自己现在看了真喜欢,那你再来第二篇它的意义在哪里?好多是来自于这样的疑惑。那种疑惑,最后让你陷入虚无。
陈村:是有一种惯性。比如我一直在写小说,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呢,我明天不会问我为什么要写小说。反正就是惯性就写下去了。
苏童:对。
陈村:当你停下来的时候,再开始,就问为什么。
苏童:所以作家真的要干什么不能多问为什么。为什么是一个非常害人的事,对于一个人的生活来说,问为什么是悲剧。不要问为什么,学会不问为什么这才牛逼。
陈村:你我第一次写小说的时候也没有问为什么。
苏童:所以我觉得好多地方是生理需要,我觉得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生理需要。生理需要不要问为什么。
陈村:中间有一个差别,就是当年有一种要把它写下来的强烈的欲望。今天这种欲望不一样了。对我来说,今天就没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把什么东西……
苏童:我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因为这个意义是压倒一切嘛,或者你觉得这个故事是太辉煌了。太伟大了。
陈村:我就讲那种我自己的经历。年轻时候你什么都不问了,什么技巧啊什么语言啊什么的你不管,你只想把这个事情这个人写出来。到后来呢,你写着写着就来东西了,有产了,你觉得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结构,然后用一个什么什么的。开始将一种技术的东西加进去,再写下去呢再加。我在停掉小说的以前,大概80年代末……
苏童:《鲜花和》是最后一篇了。
陈村:《鲜花和》其实已经是一个例外了。我在那个以前,到1989年以前几乎不写小说了。后来写过一两个短篇,都是被人家逼出来的。人家《收获》说要什么的,我就给人家写一篇吧,《临终关怀》。那个时候的我有点作怪。我蛮喜欢那种不太写实像西方有点抽象意义的小说。可这种小说再写再写,你会发现不对了。本来小说我就讲是一个具象的东西啊,本来可以脚踏实地的。那种具象的东西都逐渐被我抽掉了,那么就变成了一个半幻想半真实的一个故事。我写过一串这样的短篇,写到后来发现不对了。写到后来比那篇《死》要远,写过《起子和他的五幕梦》、《上街走走》、《F,F,F》等。其实写到《象》的时候我已经不愿意好好说话了。是用倒叙在说。《象》变成像一个人在说,其实你已经无意好好讲故事了。可能跟我这人性格有关,写小说老那么写我会烦,我又不是巴尔扎克。
苏童:对。
陈村:用一种办法写所有人的故事我会烦。写那个《一天》,写了一些后,这个稿子被我扔下一年多。
苏童:但是《一天》还是很震撼,现在看起来。其实你还有一个小说更游戏的,比较游戏的就是拿很多歌词串起来的。
陈村:《我的前半生》。我写《一天》的时候我没找到叙述方式,只好扔下了。后来有天我跑到昆山去闭门写作,我就想起来应该这样写,就是你不要把自己弄得很聪明弄得词汇很多,我用最简单的句式来写。不要觉得我可以弄出很多句式可以很花哨,可以用一种文人的士大夫式的一些腔调,或者很书面语式的来阐述一个其实是很漠然的生活,应该不动声色。
苏童:这是一个听上去很简单的,就是一个简单的人生,一个很简单的故事,用最简单的方式。
陈村:有时候写着写着会死在那里,你知道这个小说是有价值的,但是觉得你使不出力了,你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去对付它的时候你就会就傻掉了。但是写小说,对我来说还是喜欢的,造人,我觉得很有意思。
苏童:是。
陈村:因为它是虚构的。因为我们生活中一虚构就是吹牛啊,就是骗子。
苏童:说实在的他妈的生活当中就剩这一件事了,虚构,让人跟现实生活可以拉开一个距离。说起来还是幸福,还是有一点幸福感的。
陈村:而且是可以给你一种幻想。
苏童:确实,我一直说这样你一个人去寻找两个世界很难,但写作就是一种捷径,写作就是唯一一种捷径,寻找两个世界的捷径。那么魅力也就在这里。
陈村:你寻找两个世界,而且过了几辈子的生活。
苏童:过完了,人事沧桑,我替别人阅历。你比方说《我的帝王生涯》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典型的就是我通过这个小说我完成了好几个人生。
陈村:而且完成了你不可能的人生。
苏童:对。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其实是掠夺的欲望。
陈村:有些小说很奇特,我以前说过好几次。我说你的男孩写得好,我蛮喜欢把男孩写好,男孩是很难写的。人家讲女孩难写,其实女孩或一个女人大概容易备受关注,或者写得可爱或者写得什么清纯。男孩很难些。我觉得你今天再写男孩可能就不如当年了。
苏童:对对。
陈村:就像小仲马再写《茶花女》。
苏童:我写男孩系列那个时候还是三十岁以前。因为我自己其实开窍蛮晚的,我就是这方面,晚。所以我觉得是我自己比较挽留那段所谓少年生活,是因为自己的一种性格啊各种方面原因,好像自己很无意的把它时间挽留得长了一点。所以我自己觉得在写那些小说的时候,我其实在闻自己的袜子,我觉得有这种感觉。我是比较喜欢闻自己袜子的,这是怪癖。
陈村:哈哈。而且那个很好。我就讲人大了以后呢也许可以深厚,可以辽阔,但是他不大纯了。他很浊了。浊么那大海也是浊的,黄河长江也是浊的。但是你那些比较清新的比较容易受伤害的那种东西都没有了。
苏童:你刚才说什么关于写女性?男写男,女写女?我一直不同意男女分治,我们现在所流传在世的所有小说当中最好的女性形象,是谁创造的。所以我们现在要说的女性形象,比如说《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妮娜》,《红字》,这些女性全是男性作家创造的。
陈村:对。
苏童:这个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自我纵容,男性作家逃避描写女性,我从来不觉得可以给自己找理由。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写女性写得好。但是这个外界都说了十几年了,说得我自己都认为我写女性写得好了。现在是这种状况,感觉自己接受了一个古怪的荣誉。
陈村:写女性呢,我觉得有一种愿意。什么叫愿意呢,就比如说我写一男一女两个人的事儿。那么我的立场很容易就是想把男人的想法表述出来。
苏童:对。
陈村:然后就是压抑了或者忽略了女性的想法。如果你好好去想女性在这个处境下会怎么样,其实你大概也能想出来。但少感性的东西。
苏童:其实我一直这么说,也就是说你不肯给她一个立足之地。就是思想上和创作过程当中不肯给她一个立足之地。是你觉得是你要站在那,而且你有一个预设立场是男性立场。而且多多少少里头有一个潜意识。不能说是沙文主义但确实是有男性优先,觉得她的这个角色不要来冲淡我这个男性小说架构,男性的一个小说架构。他有这么一种潜意识其实恐怕多多少少会存在。除非有一种现象,就是从一开始就走反棋。我就是写一个《包法利夫人》,我就写一个《安娜·卡列妮娜》怎么样?我看你的立场能不能就是很固定的在男性架构的。
陈村:就是不要男主人公的。
苏童:男性角色是配角。可以试一试就是这样。我觉得一下就可以顺过来了。
陈村:因为已经无能,就像一个房子啦,这根梁这根柱子没有了就是只能用另一个柱子。这也是一个办法。这种平衡是蛮有意思的。我在想我看那么多女性写的也是。其实女性写到的男人多半也不大像男人。
苏童:我觉得我写的女人也不是很那么女人
陈村:不,你有一个关注女性命运的眼光。
苏童:应该关注。
陈村:有些人他不大关注女性的命运。觉得女性命运可能也是可以附带在男人的……
苏童:对。其实还是刚才我说的,他是有沙文主义的。多多少少有一点。
陈村:一个作品写出来,自己读作品的时候会有点不一样。会看到那些过分了地方。我曾经改过《鲜花和》。那两年里,我因为一个事情中掉了,断过以后一看不对。这样写是不对的,你会修正一下立场。让大家都讲他的道理都做他的事情。当然做的还不够,不好,但是总算有点意思。就是说让别人也要活一活,让别人也要说一说,不要你一个话筒拿在手里都是你一个人唱。
苏童:对。不要做麦霸。我觉得现在好多人自己给自己设置地位啊,或者说就是麦霸心态。麦霸心态就是要唱而且老唱,声嘶力竭也要唱。
陈村:你们听着。
苏童:不听不行,听着。
[陈村按:每次做文本,最让我痛苦的是被篇幅害了,只能挥刀自宫。只能等最后结集,一一复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