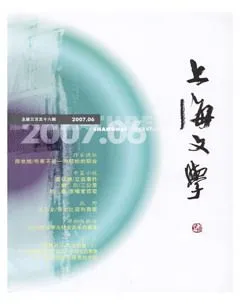冬至
对北半球的人们来说,冬至这一天,就像长途的旅人在缓慢嘈杂的火车中经过的最后一条黑暗隧道,艰难而漫长。彼岸和此岸的时空常常会交错重叠,令不得不走夜路的人,惊倒在重现的亡者面前——只有对繁琐仪式一丝不苟的执行,才能稍稍缓解人们心中的焦虑和不安。当然,咬牙穿过这一天,白天就会慢慢地变长,春天的小牙齿,将要一口一口地啃噬掉严冬,但是在这之前的等待,已经快要令人承受不住。
这一天正是冬至。扫墓的人们,像一杯泼在泥地上的黄酒似的,从城市的中心流散到城郊的墓地。对大家族来说,扫墓和郊游,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在滔滔不绝的闲谈和层出不穷的零食之下,若还能对亡者保持思念倒反而显得不识趣。当然,在公共汽车靠窗的座位,也能见到一些沉默的,皱着眉头的乘客。林溶就是这样一个孤身的扫墓客。此时她怔怔地望着窗外,心里空荡荡的,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难过。她的目的地是城郊的玉韩县。因为春申城唯一的一座小山就坐落在玉韩县,所以本城的公墓多分布在此,在冬至或者清明这样特别的节令,通往玉韩县的道路就会变得格外堵塞。
车到了公墓。烧完香烛,林溶抱膝在墓碑旁坐了一会儿——虽然还只是下午三点多钟,冬日的阳光却已呈现出颓势,不咸不淡地糊在西边的天空上。算来父母去世已经十年了,失去至亲的悲伤被时间冲淡得只剩下一点模糊的印记。父母去世的时候,弟弟林霁才十五岁,正是爱闯祸的年纪,而那时林溶才刚毕业。今晚,这小子要结婚了——总算是一个过得去的交待,她想,她很少回想往事,只向前看。林立的墓碑,像一束束香,上指着无垠的天空,温柔而深沉地标记着家人们的思念。林溶用目光扫过陌生的墓碑上密密麻麻的名字。也许时间不过是把人类当作漂浮的跳板,在茫然无垠的宇宙中嬉戏,可是,谁又考虑过跳板的感受?墓地的风从她的肩头掠过,令她不禁打了个寒噤。她站起身,掸了掸衣服。
返程的车上,林溶的心情就像周末早晨拉开窗帘的落地窗,一片明澈。可以把弟弟这个捣蛋鬼托付给别的女人了,她对那个新娘几乎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
“可以吗?”一个和林溶差不多大的美貌女人,指着林溶身侧靠窗的座位。
“当然。”林溶笑着说,挪进靠窗的座位,将靠走道的座位让给她。
一个穿着白色风衣的女人,还拉着一个咖啡色的拉杆箱,看上去,像是刚从外地回来。不知为什么,林溶总觉得她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她自嘲地想,也许是自己老了,才会对同龄的美人,产生莫名其妙的不适感。她摇摇头,想把这些虚妄的想法甩出去,转头望向窗外。天色已经晚了,路灯和霓虹灯辉映出一片灿烂,车厢内还是一片昏暗,窗玻璃上倒映出那个女人的侧脸和颈项,洁白而优雅。
在春申城最繁华的地界下了车,林溶如释重负般疾步向举行婚礼的饭店走去。不知为何她有些烦乱。要不是这一天假期来之不易,她不会把扫墓和出席婚礼放在同一天。一边胡思乱想,一边已到了饭店的门口。林溶的脚步慢慢地停了下来,她仿佛站在一个飞速旋转的巨大的轮盘赌的面板上——她想到是哪里不对劲了!如果车外比车内要明亮得多,车窗上怎么会映出车内的景象?她又怎么会在窗玻璃上看到坐在自己身旁的女人的相貌!她心跳得怦怦直响,回想当时的情景,没错,不仅如此,那块窗玻璃上除了那个女人的影子,并没有车厢陈设的倒影,甚至也没有她自己的脸!
林溶哆嗦了一下,愣在当地,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一辆自行车撞在她的胳膊上,将她朝前带了好几步。她节约地使用着这股惯性,朝饭店内走去。
三楼大堂灯火通明,遍地撒着鲜花,满墙流着奶油,弟弟和他娇美的新娘站在花门下,僵硬地笑着,和来宾握手拥抱。远远地,林溶停下脚步。林霁尴尬的样子真好看啊。读中学时,不知道被老师多少次家访,那时的林霁,恨不得把头也塞到领口里去,林溶则不得不顺着老师的抱怨大声喝斥,其实心里还憋着一个放声大笑。今天,终于可以松松快快地笑话他一番了,她刚扬起嘴角,却将眼睛弄得酸酸的,便绞了一下手,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过去,歇落一声暗暗的长叹,抱住弟弟的肩膀。林霁安慰似的拍着她的背,一时,姐弟俩都没有说什么话。
弟媳也向她伸出手来。林溶看着那只洁白光滑的手,竟有些发怔,一时忘记了回应。抬头去看她的脸,林溶吓得倒退了一步——她竟然长得和车上的女人一模一样——不,根本就是!那个女人此时正挽着弟弟,穿着雪白的婚纱微笑着。在林溶看来,这笑容是如此凶险。恐惧压倒了伤感和喜悦,她连来宾胸针都不记得领,便魂不守舍地向大厅走去。
在主桌上找到座位坐下,林溶发现自己已经汗透重衣。弟媳是谁?为什么能在完全相反的光照条件下照出倒影?她出现在弟弟身边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把车上的经历告诉弟弟,他会不会认为我发了疯?林溶反复捏着杯子出神。她觉得口渴难当,拿起杯子猛地喝了一口——黄酒!怎么会是黄酒,刚才明明要的是可乐啊?她艰难地把那口冰冷的还带着些土腥味的黄酒咽下喉咙,拿着杯子迷茫地问:“妈,怎么是黄酒?”
林溶妈无奈地笑着说:“只有这一种酒啊……”
妈妈!林溶脑中轰得一声,打了个激灵,涨红着脸从座位上蹦起来:“妈!!!你……”
林溶妈的微笑依然不变:“你是林霁常常提起的姐姐吧,我是小蓉的妈妈。”
哦,是弟媳的妈妈?是我记错了妈妈的长相,还是真有长得那么像的人?毕竟是有安慰性的一种说法……可是,弟媳也叫小蓉吗……林溶只觉得腿都软了,勉勉强强地重新坐下,多喝了几口酒给自己压惊。不管怎样,在初次见面的亲家面前就如此失礼,实在是丢脸至极。林溶用湿纸巾敷着自己滚烫的面颊,决定暂时不去想这些恼人的问题——到底还有什么能比弟弟的婚礼更重要啊!
林溶木然地将目光投向另一边:一个六十多岁左右的老人,正和邻座谈笑风生,忽然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他转过头来,抿了一口酒。看到他的侧面,林溶一颤,将酒洒在了雪白的桌布上:“爸爸!”她像被雷劈了一下似的,腾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不会错,一定是爸爸!那么刚才那个,也一定是妈妈!震惊、恐惧、眩晕和委屈混在一起……她不由蹲下,抱头大哭起来。是幻觉,是梦魇,还是巧合?十年来,她没有一天不想起爸妈,却没有一个夜晚梦到过他们,这是为什么?他们怎么可以就这样不要自己和弟弟了?
整个大厅忽然变得死一般的寂静。林溶此时已从深渊般的风暴中心打捞起一些理智。她抬起满脸泪痕的脸,父亲正慈爱地看着她:“小溶,你哭什么?”正是爸爸。这声音像在她心上狠狠地踩了一脚。她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大滴大滴的眼泪掉出眼眶。她应了一声,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她扑上去,想要勾住爸爸的脖子。可是爸爸却眉头一皱:“别过来!”
林溶的身体僵住了——爸爸到底还是那么严厉。妈妈在一边无奈地笑着。这时,宾客们呼啦一声围了过来,似乎在念叨着什么:
“居然把酒泼掉了,这孩子真不像话。”
“老林家的孩子,没家教。”
“她要怎么赔啊?”
“拿她自己抵数嘛!”几个年轻的宾客开玩笑般起哄道。
爸爸妈妈拦着他们,惊恐地向林溶喊道:“小溶,快给大家道个歉。”
道歉?为了什么道歉?又向谁道歉?林溶一头雾水地愣在那里。不知不觉间,宾客们围成了一个圈,几个年轻人甚至伸手来拉林溶的胳膊。爸妈被挤到厂外圈,模模糊糊地,林溶感觉他们几乎要哭出来的样子。她不免更奇怪了。到底怎么了?她迷迷糊糊地低下头,看自己身上有什么地方引人注目。忽然有人惊呼:
“新郎来了!”
人群哗地散开一条过道。身材轩昂的弟弟,穿着雪白的西装,特别严肃地走过来,像一份合同下的落款。林溶看着林霁,心里恍惚。这孩子好得意的气质。真是长大了,像个当丈夫的样子了。林霁已走到了林溶身边,他沉着嗓子说:“谁敢碰我太太?”
太太?人群沉静下来。林溶茫然地左顾右盼:弟媳也在?没有见到她啊……他不经意间一低头——天,这是婚纱?我……就是弟媳?那个奇怪的女人?那么我又是谁?姐姐又是谁?一个接一个荒诞的想法,像潮水般漫过她的脖子,令她忍不住倒向弟弟怀中。林霁有力的手臂围着她的肩膀,温和的声音中却带着一种绝对的权威:“谁也不许碰她。”
她眼前华美的婚礼大堂忽然扭曲,变形,像潮水一样退去了。血红的厚绒地毯变成了天青色的河流,宾客们坐着小船在河流上载沉载浮……他们面目模糊,也无法从中分辨出林家父母了……她和林霁站在一条微微起伏的小船上,静静地看着这一切,林霁不说话,她也沉默着。水波拍打着船沿的声音,扑到他们脚下,又像轻尘一般散去了。
“嘭”地一声,小船被暗流冲得靠上了河岸。“回去吧。”林霁温柔地对她说。他站在摇晃的船头,将她先扶上岸。她一踏上青色泥地的边缘,便回身来拉林霁……船远了……林霁没有回头。昏暝的天空下,他挺拔的背影像一座碑。
墓碑。她面前这一块。“小弟林霁之墓”。右边紧挨着的,是爸妈的合葬。没有婚礼,没有河流,没有爸妈,没有弟弟。她缓着呼吸,扶着弟弟的墓碑,坐起身来。
夜已经很深了。繁星刺破了深蓝的绒幕,却没有办法将光投到人间。
“怎么一个人在墓地里睡着了?”
“大概是累了。”
“这是你弟弟?”
“是。”
“才二十二岁,很年轻。”
“是。大学才刚毕业呢。我们去了四川,是我早答应他的毕业礼物。入川的路上出了事。我没想过能同来。我也没想过要回来。……这孩子特别得意,人人都喜欢。他今年本来该二十五了,该结婚了,也会有孩子。”
“回家去吧。”
“这儿就是我的家。”
“他们和你失散了。但是,会再见面的。人人都有一死,所以不必迫不及待。”
林溶拼命地抿着嘴唇。过了很久,她抬起头。身边是年轻的守墓人,温热的手掌搭在她肩上,沉默地看着她,在黑暗中,像一座碑。
“好吧。”
他们向墓园的大门走去。他缓慢地推起两扇沉重的铁门,咣啷啷地锁上,黑暗无垠的墓地,一灯如豆的门房,便已将林溶隔在外面:“下次,和春天一起来吧。姐,清明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