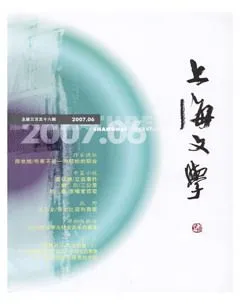你带什么东西逃走
在一个弯脖子老树旁,徐玢叫司机停车。司机照例一声不吭,打一下方向盘,把车拐进树阴里。“你等这。”说罢,徐玢开了车门,跨下车。
出树阴,照在他脸上的七月阳光,使他感到就像是正在抚摩他的一双同性的肥腻的手。他摇摇头,像是要把这种感觉甩掉。在窄窄的白色水泥路上走了一阵后,闻着被阳光晒熟了的路两旁各类农作物的清香,尽管走得鼻子上已经沁出了粒粒汗珠,可他心里却在慢慢爽起来,就像刚才还是四面不透风的一间暗室,突然被风吹开了一扇窗。
心情爽了一点,他就开始想一些与自己有关的有趣的事。从寒冬腊月开始,他就和单位的几个哥们隔三差五地去泡澡堂。有一次几个哥们各约了要好的女伴一起去,洗罢,各自开了包房后竟发觉很好上手。从此,他们似乎发觉了一条泡女人的捷径。约女人去洗桑拿,容易开口,也易于被人接受,但直接约女人去宾馆开房间,这就不太容易开口,也不太容易被女人接受了。所以,直至夏天,他们还常常去泡澡。碰到其中一个哥们新处了一位女友,想知道他们的关系到底处到什么程度,他们也开始这么问:洗过澡了吗?有的哥们为了表明一个女人已是他的人了,就会说,他与那女人已经洗过澡了。有一次,徐玢在单位问一位哥们与某某女士是否洗澡了,单位的头、杨红主任正好路过听见,就说徐玢:你这个副主任管得宽,还管人家洗澡的事!杨红的数落立刻引得徐玢周围的几个哥们发出哄然大笑。这天深夜,在杨红那儿,徐玢一边左手抚摩着杨红的耳垂一边向她解释“洗澡”的出处,杨红听明白后使劲用手拧了一下徐玢布满体毛的左腿,然后低声对徐玢说:我们早已经是洗过澡的了。
在七月骄阳下走着的徐玢已经不反感正抚摩着他的阳光了。他想,忙于事业忙于赚钱的男人有时候确实是一间四面不透风的暗室,而那些与女人有关的趣事恰正是一扇暗室上方的窗,或者是一阵正在吹开那扇窗的清风。不远处的晚稻田尽头有一片灌木丛林,几只斑鸠在那里咕叽叽地叫。
白色水泥路的尽头是一家初具规模的名叫“百果园”的农家乐休闲中心。望着不远处那农家乐休闲中心用青毛竹搭就的后门楼,徐玢想,今天他要去的那个农家乐休闲中心是不是他的又一扇窗或掀动窗扇的清风?
呱的一声,身旁稻田里飞起一只不知名的红嘴鸟。几乎是同时,徐玢感到眼前一暗,太阳已经躲进了云层。又向前迈了几步,徐玢感到云层低了好多,并闻到了风中挟裹着的凉丝丝的水汽,他不由得带紧了脚步。夏天的气候,说变就变的,果然,徐玢走到农家乐休闲中心后门楼时,雨点开始降下来了。从后门楼到他今天要去的地方还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好在走廊的顶上爬满了葡萄藤,开始稀疏又很快密集的雨珠就打在葡萄藤叶上,有一次,雨把一颗烂葡萄打下,那烂葡萄正巧落在了徐玢的脖颈里,徐玢赶忙把左胳窝里的皮包换到右胳窝,用左手把那颗烂葡萄拿掉。他是左撇子。甩掉手里的烂葡萄后,脖颈里那滑腻腻的感觉却可恶地还在,徐玢立刻又胸闷起来,觉得不多会儿还感觉到的那个暗室的窗和吹动窗子的清风不在了。
走廊尽头,是一幢用杉木搭就的茶楼,茶楼顶上,稻草把瓦片严严实实地覆盖住。茶楼正门屋檐下挂着几个红灯笼和几个鸟笼,鸟笼里各有几只小云雀在唧唧喳喳地叫。从茶楼门里看去,里面白汽袅袅。徐玢正要跨进茶楼,门边一个穿着对襟碎花袄的服务员就对他一低头,说:“先生下午好,里面请。”徐玢发觉这位服务员小姐是一位单眼皮的清秀女孩。在这位清秀女孩的引领下,徐玢迈进了茶楼。茶楼里面几乎坐满了人。女孩领着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空位置。女孩问他要什么茶,他说随便。女孩弯弯的双眼里露出迷惑的神色。待女孩转身,徐玢就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机。说好一到茶楼就给姚小叶打电话的。一串数字揿下,徐玢就感觉到自己的心就别别地快速跳起来。
服务员小姐把一壶乌龙茶和一个青瓷小盅端来了,徐玢抬脸用柔和的亲切的语调对服务员小姐说:“再拿一个小盅来。”但是,当姚小叶向他走来时,徐玢发现还有一个近五十岁的中年妇女跟着她。显然还要拿一个小盅。俩人在徐玢身边坐下后,徐玢觉得原本属于那间暗室的窗子和那股清风离他越来越远了。
“这是工业园区动迁部的领导。”姚小叶向中年妇女介绍徐玢。姚小叶今天上身短袖衬衣下身黑色长裤,没有穿休闲中心客房部的工作套裙。
“不是领导不是领导,挂了个副主任的名。”徐玢自谦道。
姚小叶又介绍中年妇女,说她是农家乐休闲中心客房部的崔大姐,是她最要好的同事了。姚小叶在说话时,目光显得游移不定,总是极短促地看徐玢一眼,又很快低垂下目光。徐玢则始终看着姚小叶。或许正意识到徐玢的目光一直落在自己脸上,她的目光才显得游移不定的。
“管事的副主任有的时候比正主任厉害哦!小叶家的事你可得全力帮忙啊!”崔大姐心直口快地说。
徐玢没接崔大姐的话茬,还是看着姚小叶略显沉静的脸庞。三十挂五的人了,眼睛还是很清,睫毛很长。还是白里透红的脸色,脸上竟还有一层细细的茸毛。
十多年前,看她在河滩石上洗衣服时的样子,我就想与她洗澡的啊!徐玢想道。那时,同村的徐玢常常溜到河北岸,躲在一棵大槭树后,偷偷看姚小叶洗衣服,她的衣袖绾得很高,露出的两截手臂就像洁白的藕段。
隔壁一桌上的几个茶客在交流赚钱的经验,有一位茶客开始谈论股市,说这一次肯定要破一千点,并忿忿然地警告其他几位茶客:“人啊,应该远离毒品,远离股市。”“那是,那是。”其他茶客附和。
崔大姐又开口:“徐主任啊,小叶家的事全靠你哕,她可只有你这一条门路。小叶也不容易,丈夫病成这样,一家全靠她撑着。”
藤桌上放着熏青豆等江南小吃。徐玢拿起几粒青豆往嘴里一送,看着姚小叶依旧是以前的模样,看着她如今在他面前时的那种柔顺,徐玢又感觉到那间暗室的窗子开了,清风正通过窗子吹进室内。
“小叶家的二楼二底房子没造多久,装潢也好。拆掉真可惜。”崔大姐说。她看着姚小叶,好像只是在对姚小叶说。
见徐玢和姚小叶仍没有开口,崔大姐叹口气,站起来。
“我还要到家里去一次,先走了,你们接着聊。”崔大姐站着说。“房子动迁,一出一进,一差就是几万几十万的啊。”
“动拆迁的事也不是由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这一次,徐玢终于接了崔大姐的话。
崔大姐走后,徐玢和姚小叶之间竟有了几分钟的冷场。
“我们出去走走?”闻着隔壁桌上飘过来的烟味,姚小叶说。
两人就站了起来,走出了茶楼。外面的雨竟然停了,太阳重新从云层中钻了出来,雨后的阳光好像也被雨水稀释过一样,由火红变成了橘橙色,这橘橙色的阳光照在青砖地面以及场边的矮荆丛上,使青砖和矮荆丛上的水珠熠熠闪亮。
走出茶楼前的青砖场地,踅到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径上。
“崔大姐和我一起到茶楼,你没有不高兴吧?”姚小叶说。
“哦没,没有不高兴,她是个热心人。”徐玢说。
鹅卵石小径的南侧是一条垂柳袅袅宽约数百米的大河,垂柳掩映的是一个个新造的“渔人码头”。鹅卵石小径通向不远处几排青砖黛瓦的房屋。
见徐玢看着不远处的那几排青砖黛瓦的房屋,姚小叶说:
“那就是这儿的客房,常常客满呢。几年没见你,我有点紧张,所以叫崔大姐一起到茶楼的。”
很快到了客房那里。两人在一幢独立的楼房前站住。这完全是一幢江南古民居的仿制品。楼前是一垛城墙式的立面墙,墙头砌有城堞。立墙正中偏下方的门洞类似“城门洞”。徐玢随姚小叶的脚步跨进了“城门洞”,看见两侧相距十米又各有一垛与“城墙”及正面的楼房相互垂直的立墙。立墙高度与楼房底层持平,略低于“城墙”。左右立墙各开一个月牙形洞门,可通达楼房左右两厢。在“城墙”、左右立墙及楼房隔成的井形空间里,紧贴楼房南外墙的是一座精巧的旱桥。翠绿色的琉璃瓦筒桥栏,竹节形扶手、水泥磨石子阶梯。两人从旱桥一侧拾阶而上,到了楼房第二层的外走廊。
“如果没有碰到家里房屋动迁,你不会联系我的吧?”徐玢问。两人走得很慢。
姚小叶点点头。
“为什么我说了这事政策很强,如果仅仅想打个擦边球,也需要很大代价后,你很长时间没回音了?”徐玢说。
姚小叶没回答。徐玢注意到她抿了抿嘴唇,像是要把什么话咽进肚里。不过现在姚小叶好像比在茶楼时自信了许多,目光不再游移,落在徐玢脸上的目光似乎分明在说:你还不明白吗?
在走廊东端的一个房门前,姚小叶从手提包里摸索出了一把钥匙。房内,除了一张正中央的楠木大床外,一式的藤制品,藤椅藤桌藤茶几。刚进屋内的一刹,两人很尴尬地站着,俄顷,姚小叶说:“坐吧。”
徐玢就在藤椅上坐下了。
“你男人的病仍旧靠药吊着吗?”徐玢问。
姚小叶点头。
姚小叶的双手放到了藤椅上,手指纤长、白皙,指甲修得很光滑。徐玢看着她的手,突然想到了一句不久前在书上看到的形容美女的话:手若柔荑,肤若凝脂。他想,除了手,姚小叶的被衣服遮住的其他地方又该是怎样的胜景啊。
她那儿有一颗紫红色的桑葚形的斑。十几年前同村哥们针对姚小叶的这句话至今还会时时在徐玢耳边响起。
“那里是哪里呢?”徐玢当时问。
“就是,就是肚脐下面一点。”同村哥们说。
顿时,徐玢的双眼里喷出了嫉恨的火苗。那么说,还没有出嫁的姚小叶已经是同村哥们的人了?那天晚上,徐玢整整一个晚上没有睡,他第一次体会到了自己身上的东西被强制割裂开去的那种痛楚。
那个同村哥们后来也没娶姚小叶。那哥们现在在工业园区的物业科上班,与他属同一单位的不同部门。徐玢记得十几年来向那哥们儿求证过好几次紫红色桑葚斑的事,脸上表露的神情好像是要恳求那哥们否认他说过的话。最近,徐玢还问过那哥们:你真的十几年前就和村里的姚小叶洗过澡?废话!同村哥们响亮而自豪地回答。
现在,身上生着紫红色桑葚斑的女人正和他呆在一个房间里。他想,约女人去洗桑拿,容易开口,也易于被人接受,但直接约女人去宾馆开房间,这就不太容易开口,也不太容易被女人接受。但此刻,是姚小叶自己领着他来到了一个房间啊。他又感觉到了暗室上的那扇窗以及正通过窗子的清风。要知道,那颗桑葚斑有一段时间确实像一间密不透风的暗室一样让他有窒息的感觉。
房间内的空调正在换气,发出轻微的吱吱吱的声音,一股冷气吹在了徐玢的脖子上。
“我叫你晚上来的,你为什么偏要下午来呢?”姚小叶问。
“我晚上要到浦东机场,和主任一起外出。”徐玢答。
徐玢的皮包已经放在了面前的藤桌上,他的双手则按在了皮包上。徐玢发觉姚小叶的如荑之手此刻也移到了皮包边,移在徐玢触手可摸的地方。
徐玢突然拉开了皮包的拉链,从包里拿出四份合同,摊开到了桌上。
“你家的老屋共200平方米,”徐玢说。“因为你公公和你们住一起,用足政策,可以给你们三套住房,两套100平米的,一套50多平米。合同一式四份,签吧,日子早签一个月。”
姚小叶接过徐玢递过去的水笔,开始在合同上签字。她的几缕头发突然落在了也低着头的徐玢的脸颊上,一股馨香猛地袭击了徐玢的鼻腔。徐玢把手放到了姚小叶的后背上,慢慢摩挲。姚小叶放下笔,转身一下抱住了徐玢的腰。
“哥。”姚小叶低吟。
“不要叫哥。”徐玢低声道,一边把手伸到了姚小叶的衬衣里面,感觉着姚小叶凉滑的肌肤。徐玢一哈腰,抱起了姚小叶,向那只宽大的楠木大床走去。
重新从那幢仿制的江南古民居里走出来时,太阳又不知躲在了哪里,天色阴沉沉的。徐玢仍不敢从农家乐休闲中心的前门出,他仍然穿过那个盖满葡萄藤的长廊。走出长廊,迈上白色水泥路时,他猛地发觉自己犯了一个不该饶恕自己的错:那个紫红色的桑葚斑呢?自己怎么看也不朝姚小叶的身上看!
那个同村哥们的话再次在他耳边响起。徐玢的内心开始像天色一样变得阴暗了。
司机仍忠心耿耿地等在弯脖子树下等他。上车后,徐玢从包里取出四本动迁合同,交给司机,说:
“送我回家后,你到单位把这交给办公室王主任,然后你也下班回家吧。”
司机接过合同,说:
“怎么回家了?不是还要送你到浦东机场吗?”
徐玢摇摇头。
回家后,徐玢在自己的书房里呆坐了一会儿,又打开了一只袖珍收音机。看到茶几上的笔墨宣纸,他起身,铺开了宣纸,拿起了那支狼毫笔,狼毫笔蘸了淋漓的墨汁后开始在宣纸上走动。写下一首唐诗后,徐玢摇摇头,重新搁下笔。
他摸出手机,拨通了那个同村哥们的电话。
“我一直怀疑你的话,现在我相信了,她身上有那个斑。”徐玢说。
“什么什么?”同村哥们在电话里听不真切他的话。
徐玢则已经放下手机。他又拿起毛笔。这一次,宣纸上留下了这一行字:女人的魅力是拒绝。这是一个爱情高手曾经告诉给徐玢的话。看着这行字,徐玢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来听。是工业园区动迁办主任杨红打来的。
“我已经在机场,你也快点来吧。”杨红说。
“等等。”徐玢说。
“等什么?你不是说过连替换衣服也不带,就带以前写给那个村姑的没有寄出的信和诗歌稿的吗?”
“我不想走了。”
“什么什么?你神经病又发作了?那个资金窟窿这么大,留下来你找死。”杨红在那头急了。
徐玢放下了手机。手机又响起,徐玢不接,任它响。这时,那个袖珍收音机里正在播一条新闻。播音员的声音清脆响亮:日前,逃匿在加拿大的走私团伙首领、原厦门远华集团董事长赖昌星再一次通过律师,向当地法院递交了要求政治避难的申请,加方迫于中方数次要求引渡赖昌星的压力,表示将尽快对赖昌星要求政治避难的申请进行裁决。
徐玢又拿起了毛笔。一行字几乎在一笔之间写成:古人有困而修德穷而著书。徐玢歪头一看,这一行墨汁淋漓的字显得那么遒劲有力。
“著书?”徐玢喃喃自语。想到自己青少年时代是那么安于清贫、热衷于写诗写小说,他脸上露出了甜甜的笑。
2007年2月22日完稿于青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