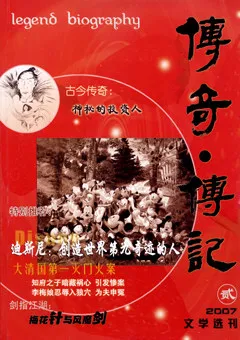大清第一灭门火案
引子
大清咸丰初年,浙北嘉兴府城里的紫阳街发生了一场离奇的大火。这场罕见的大火之后,整条繁华的商业街都化为灰烬,三十三条人命丧于火海,还有三家遭到了灭门之灾。这是大清定国以来,在民间发生的最大一次火灾了。
抱着咽了气的麦郎,李梅娘失声痛哭
话说嘉兴城紫阳街的觅秀里有一家经营字画兼装裱的店铺,称为“石梅居”,始创于大清嘉庆初年。“石梅居”有三开间门面,当中一间为店堂大门,东、西两间为一排朝南的矮窗。店堂两间进深,中间一扇八折屏风,屏风下一张红木茶几,两边各置一张太师椅,四周字画点缀,布置得古朴雅致。店门上檐是一块楠木的匾额,上书:石梅居,店门两边是一副粉底金漆的对联:
残墨留古迹,点缀烟云米氏居;
妙笔焕新华,装潢书画麦家坊。
这块匾额为大清名士林则徐手迹。那还是道光元年七月,当时嘉兴府属石门县刚刚编纂好《石门县志》,便邀请浙江杭嘉湖道侯官林则徐为《石门县志》作序,之后到嘉兴游鸳鸯湖,又到紫阳街看字画。林则徐见这家字画店颇有几分气势,便欣然挥毫留下“石梅居”手笔。
“石梅居”的店主麦文石现年三十岁左右,生得斯文儒雅。麦文石虽是做字画生意的,但为人豪爽,没有丝毫生意人的习气,地方上的文人都喜欢和他交往,有些落魄文人拿些字画来寄售,他也很乐意帮忙。五年前,麦文石娶平湖名媛李氏为妻。此后,嘉兴人赞誉“石梅居”有两件宝,第一件宝是一幅古画,即北宋李成画的《读碑窠石图》。北宋前期,有三位声名卓著的水墨山水画家即李成、关仝和范宽,宋人尤其推崇李成,誉他为“古今第一”。这幅《读碑窠石图》为绢本立轴,画的是旷野中,窠石边,一位骑驴的老者立在一座古石碑前,仰头读碑,旁边候着一位童子。石碑旁边是几株脱尽了叶子的枯劲老树及疏落的荆棘短树,露出窠石一角。所谓窠石,其实就是凹凸不平多洞孔的石头,整个画面意境荒寒冷寂。石碑旁有八字题款:“王晓人物,李成树石。”也就是说读碑老者和侍立童子乃北宋名画家王晓所作,枯树石碑窠石才是李成所画,两位名家合作,可谓珠联璧合。画的右下角还有北宋末年徽宗赵佶的御阅印章,使这幅画愈显珍贵,这幅画是“石梅居”的镇店之宝。第二件宝是麦文石的妻子——李梅娘。李梅娘是李成后裔,到了李梅娘这辈,惟有独女李梅娘,她出嫁时李家就将这幅《读碑窠石图》作为陪嫁,一起到了麦家。李梅娘不仅有闭月羞花之貌,且知识渊博,精通文墨,特别是在字画鉴定上很有造诣。麦文石遇到疑难不能决断的字画,都是由夫人出面鉴别的。但没有想到的是,“石梅居”正是因了这两件绝世之宝,竟招来了一场大灾难。
平时,麦文石在店堂做生意,李梅娘则在后室整理装裱客人来寄售的字画。有人仰慕李梅娘的美貌,常拿一些字画来鉴定、寄售或装裱,明里是做字画生意,内心则是想借机一睹李梅娘的绝色芳容。但李梅娘严守妇道,深居后宅,从不跨出内院一步,有时麦文石遇到疑难,也是自个儿拿了字画进内宅让夫人鉴别,所以能有幸一睹李梅娘风姿者寥寥。
当时的嘉兴知府骆文彬系江苏常州人,道光初年的进士。骆知府婚后数年,夫人不曾生育,想不到过了不惑之年,夫人竟为他生下一子,骆知府中年得子,欢喜非常,为儿子取名骆德顺。骆德顺七岁那年,骆夫人一病不起,撒手西去。此后,骆知府对儿子更是宠爱有加,邀来饱学之士教他作诗绘画。骆德顺生来聪明伶俐,这么一调教,到十四五岁时,在地方上已颇有才名。光临“石梅居”的书生中,骆德顺也是其一,而且就数他去得最勤。经常往来,麦文石对他就有些熟不拘礼,有时还留他一起喝两杯。近来,骆德顺到“石梅居”去得更勤了。原来,骆德顺不但馋涎李梅娘的美色,还另有一桩心事。
半年前,有人介绍骆德顺和一位叫武田三郎的东洋人结识,武田三郎让骆德顺想办法去骗取“石梅居”的镇店之宝——《读碑窠石图》,他愿意出一万两银子向骆德顺购买。骆德顺不解,问武田三郎为什么不直接去找麦文石购之。武田三郎说,麦文石为人迂腐,死抱着这幅古画不放手,而他一个东洋人,在此人生地不熟的,所以只好求助知府公子了。于是骆德顺隔三岔五地到“石梅居”串门,今天抱一幅字,明天携一张画去鉴定,趁机露出想购买《读碑窠石图》的口风,麦文石则以此画为妻子娘家的祖传之宝为由,一口回绝。
这天,骆德顺拿了一幅明人陈道复的《松石图》,来请麦文石鉴别。麦文石点燃檀香,净罢手,在案上摊开《松石图》,仔细观看,一时不能确定其真伪。于是他一时大意,竟和骆德顺一起携画进了后宅内室,请夫人李梅娘鉴定。
李梅娘仔细看了《松石图》后,轻启樱唇:“这幅画恐是赝品!”
“娘子何以认定此画是赝品?”麦文石问道。
李梅娘伸出纤纤素手,指着《松石图》道:“此画面中间的青松挺拔,古藤盘旋其上,更显出苍松的沐雨经霜和皮老节劲,这些确是陈氏的画风。但官人请细看,那松树上多层次的松针泼墨似乎有些生硬,以陈氏的画风,这些松针应通过墨色的自在渗透,展现出叶色的深浅变化,绝不应该这般迟滞不化。”
这时,一旁的骆德顺插话道:“此画也许为陈道复年青时所作,故泼墨稍嫌不畅。”
李梅娘道:“后人临摹陈道复的画作极多,其中不乏高明之作,以致使人真假难辨。不过,这幅《松石图》定是赝品无疑,你看画面左上角所题‘嘉靖辛丑,中秋前三日道复写于城南草堂’,按嘉靖辛丑,即公元1541年,陈道复生于1483年,卒于1544年,那时陈氏已五十九岁,画艺已炉火纯青,用墨该更为飘逸洒脱!”
麦文石击掌道:“夫人一番话,使为夫茅塞顿开!”
旁边的骆德顺也暗暗称奇,心想:“这李梅娘果然名不虚传,确是才貌双全,如能得此女终生厮守,一生足矣!”于是一个计谋在心中产生。
骆德顺故意磨蹭到晚饭时分,麦文石便留他一起用晚餐,几杯花雕酒下肚,骆德顺又提出想欣赏那幅《读碑窠石图》。麦文石仗着七分酒意,从内室捧出一只雕花画匣,拿出那幅《读碑窠石图》,缓缓展于书桌上,与骆德顺一起玩赏。当晚,两人边饮酒边谈论字画书艺,直到谯楼更声响起,骆德顺才心怀鬼胎地起身离去。
当夜,四更刚过,一场大火忽然冲天而起。当时正值冬季,气候干燥,待紫阳街的居民们从睡梦中惊醒时,大火已经烧红了半边天,紫阳街陷入一片火海。睡梦中的李梅娘觉得热浪灼人,被烟雾呛醒,睁眼一看,见满屋里烟雾弥漫,她连忙爬起身,推醒麦文石,两人胡乱披上衣衫,急急逃出门外。忽然,麦文石大叫一声:“我们的画匣!”便又返身扑进了浓烟滚滚的房间。李梅娘急得大叫道:“麦郎,屋子要坍塌了!”但哪里还叫得住,急得她跺脚大哭。不一会,从烟雾中艰难地爬出一个人来,李梅娘忙上前扶起,只见麦文石紧紧抱着两只雕花画匣,其中一只已经被烧焦了小半只。麦文石将两只画匣交给妻子:“梅娘,我不行了,你一定要保存好《读碑窠石图》!”
抱着咽了气的麦文石,李梅娘失声痛哭。当她忍痛打开两只画匣时,只见那只烧焦了一小半的画匣里,只剩下小半幅烧焦了的画,从残画上推测,那就是李成的《读碑窠石图》,大部分已被烧毁,只剩下那几棵姿态不凡坚韧瘦削的老树;而另一只画匣里空空如也,画匣里的画失踪了。
李梅娘故意迎合
骆德顺趁机而入
紫阳街的这场大火,烧毁民房一百余间。因火起深夜,有居民三十三人来不及逃出被烧死,还有三家惨遭灭门之祸,阖家丧命于大火之中。
清晨,嘉兴知县马先木睡得正香,忽然被一阵“嘭嘭”的敲门声惊醒,当衙役向他禀报了紫阳街的火案后,他吓得脸色都变了,急急赶到知府衙门,请知府一同前去。嘉兴知府骆文彬知道这事非同小可,便和马先木带了捕头仵作等人赶到紫阳街。但见原来繁华热闹的一条商业大街成了一片废墟,满眼是残垣断壁,断梁焦木,几十具尸体横陈,号哭之声不绝于耳,其状惨不忍睹。经过仔细勘查,发现大火竟是从“石梅居”的厨房烧起来的,那么这场大火的责任人该是“石梅居”主人麦文石了。但麦文石自己也在这场大火中身亡,这件事也就不好追究了。
一场大火使许多人流离失所,李梅娘就是其一。李梅娘是独女,嫁给麦文石不久,其父母相继去世,李梅娘已无家可归。听说嘉兴知府骆文彬的老母年逾八十,最近这段时间忽感身体不适,而身边原来的使女被她娘家人赎回,缺个身边服侍的使女。李梅娘在紫阳街大火后曾经暗忖:“这场大火本来就烧得离奇,加上其中一只画匣中的那幅画被窃,想来是有人故意纵火。骆德顺几次向麦文石提出要买这幅《读碑窠石图》,麦文石都婉言拒绝了;而且失火的当晚,骆德顺和麦文石边饮酒边玩赏了这幅画,在‘石梅居’逗留到很晚才离去。这场大火也许和骆德顺有些关系。”李梅娘知道,要查明这场大火的起因,只有进骆府寻机接近骆德顺,或许能探明缘由。于是她便进骆府说明自己无家可归,情愿入骆府为骆老夫人当使女。骆老夫人见李梅娘容貌端庄秀丽,谈吐文雅,又知书识礼,自然非常喜欢,就留下了。
其实,紫阳街的这场大火,正是知府公子骆德顺所为。那天半夜,骆德顺离开“石梅居”后,直接去赌场找到一个酒肉朋友——绰号为“鼓上蚤”的盗贼。当夜,他俩一起潜入“石梅居”,趁麦文石酒醉,偷到了那幅《读碑窠石图》后,想到自己朝思暮想的美娇娘正和别人睡在一张床上,心中不由又妒又恨,便不顾“鼓上蚤”的劝阻,在厨房里放了一把火,因时值冬季,气候干燥,火借风势,大火马上冲天而起,殃及了整条紫阳街。骆德顺得画后,将画交给了武田三郎。武田三郎当即偷偷带回日本,经日本专家鉴定,这幅用三十三条人命换来的《读碑窠石图》立轴,竟是一幅后人临摹的赝品。武田三郎知道,那幅真迹一定在大火中被烧毁了。武田三郎不但没有得到真迹,还受到同行的嘲笑,他觉得有种被戏弄的感觉,便暗暗发誓,一定要置骆德顺于死地。
当骆德顺得知李梅娘当了祖母的使女时,乐得心里开了花。以前这美娇娘深居“石梅居”,难得一睹芳容,现如今就住在自家府中,岂不是可以朝夕相处!于是他便常借故去骆老夫人房中,明里是探望老夫人,实则是想趁机接近李梅娘。
李梅娘本是有因而来,见骆德顺如此频繁地穿梭往来于老夫人的房里,知道他的心思,便故意迎合,骆德顺趁机而入,时间不长,骆德顺就如愿以偿。
这天晚上,骆德顺外出赴宴回来,醉醺醺地摸进李梅娘的卧室西厢房。李梅娘见骆德顺已有十分醉意,一阵缠绵后,便趁机说道:“公子,我们这样偷偷摸摸地总不是长久之计,总得想个法子才行!”
骆德顺叹了一口气,道:“娘子,我前天曾向老夫人提起,想正式娶娘子为夫人,可老夫人她不肯答应,还把我数落了一顿,她要我用心读书,来年到省城应试。唉……”
原来,骆德顺已有此心,仗着祖母对他的宠爱,便提出娶李梅娘为妻。骆家只有这么一根独苗,而骆德顺年仅二十,李梅娘比骆德顺大了三岁。嘉兴有句俗语:“男大三,金门槛;女大三,恶水滩。”何况李梅娘的身份是个丫环使女,还是个死了丈夫的寡妇,所以骆老夫人坚决不同意,还狠狠教训了他,让他用心读书。
李梅娘幽幽地叹了口气,道:“既然如此,公子为什么还来找小女子,如今我的身子已经被你玷污,我不如跟着先夫去了!”
骆德顺忙一把抱住她,急道:“娘子千万别着急,虽然老夫人不让我娶你为妻,但我可以到外面买一幢房子,将你安置下,我拼了终身不娶,也要和你厮守。”
李梅娘抹了一把泪,道:“外面买房,你说得轻巧,哪有这么多的银子?”
骆德顺笑嘻嘻地从怀里掏出一叠银票,“唰唰”一甩:“娘子你看,凭这一万两银子,还买不到一幢房子么?”
李梅娘故作惊讶:“公子,你哪来这么多的银子?”
骆德顺醉意已浓,哪还有防备之心,笑道:“说起来,这一万两银子,还是娘子你赐于我的呢!”便将如何受武田三郎之托,伙同“鼓上蚤”潜入“石梅居”窃画纵火的经过讲了一遍。李梅娘听了气得浑身发抖,好在骆德顺已喝得酩酊大醉,不曾察觉。
李梅娘强忍怒火,故意试探道:“公子真会编故事,谁会有这么好的身手,放了火再拿了画去?”
“娘子怎么不信?我可出了八百两银子,雇的是有名的‘鼓上蚤’。此人轻功极好,飞檐走壁,登堂入室,不在话下。那天,他带我进入‘石梅居’,取走《读碑窠石图》,轻而易举啊!”骆德顺哈哈笑了几声,搂着李梅娘呼呼睡去。
李梅娘望着睡得像死猪般的骆德顺,恨不得一刀捅他个透心凉,为丈夫和被烧死的三十三条人命报仇。转念一想,若这样杀了骆德顺,这紫阳街的火案真相如何公诸于众?一定要让嘉兴府的百姓都知道骆德顺这个狼心狗肺的纵火恶贼,将他绳之以法。李梅娘翻来覆去想了一夜,想出一条计来。
只见李梅娘高叫一声后,一头朝廊柱撞去
农历六月二十八,是传统的“观莲节”。这日,嘉兴的城乡百姓都聚在莲花盛开的鸳鸯湖畔观赏莲花。鸳鸯湖位于嘉兴城南,又称南湖。湖心有一岛屿,上面建有一座五楹二层重檐的建筑,其雕梁画栋、朱柱明窗,与碧水绿树竞相辉映,那就是浙北有名的烟雨楼。
相传,五代时广陵王钱元僚任中吴节度使时,曾在鸳鸯湖滨筑宾舍以为“登眺之所”,因其“轻烟拂渚、微风欲来”的迷人景色,成为江南一大名胜。清高宗乾隆六次下江南,八次畅游鸳鸯湖,并驻跸烟雨楼,并在此楼大宴地方官吏。乾隆皇帝将烟雨楼比作蓬莱岛,把鸳鸯湖比作杭州西湖,觉得美景天成,畅快之余写下十四首诗词,刻在烟雨楼前的石碑上,因此这鸳鸯湖的烟雨楼被历任官吏视为圣地。每年“观莲节”,不但嘉兴知府、知县要亲临“观莲节”,而且省府的官员也必定会来,以瞻仰“圣地”,与民同乐。
这天是个阴天,上午辰时,从清晖堂出来一群人。只见这群人都身着朝服,胸悬念珠。为首三人,左右两位分别是嘉兴知府骆文彬和知县马先木,当中那位身着蟒袍,三绺长须掩胸、气宇轩昂的官员正是浙江巡抚乌伦托布。一行人步出清晖堂,踏上万福桥,眺望湖面,但见湖面渺茫,细雨濛濛,碧水、绿柳、画舫相映成趣,乌伦托布不由捋须长笑:“景色如画啊!难怪当年太祖、太宗二帝要不惜刀兵,来夺南朝江山,这儿确是一片花花世界呢!”
随后,乌伦托布情不自禁地脱口吟道:“千里莺啼绿映红,山村水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之的诗,写的就是眼前的景色呢!”
骆文彬见乌伦托布兴致极高,也笑道:“抚台大人不愧为北疆才子,文武全才呀!”
乌伦托布道:“哎,想我们大清能一统中原,对汉人文化当然也了解了。想当年,我们八旗子弟金戈铁马,靠的是以武力开创国家。现如今,我们要以文治国,要的可是民心!”
“抚台大人说得是!”
一行人簇拥着乌伦托布,来到钓鳌矶。乌伦托布望着“钓鳌矶”三字石刻,笑问:“名为‘钓鳌矶’,是不是指望嘉兴能多出人才,独占鳌头?”
骆文彬道:“那是前朝嘉兴知府龚勉所题,其意确如抚台大人所说,但仅是希望而已。”
乌伦托布道:“不然,据本官所知,龚勉题字立碑的第二年,即大明万历十一年,嘉兴人朱国祚就中了状元。从此,这‘钓鳌矶’的名气大振,许多文人学士都争相前来顶礼膜拜呢!”
想不到这个满族旗人对嘉兴的人文历史竟这么清楚,骆文彬和马先木不由得暗暗佩服。
忽然,一个女子的声音传来:“各位大人在上,紫阳街三十三条人命冤枉哪——”
众人吃了一惊,骆文彬望了望马先木,不悦地问道:“马大人,这是怎么回事?”
马先木忙走上几步,喝问道:“何人在此喧哗!”
只见一个女子急步抢上前来,几个衙役上前阻拦,没能拦住。那女子朝乌伦托布等人跪下,悲道:“小女子为紫阳街大火烧死的三十三条人命鸣冤!”
骆文彬这才看清,这鸣冤女子竟是自己母亲的使女李梅娘,不由大怒:“你这刁妇,不在家侍候老夫人,为何跑到鸳鸯湖来撒野!”
李梅娘大叫道:“各位大人,紫阳街大火,其实是有贼人纵火!”
马先木喝道:“抚台大人在此,不许胡闹,待会到县衙公堂上,本县自会审理!”
李梅娘道:“因这纵火贼徒非同常人,小女子定要面告抚台大人!”
乌伦托布一抬手,道:“好了,且让她向本官申诉!”
“那紫阳街的纵火恶贼,正是知府骆大人的公子骆德顺!”李梅娘道。
骆文彬大吃一惊,喝道:“你这贱妇刁女,竟敢在抚台大人面前胡言乱语!”
“小女子不敢胡言乱语,正是骆德顺花了八百两银子,雇了惯贼‘鼓上蚤’,他们一起潜入‘石梅居’,窃画纵火,使得紫阳街一百余户居民的住宅化为灰烬,三十三条人命无处申冤!”
骆文彬道:“骆德顺出银子雇人偷画后,再纵火焚烧紫阳街,平白无故,没有丝毫道理!”
“贼徒骆德顺的目的是为了谋夺《读碑窠石图》,然后再霸占小女子!”李梅娘悲泣道。
骆文彬还要再说什么,乌伦托布又一挥手,吼道:“好了,此案关系到三十三条人命,先将这女子带到县衙,本官要亲自审理!”
来到县衙,乌伦托布坐了正堂,左右分别坐了知府骆文彬和知县马先木。衙役将李梅娘带上大堂,乌伦托布问道:“堂下原告,姓什么,叫什么,所告何人?”
李梅娘道:“抚台大人,小女子姓李,是紫阳街‘石梅居’麦文石的妻子,告的是嘉兴知府骆文彬的儿子骆德顺!”
乌伦托布道:“按大清律法,平民越级告状,要先打五十股杖;平民状告朝廷命官,也是五十股杖。你若要告状,先要行刑一百股杖!”
李梅娘从容道:“抚台大人,小女子为丈夫麦文石和紫阳街三十三个冤魂申冤,死都不怕,何惧一百刑杖!不过,小女子有一个请求!”
乌伦托布道:“道来!”
“抚台大人,以小女懦弱之躯,经这一百刑杖后,必死无疑……”
骆文彬冷笑道:“这么说来,你是不想告状了?”
“不!”李梅娘柳眉一竖,“状一定要告,一百刑杖也准备受,只是小女子受了一百刑杖以后,必已毙命,如何还能将案情讲清!所以小女子请求,先让小女子把案情陈述清楚,然后再动刑可否?”
骆文彬“嘿嘿”几声冷笑:“大清还没有这律法!”
“哎!”乌伦托布手一挥,“事出有因,今天本官就破个例,让你先把案情讲述清楚!”
李梅娘朝乌伦托布磕了一个头:“多谢大老爷!”于是便把骆德顺拿一幅陈道复的赝品来“石梅居”鉴定,当晚喝酒,半夜起火,及她怀疑骆德顺有纵火窃画的嫌疑,卖身到骆府做侍女,舍身事贼,趁骆德顺酒醉套出真相等经过一一述之。
“抚台大人只要抓了窃贼‘鼓上蚤’,就能证明小女子所言句句是实!”
乌伦托布听了李梅娘的诉说,当即令嘉兴知县马先木派人追捕“鼓上蚤”。这时李梅娘又朝乌伦托布磕了一个头,道:“抚台大人,小女子的冤屈已经向大人申诉,但受这一百刑杖,小女子也必死无疑。何况我已失身事贼,受贼徒玷污,再无脸面苟活世上,这苦就不受了!”未待堂上人反应过来,只见李梅娘牙一咬,高叫一声:“麦郎,为妻来了!”一头朝廊柱撞去,只听得“噗”地一声,当即头破血流,倒在地上,香消玉殒。
乌伦托布想不到这女子竟这般贞烈,感叹之余,当即下令,将骆德顺拘拿到堂。骆文彬忙起身道:“抚台大人,一个疯女人的话,如何能当得真?”
乌伦托布拍案而起:“一个弱小女子,为了申张正义,为夫报仇,竟然连贞操、性命都不要了,还能有假?”
不一会,骆德顺被带到大堂,乌伦托布正要亲自审讯,忽然省城飞马来报,说有要事请巡抚大人速回省城处理。乌伦托布只得命马先木将骆德顺暂且押入大牢,急急回省城去了。
骆文彬回到府衙,不由得又气又急,他知道烧死的三十三条人命实为旷世巨案,一旦查实确系骆德顺所为,按大清刑律,就是凌迟处死也不为过。骆德顺可是骆家唯一的独根,骆文彬正急得团团转,忽报知县马先木来访,骆文彬忙把马先木迎进后堂。仆人端上茶来,骆文彬挥手让其他人都下去,然后朝马先木一揖到底,马先木慌忙起身道:“骆大人,这是为何?”
骆文彬道:“马大人是本县父母,务必请设法救小儿一命!何况本府上有八旬老母,一旦得知唯一的孙儿出事,她老人家如何还活得?”
马先木原是嘉兴府的刑事师爷,举人出身,一向以足智多谋著称,深得历任知府器重。两年前,嘉兴知县离任缺职,知府骆文彬便举荐他出任了知县一职。马先木将眼睛眨了眨,轻声说道:“大人勿急,如今李梅娘已死,唯一知情的活口,就是那个‘鼓上蚤’了,如今之计,只有让‘鼓上蚤’闭嘴了,只要公子自己不承认,也就死无对证!”
见骆文彬点头,马先木又道:“下官奉抚台大人之命,追捕‘鼓上蚤’,可以让追捕的衙役寻个机会杀了他,到时只要说那‘鼓上蚤’拒捕被杀,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瞒过去!”
骆文彬听了,喜笑颜开。马先木却道:“大人且慢高兴,那抚台大人这一关可不好过。大人你也知道,这抚台大人对下属一向严厉,恐怕他还会追根问底,一直追查下去的。”
骆文彬皱眉道:“这乌伦托布不贪财、不好色,可怎么摆平他?”
马先木嘻嘻一笑,又道:“大人放心,再硬的金刚也有软肋,抚台大人的夫人可是出了名的母老虎,抚台大人天不怕,地不怕,怕的就是他的夫人。下官新娶的内子,以前曾给抚台夫人当过使女。去年秋天,抚台夫人曾向下官打听过,她知道大人逝去的夫人遗有一件翡翠梳妆盒,乃是前朝宫中之物,大人只要疏通了抚台夫人,还愁此事办不成?”
骆文彬道:“为了骆家的一线血脉,我将翡翠梳妆盒拿出来孝敬抚台夫人就是了!”
“还有,抚台大人喜欢抽两口,大人你也得打点一下。”
骆文彬不由笑道:”这么说来,抚台大人的软肋还真不少呢。”
明朝末年就有鸦片流入中国,大清入关建国后,虽然也曾多次禁止,但成效不大。到嘉庆初年,朝中大臣已嗜烟成瘾,一些中高层官员都以抽鸦片为时髦,于是便有投机者专门购买上等的鸦片,用以贿赂上司。
骆文彬几经辗转买到了一些上等鸦片。几天后,和马先木来到杭州,分别求见乌伦托布及其夫人。
果然,乌伦托布收下礼物,又碍于夫人的情面,便顺水推舟,答应道:“唉,骆公子是骆大人的独子,本官也知道骆大人的苦衷,且那李梅娘也是一面之辞。如今原告已死,若没有苦主上告,本官也就不再追究了。”
骆文彬连忙拜谢:“多谢抚台大人再造之恩,至于紫阳街一干苦主,下官一定打点好,不会让他们再滋生事端了。”
骆文彬和马先木回到嘉兴后,两人一番密谋,便调遣人手,追杀“鼓上蚤”。
骆文彬瘫坐在马先木的县衙大堂上,双目发直
这日,乌伦托布处理完公务,抽了几口鸦片,打起精神,便在庭院里舞剑,忽听外面一阵喧哗,有衙役进来禀报道:“大人,京城刑部的董大人携圣旨已到门外。”
乌伦托布吃了一惊,正想仔细询问,只听得门外有人高喊:“圣旨到——浙江巡抚乌伦托布接旨!”
乌伦托布连忙换上官服,置香案迎接圣旨。
原来,前几天宫中侍卫在御花园拾到一封奇怪的信,意思是揭发嘉兴知府骆文彬的儿子骆德顺偷盗国宝《读碑窠石图》卖给日本人,并在紫阳街纵火烧毁民房一百余间,烧死居民三十三人……
皇上看了信,虽不知是真是假,但龙颜大怒,想自己登基以来,从来没有出过这么大的人为灾难。皇上当即拟下一道圣旨,派刑部尚书董卿为钦差,赴杭州会同浙江巡抚乌伦托布迅速查明此案,从严惩处。
乌伦托布接到圣旨后,哪里还敢怠慢,马上带领随从和董卿一起乘官船沿古运河直抵嘉兴。来到嘉兴县衙,骆文彬和马先木前来迎接,尚书董卿和乌伦托布亮出圣旨,说明来意,问是否已将“鼓上蚤”捉拿归案。
马先木战战兢兢地答道:“回禀两位大人,下官派出人手,四处捉拿,但那‘鼓上蚤’却不见人影。”
对于紫阳街纵火一事,马先木推说原告已触柱身亡,“鼓上蚤”又不曾擒获,而被告骆德顺也矢口否认雇人窃画纵火之事,所以一时难于查明定案。
董卿和乌伦托布正无奈间,忽有随从来报,说门外有个自称“鼓上蚤”的人,前来向钦差大人和巡抚大人投案自首。董卿和乌伦托布又惊又喜,忙传令将“鼓上蚤”带上堂来。
这“鼓上蚤”怎么会来向董卿和乌伦托布自首呢?原来,“鼓上蚤”想不到骆文彬和马先木他们会杀人灭口,只得四处躲藏。这天得知当今皇帝委派刑部尚书董卿为钦差,和浙江巡抚乌伦托布共同追查紫阳街纵火命案,也明白自己受人雇请入室偷盗,按大清律法,最多只能判个充军边疆;若是躲不过骆文彬和马先木的追杀,便是死路一条。思忖再三,他索性把心一横,直闯嘉兴县衙,投案自首。
董卿问明事由,不由大怒,便下令将“鼓上蚤”打入大牢,又把骆德顺提出大牢,和乌伦托布一起审讯。那骆德顺得知“鼓上蚤”已经自首,故已难抵赖,只得一一供认不讳。当董卿问起那幅《读碑窠石图》的事,骆德顺大叫冤枉,说“鼓上蚤”帮他盗出的那幅《读碑窠石图》只是一幅赝品。骆德顺也精于书画鉴定,当“鼓上蚤”将那幅画交给他时,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一幅赝品,这才明白麦文石和李梅娘已临摹了一幅《读碑窠石图》,想那场大火也一定将那幅真迹焚于火海了。便欺武田三郎不识中国字画,冒充真迹,换了一万两银子。谁知正是这幅赝品,使武田三郎恼羞成怒,必要置骆德顺于死地。武田三郎返回中国后,就写了一封信,揭发骆德顺纵火焚烧紫阳街,烧死三十三条人命之事。并买通皇宫中人,将信携入皇宫,掷在御花园里,让皇宫侍卫拾去,终于使皇帝传旨追查此案。
董卿和乌伦托布问清真相,乌伦托布气冲冲地对骆文彬道:“骆大人,此案已惊动了万岁爷,本官和董大人也无法为你遮掩了,如何处置贵公子,就交给骆大人自己了!”
董卿和乌伦托布走后,骆文彬好像被剔除了骨头架子,浑身发软,再也没有力气回府衙了。他瘫坐在马先木的县衙大堂上,双目发直,讷讷自言:“怎么办,怎么办?这可是骆家惟一的血脉呀!”
马先木见骆文彬痴痴呆呆的模样,跨上一步,道:“骆大人,快想办法吧!”
骆文彬一双眼睛瞪得血红,他一把揪住马先木,吼道:“你说,该怎么办,怎么办?”
“骆大人,刚才抚台大人说,让你处理这一案子,大人,你决断吧!”
骆文彬涕流满面:“乌伦托布是要我亲自判亲生儿子的死罪呀!我骆某人情愿不要这五品顶戴,也要留下骆家这条根!”
马先木道:“骆大人难道弃了这头上的顶戴,就能保住公子的性命了么?”见骆文彬沉默无语,又道,“骆大人知道,紫阳街那三十三条人命,已经惊动了当今圣上。骆大人就是弃了头上这五品乌纱,公子也难逃一死,到时骆大人还会背上一个教子无方、纵子犯法的恶名!”
骆文彬忽然仰天狂笑:“骆家,我堂堂骆家,到我这一辈,竟然断子绝孙了!苍天哪,列祖列宗哪,你们惩罚我这个不肖之孙吧,竟不能为骆家留下一条血脉!”
马先木眼睛骨碌碌一转,道:“骆大人,下官有一计,虽然不能保住公子的性命,但能为骆家留下一条血脉,以续骆家香火。”
骆文彬一听,忙朝马先木一揖到底:“马大人,本府就拜托你了。只要能为我骆家留下一线血脉,本府就是死了,也无一丝的遗憾!”
马先木笑道:“其实这事并不难,骆大人也不必言谢,就算是下官报答大人的举荐之恩吧!抚台大人不是让骆大人亲自处置这桩案子吗,那么,骆大人尽可秉公执法,赚个大义灭亲的美名,判公子一个斩刑……”
骆文彬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嘶声叫道:“你胡说,斩了骆德顺,本府如何还有血脉延伸?”
马先木“嘿嘿”一笑道:“骆大人稍安勿躁,听下官把话说明白。骆大人将公子判了斩刑,必要呈文刑部,由刑部批复后,方可行刑,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让骆家留下一个血脉!”
骆文彬急道:“马大人,快说。”
“骆大人还记得那个‘鼓上蚤’吧,那个帮公子窃画又来自首的盗贼,按照大清刑律,下官判他发配黑龙江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到时你我只要将两件公文调换一下,把呈京城刑部的公文随‘鼓上蚤’送到黑龙江,呈黑龙江的公文则呈到京城刑部,不就——”
骆文彬猛然省悟:“马大人的意思是——”
马先木笑道:“到时,刑部接到的是送黑龙江的呈文,知道送错了,便要原文退回来,这一送一退,少说也要三四个月;而随‘鼓上蚤’送到黑龙江的呈文也是一样,而且黑龙江的路途更为遥远,几千里迢迢路程,到了那里,发觉装错了公文,再退回嘉兴,这一送一退,没有半年是回不了嘉兴的。那时再将黑龙江退回的呈文送到京城刑部,岂不是又要一去一回!如果那呈文路上有所耽搁,那就是十个月,或者一年,也说不准了。这段时间,公子呆在狱中,骆大人尽可挑选一个年轻女子,送入狱中服侍公子,待刑部批文下到嘉兴时,公子或许还能见到自己的儿子呢!”
骆文彬思虑再三,认为眼下也就这么一个办法了,便和马先木一起升堂,带上骆德顺,亲自复审。这骆德顺见是父亲亲自复审,还以为尚有活路,便把作案经过又重述了一遍,骆文彬让他在供状上画了押,便又送回大牢。又让狱卒专门整理了一间干净宽敞的牢房,置办了些生活用品,让骆德顺住,一日三餐,也由骆府派专人送入狱中。因狱中狱卒人等都知道这位犯人是知府大人的公子,虽犯了死罪,但还是尽量关照他,所以这骆德顺虽说是坐牢,其实和住馆驿一样。
钦差尚书董卿和乌伦托布几次过问此案,骆文彬和马先木便如实回禀,说已将骆德顺判了死罪,并将送刑部批复的有关文案让董卿和乌伦托布验看过目。
骆文彬一切安排妥当,却为找一个服侍儿子的女子犯了难。原来,紫阳街纵火案早已传遍了江浙,老幼皆知,杭嘉湖一带更是家喻户晓。如今这杀人凶手判了斩刑,囚于狱中,哪个女子愿意进牢狱服侍他呢?而这名女子名义上是服侍起居的丫环,实则是为骆家传宗接代的儿媳妇,一般粗陋的女子骆家还看不上,万般无奈,最后到安徽宣州买来一个刚被卖入妓院的姑娘,送入狱中。十个月后,几经辗转的刑部批文下来,骆德顺被处斩刑。行刑那天,嘉兴城里万人空巷,男女老少都赶到刑场观看。有人痛骂骆德顺丧尽天良、灭绝人性;也有人赞誉骆文彬大义灭亲,处斩独子。
不久,那位宣州的姑娘果然为骆家生下一个男孩,续了骆家的香火。
至于李梅娘自杀前那半幅李成的真迹《读碑窠石图》,已下落不明……
〔本刊责任编辑 君 早〕
〔原载《中国故事》总第2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