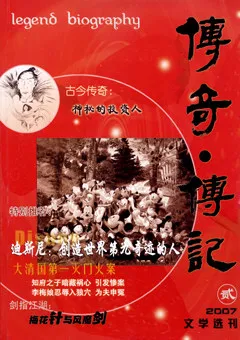金庸与夏梦的未了情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的名门望族,家学渊源,祖上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荣耀。他在大学主修英文和国际法,毕生从事新闻工作。曾在上海大公报、香港大公报及新晚报任记者、翻译、编辑,1959年创办香港《明报》,任主编兼社长历三十五年,其间创办《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新加坡《新明日报》及马来西亚《新明日报》等。
他自幼酷爱读书,并且笔耕不辍,是一名成功的报人,也是社会评论家和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他1955年在《新晚报》发表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9月《鹿鼎记》连载完结,二十年间先后完成“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四部小说,成为武侠小说的典范。
金庸武侠小说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难解之谜。他是香港文化界的擎旗人,被誉为“文坛侠圣”。
然而,文坛上辉煌得意的金庸,在情场上却曾是悲苦失意的,纵是侠圣才子也难圆爱情的美梦。他嗟叹:“即使‘流水有情’也毕竟东流去……”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侠圣”的仲夏夜之梦
1957年,金庸加盟新组建的以大明星夏梦为当家花旦的香港“长城电影制片公司”。金庸是个名满香江的大才子,为什么要加盟长城影片公司,屈就去当个编剧呢?原来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完全是为了接近夏梦而去的。据他的一位挚友说:他爱夏梦如痴如醉。年轻的金庸,每当人们提起夏梦的名字,他的脑海里总会出现一幅画面:仲夏月夜,一轮如水晶如温玉一样皎洁的圆月,挂在天鹅绒般湛蓝色的夜幕上,空气中可以闻得到淡淡的、带一点甜味的桂花香。那是他的仲夏夜之梦,这个梦总是和一个名叫“夏梦”的香港女明星纠缠在一起。在他眼里,夏梦就是那样一个像梦一样轻盈、缥缈,像夏夜的月亮一样高洁、脱俗,令人可望不可即的女子。那个有着一双像黑珍珠一样清澈明亮的大眼睛,有着像仙女一样的美丽容貌的佳人芳名,镂刻在他的心里,折磨得他寝食难安。苦于在生活中难以见到夏梦,金庸不得已才想到了“加盟”这个绝招。金庸还开玩笑说:“当年唐伯虎爱上了一个豪门的丫环秋香,为了接近她,不惜卖身为奴入豪门,我金庸与之相比还差得远呢!”
金庸到了长城影片公司之后,取了个艺名叫做“林欢”。为博得夏梦的欢心,他在工作上极其卖力。短短三年就先后创作了《绝代佳人》、《兰花花》、《不要离开我》、《三恋》、《小鸽子姑娘》、《午夜琴声》等电影剧本,可谓是多产编剧了。后来他又学习导演,他既有才气又肯下工夫,于是不久便与人合作导演了影片《有女怀春》、《王老虎抢亲》等影片。他在工作上的出色成绩,得到了夏梦的称赞。
“盈盈一水间
脉脉不得语”
当时三十三岁的金庸,由于能够长期与二十四岁的夏梦在一起工作,时时都能与之见面或交谈,佳人的一颦一笑都使他狂喜,深陷情网的他神魂颠倒,痴迷日增而忘乎所以。
夏梦是长城影片公司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与石慧、陈思思合称“长城三公主”,夏梦居长,号称“长城大公主”。她外形艳而不媚,贞静平和,娴雅大方,兼之一米七○的高挑身材,有“上帝的杰作”之美誉,是有口皆碑、大名鼎鼎的“梦美人”,在香港演艺圈里有“西施”之称。
夏梦原名杨蒙,祖藉苏州,少女时期生活在上海。她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族教育。1947年,她随家人来到香港,进入圣玛利诺英文书院读书。1949年,学校举行文艺联欢会,由学生用英语演出《圣女贞德》,夏梦主演贞德,获得了极大成功。人们夸她“人极漂亮,戏又演得精彩”。她喜唱京剧,是一名出色的花旦。因容貌清丽,体态线条优美,艳光熠熠照人,她十七岁就进入长城影片公司当了演员。由于文化素质高,人聪颖灵慧,扮相又极俏丽,所以在银幕上极有光彩。她现代戏、古装戏、戏曲、电影皆能胜任,反串男装更是俊逸潇洒,风采不凡,气质神韵独步影坛,是国语片子罕见的全能演员,不愧为第一流的明星。
正因如此,才使金庸爱慕不已,倾心拜倒。金庸完全被她迷住了。他曾说:“生活中的夏梦真美,其艳光照得我为之目眩;银幕上的夏梦更美,明星的风采观之就使我心跳加快,魂儿为之勾去。”
但使金庸极其苦恼的是:他对夏梦的爱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虽满腔痴情,苦苦相恋,却难于实现自己的愿望,其根本原因在于夏梦早已名花有主。早在三年前她二十一岁时,就与林葆诚先生结过婚了。林葆诚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虽是从商,却对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是个电影迷,特别爱看夏梦主演的影片。一天,他跟朋友去长城影片公司看夏梦拍《姊妹曲》,恰巧该片缺一个扮演教师的演员,他就毛遂自荐客串演出,从此与夏梦相识相爱,两人于1954年结婚。由此可想而知,金庸感到爱上一位少妇,心理上是有障碍的。更重要的是夏梦忠于夫君,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许多爱慕追求者,都一律冷若冰霜加以拒绝。
但金庸此时对夏梦已是极难“慧剑断情丝”了。他已深陷情网,爱得如醉如痴,不能自拔。出于自尊和人品的考虑,金庸不能对夏梦采取纠缠的态度,也不能显山露水地去表示什么,而只能限于“临去秋波那一转”,眼角眉梢间的脉脉传情。有时候,他实在憋不住了,或委婉含蓄地暗示几句,或旁敲侧击地说上一番。夏梦机灵敏感,对金庸的隐情曲衷,心里自然明白。说实话,金庸风采俊逸,人品高尚,才华过人,她也非常欣赏他、喜欢他,但“罗敷有夫”,不可能再接受他的爱。可又不能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因为实在不忍心伤害他。于是她就采取一种非常友好的态度对待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比爱情少,比友谊多”的介乎两者之间极其微妙的状态。偶尔夏梦也对他眉目传情,或嫣然一笑,或言语温存,这已经给了金庸很大的慰藉。金庸也明白,他们不能像其他情人那样,有更亲昵的举动,譬如拥抱接吻之类。但仅仅是一个眼神,已让他感到无比的甜蜜。夏梦无法回避两人的经常接触,因为他们在电影事业上还需要很好地合作,不能因为感情上的问题让电影事业受到影响。例如她主演的《绝代佳人》、《午夜琴声》等影片均是金庸编剧,对于剧中人物的理解与把握,她需要请教他。而她主演的越剧影片《王老虎抢亲》又是金庸执导,更需要他与她说戏,表演时作这样那样的具体指导。也就是说,她的电影表演事业处处离不开金庸。他们之间,无论如何不能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否则编剧与演员、导演与演员之间和谐欢快的气氛就会消失,会给拍摄工作带来损失。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夏梦是很用心对待金庸的,她温柔而又不失分寸,既让金庸感到慰藉又不让他有非分之想,保持了纯洁而又良好的关系。
“还君明珠双泪垂”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金庸与夏梦最难忘的一幕,也许是一个夜晚在咖啡店的幽会。
这是他们仅有的一次幽会,是金庸主动,而夏梦也例外地答应了。
在咖啡店幽幽的烛光和柔柔的音乐中,两人四目相对,呢喃而语,不时频频举杯,那种诗意的氛围及浪漫的情调,实在令人陶醉销魂。面对这个像梦一样轻盈、缥缈,像仲夏的月亮一样高洁、脱俗的绝代佳人,看着她那双像黑珍珠一样美丽的大眼睛,金庸再也抑制不住激情,趁着几分酒意,终于倾吐了自己深藏多年的爱慕之情。夏梦听了极为感动,她含泪对金庸说,她非常敬重他的人品、欣赏他的才华,只可惜他的“爱”迟到了一步,只能感叹“恨不相逢未嫁时”了,并说以她的为人,是绝不愿去伤害夫君的,请求他能格外原谅她。最后她深情地说:“今生今世难偿此愿,也许来生来世还有机会……”这次幽会就这样伤感而无奈地结束了。
从此之后,金庸只好幽闭心曲,把夏梦当作苦心依恋的“梦中情人”,只在心里默默地爱恋着她。
重冈已隔红尘断
1959年,金庸带着情感的失意和无奈离开了长城影片公司,去创办他的《明报》,并致力于写作他的武侠小说了。
就在金庸创办《明报》不久,夏梦曾有一次长时间的国外旅游。他就在《明报》上系列报道夏梦的游踪行迹,而且还开辟了一个专栏——《夏梦游记》,一连十多天登载夏梦写的旅游散文和小说。假如不是依然深深地眷恋着夏梦,他又何苦如此?
金庸对夏梦的“藕断丝连”还表现在他创作的武侠小说中,他在那里深深寄托着对夏梦的爱。
细心的读者都不难看出,这个当年差一点没把金大侠的“魂儿为之勾去”的“梦美人”,虽然息影多年,但在大侠的武侠世界里,处处都可以觅到她的倩影:《神雕侠侣》中冰清玉洁的小龙女、《射雕英雄传》里冰雪聪明的黄蓉、《天龙八部》中貌若天仙的神仙姐姐王语嫣……
痴情的金大侠早已把他对梦中情人的相思之情融进了他的作品里,使夏梦的艺术生命在另一个领域里得以延续。
台湾已故女作家三毛说过:“金庸小说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写出了一个人类至今仍捉摸不透的、既可让人上天堂又可让人下地狱的‘情’字。而不了解金庸与夏梦的这一段情,就不会读懂他在小说中‘情缘’的描写。”
1976年,夏梦告别了二十六年的银幕生涯。二十六年中,她共拍了四十二部影片。她那美丽的倩影,永远定格在影片中。她告别了香港,告别了热爱她的影迷们,移民去了加拿大。这自然又在金庸的心湖掀起一阵波澜。
在梦中情人远去异国之际,金庸情心依依,破例把这一件本是很平常的事,一连几天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位置上,用了很大篇幅作了详细报道。
不仅如此,金庸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社论——《夏梦的审梦》,向夏梦这个“真善美女人”祝福。《明报》专为一个女明星的移民国外而大做文章,实在是一件异常的事,不明白其中内幕的人会感到惊讶,只有懂得内情的人,才能理解作为《明报》主编的金庸先生对夏梦的那份不同寻常的痴心爱恋。
佳人远别,金庸苦恋多年,终未修成正果,但毕竟给他留下了一个终生怀念的梦。
〔本刊责任编辑 冯 因〕
〔原载《名人传记》总第27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