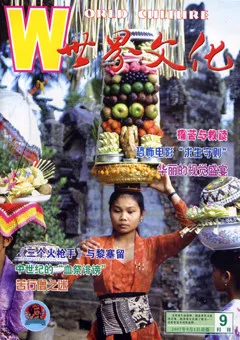文天祥后代的爱国情结
在吉隆坡工作期间,我从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黄汉良会长等侨领口中,偶然闻悉文天祥的后代就定居于吉隆坡,极为惊喜,遂特意专程去寻访。他们的代表人物是文平强博士,现任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主任。文平强原为马来亚大学地理系教授与系主任,旋后在东亚研究系担任同样的职位。文先生曾经在英国HULL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哈佛燕京研究所、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及东京的亚洲经济研究所担任访问研究员,出任过文莱大学与东京创价大学客卿教授。此外,他还在爱丁堡大学、澳洲Griffith大学、韩国kyungnam大学做过短期的访问与研究工作。
据说,在马来西亚具有教授、副教授职称的华裔人士只有几十位,是备受尊敬的。因此,文平强先生得知我是中国的一名大学教授,是前来参加中马文化交流活动的,即非常热诚地邀约我会晤。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简称华研)设立在吉隆坡市中心的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内。那是一座美丽而典雅的建筑物,楼上的几大间整洁的套房就是华研的办公室。一位年轻的华人女士引领我穿过两间书架林立的编辑室和资料室,来到最里面的一间整洁的主任办公室。文平强先生显然已恭候多时,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他即刻热情地迎接,一见如故地与我亲切握手、寒暄。
文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极其鲜明而美好的。大约1米8的颀长身材,瘦削而健朗的体型,淡红色的长袖衬衫,被皮带紧束在黑色的西装裤腰内,除了一支银色的钢笔套插在上衣的口袋外,全身别无他物,显得非常简朴而精干。再打量文先生的似曾相识的清秀面容,更让人感受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有的那种端庄儒雅的风度:灰白的短发,饱满的额头,闪光的镜片后面,一对慈和而睿智的眼睛炯炯有神。“您好!吴教授,很高兴能见到您。”一口流利的带有南洋华侨口音的普通话,似乎与他的学者身份非常吻合,使我联想到他在大学讲台上授课的音容笑貌。也许由于彼此有不少灵犀相通之处,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和语言,我们在深绿色的皮沙发上一坐下来,只需一杯清茶,就滔滔不绝地聊个没完。
我们的话题真是海阔天空,包罗古今中外。从郑和与马来西亚的关系,谈到华人在“大马”的历史地位和现实状况。从古老的华夏文化在东南亚的流播和影响,谈到华研的创办经过、工作方向与成绩表现。特别对后者,文先生是津津乐道、如数家珍,我也听得津津有味、兴趣盎然。
原来,华研创办于1985年9月15日,乃是一个关注和适应大马华社文化、教育、经济诸方面需求的全国性学术研究中心,又是一个正式注册的非营利公司组织。华研的创办象征着大马华社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其宗旨多元而广泛、涵盖面极广,但重点集中在三大领域:一是研究探讨大马华人在文化、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课题,以及华社与其他社群乃至海外华人的关系。二是出版学术刊物,传播理论观点,举办研讨jLxqy/17qYHj81fV+L/hkQ==会,联系国内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制订研究合作计划,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三是作为马来西亚华社研究资料和文献整理中心,为各有关单位和群体提供服务、咨询和帮助。多年来,华社已出版一千多种图书。为强调和提升学术研究,华研相继出版了许多刊物,如自1997年始出版了《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1999年起又有学术丛书系列问世,2000年出版《人文杂志》双月刊,2003年推出《华研研究论文系列》等。到目前为止,华研共出版了63种刊物,其中54种为中文,8种为英文,1种为马来文。此外,华社经常举办学术研讨活动。文平强先生给我看了一份近几年来的研讨会名录,其主题都是相当重大而引人瞩目的,如“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人口与华人社会学术研讨会”、“新世纪文学文化研究的新动向研讨会”、“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百年: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马中关系:新世界秩序中的定位国际学术研讨会”、“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此外,华研还不时举办“新书推介礼”,向广大读者推荐华文出版物,我从文平强先生手中接过来的一张清单上见到了一系列书目,如《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中国文学新走向》、《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马来西亚华人人口:趋势与议题》、《马来人名中译手册》、《清流甘泉:与世界智者晤谈》、《难忘的世界之友》……不胜枚举。顾以上会名、书名而思其义,可见马来西亚华人学者的视野是相当开放和宽阔的,他们立足本土,植根华人文化传统,致力于马、华文化的交流、互补与融合,同时将马中文化置于全球华人世界的大版图、大格局中,促进其在国际平台上共同发展。而华研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中枢和纽带作用。
一个上午时间,文先生几乎都在向我讲述和展示华社与华研情况,竟然没有只言片语谈及他自己的家世和私事,而我最想了解的正是:眼前这位据传是文天祥的第二十四代子孙的家族史,他们是怎么从中国大陆迁徙到马来西亚的,对我们来说,内中的故事想必都是相当新奇而神秘的。可是,这时已快到1点钟了。
“吴教授,我们先去吃午饭吧。” 文先生站起来,热情地说,“一边吃一边谈。”于是,他带我下楼,走进就在中华大会堂一侧的餐厅里。那是个环境幽雅、清静的处所,像马来西亚的许多大酒店一样,其布局、装修和陈设是中西合璧的,墙壁上悬挂着中国字画和西洋水彩画,柜台上的餐具也是中西兼备。文先生爽朗地说:“我们两个都是花甲之年了,天气又热,我就点几个清淡些的菜。”我很赞同这种真率、实惠的想法,频频点头:“对对对,简单点,千万不要浪费。”文先生对这里的食品显然十分熟悉,他无须看菜谱就点了红烧咖喱牛肉、清炖鱼、炒瘦猪肉和两个时鲜素菜,外加一碗汤,既有马来西亚风味,又有福建菜肴的特色。饮料也是绿茶与咖啡并存,热水与冰块兼有。这顿饭吃得很舒服,很尽兴,我也达到了预想的目的——请文平强博士介绍他的家史,特别是近几代人侨居海外的原委始末、来龙去脉。
文先生告知我:他的父亲文子情生于1890年;母亲陈氏生于1903年,原籍广东惠阳,客家人。“我的父亲原来也在惠阳,他是背着我祖母(她是一位基督教教徒)跑到马来西亚的。当时我外祖母家住在西马。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的父亲母亲又迁到北婆罗洲。我就是1941年出生在北婆罗洲的。很不幸,就在我出世才几个月的时候,父亲就病故了,他老人家享年只有52岁。” 文平强不无惆怅地慨叹道,“我母亲生过5个男孩,7个女孩,可在我没出世前,就死了3个姐姐。我是最小的儿子,对父亲自然没有印象。只是从母亲和哥哥们那里,我对父亲的坎坷人生才知道了一些。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家父是非常爱国的,从他给我们5兄弟起的名字里就能看到他的一片忧国忧民之心。”文先生说,他们五兄弟的名字依次为:平世、平定、平中、平原、平强。说着放下筷子,拿起钢笔,接过我递上的笔记本,写了5个很工整的字:“世定中原强”。“我父亲的心愿,就是希望世界安定,中国强盛。”这使我倏然忆及文天祥表明安邦济世之壮心的诗句:“修复尽还今宇宙,感伤犹记旧江山。”
平强先生介绍道:大哥平世、二哥平定在西马出世,生逢战乱,读书不多,都是普通平民。三哥平中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在广州财经学校任职,现定居香港。四哥平原生于中国,正是文子情远赴马来西亚30年因思念故乡而举家返国时期,他的职业是汽车司机,已退休。几个哥哥的子女都不错,大多上了大学,分布于中国、东南亚及美国。平强先生自己是在55岁时退休的,他共有三子一女,长子、次子均从事管理人才的培训工作,小儿子的专业是搞电子计算机,女儿则在毗邻的新加坡工作。一家人可谓安居乐业,各得其所。他特别说明,其母晚年过得很幸福,与子孙一起住在吉隆坡,直到2002年才去世,享年100岁。“我们祖孙几代人相处得非常团结、和睦,亲情相当浓厚。” 平强先生强调说,“我特别感激大哥二哥,是他们把我抚养成人的。”
当我把话题引到文家的先祖文天祥时,平强先生略顿了一下,沉吟道:“这个问题嘛,过去我并没有特别看重。总觉得,文天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伟大的英雄,身为他的后代当然是很自豪的,不过,我们同他老人家相隔的年代毕竟太遥远了,又长期生活在异国他乡,感性知识不多。”他喝了口茶,仿佛提了提神似的接着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初,我们回到广东老家,看到了家谱,才了解了一些情况。那时侯,我正好10岁,我大哥已经三十多了。”他回忆道:家乡的亲戚大多是农民,虽然文化不高,可他们对文天祥的故事十分熟悉,而且还保留着不少跟文天祥有关系的老习俗,譬如,文天祥因为被皇帝(宋理宗)亲自擢选为状元第一,文家人举行婚礼时可以打13下锣。据说,依照封建时期的旧礼,官吏出行鸣金开道,为知县者敲3下锣,为知府者出行敲7下锣,为道台者(省以下、府以上的高官)方可敲13下锣。直到民国时期,当地文家人仍保留着已延续几百年的传统习俗。家乡族人对文天祥始终如一的无限敬仰、怀念和隆重祭奠,使回国拜扫祖先、探望亲人的游子深受感染和教诲。从此,文平强格外关注文氏家族的历史演变,特别重视对文天祥生平、思想、事迹及著述的探索和研究。他说,他家中珍藏了一本“文氏族谱”,阅之,才得知文氏家族代代相传的概况,而他们这一辈应该是文天祥的二十四代孙。文平强见我对那本族谱很感兴趣,决定复印一本赠我。过了一天,他果然委派华研的同事潘玉婷小姐专程把两份复印件送到我的下榻处。
一份是《文信国公族谱》,另一份是郑良树先生撰写的文章《文天祥家族史迹的新资料——文氏族谱的发现及其价值》。郑良树是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他在台湾就读后,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他记述了《文信国公族谱》的发现和问世过程:“马来亚大学地理系有副教授文平强博士,与良树游,情谊甚笃。本年初,良树游香港大学甫返,与语香江学术概况之余,间及香江文氏家庙,始知其为信国公后人,且秘藏有族谱一册。原谱线装毛笔书写,藏广东归善祖庙内,渊源邈远;今谱乃其兄长于十余年前移录南传,原子笔誊录,间有误笔错字。惟昭穆有序,世代可寻。”本谱卷首有文天祥传一则,传后转录文天祥诗歌多首,诗后有“族谱序”,作者是文天祥第十九代孙文士鹏,他生于乾隆丁已年七月二十二日,本谱完成于乾隆丁酉年,是年文士鹏40岁,距今已达二百余年。
根据这部族谱记载,文氏始祖“文时,字春元,行四。成都人。汉蜀守将文翁之后。五代唐庄宗同光乙酉官帐前指挥使、轻车都尉,来镇江西,巡吉安,至永新。遂家永新。子环。”由此下传,到文天祥为第十三世。关于文天祥的身世记载较详,全文如下:“文天祥,幼名云孙,字履善,一字宋瑞。生宋理宗端平丙申五月初二子时。宝佑乙卯,以易中乡举;丙辰,廷试状元及第,历官至少保、右丞相、枢密使,同督诸路军马,封信国公,尝辟本里东山为别墅,因号曰文山。归隐,起宅于斯。德佑乙亥,奉诏赴难勤王。景炎丙子十一月,潮阳败兵,被执系狱。元世祖屡诱以大用,不屈。至元壬午十二月初九,死节,年四十七。夫人欧阳氏与十二士收殡都城小南门外,后张毅甫奉柩归里,葬木湖大坑虎形。夫人值乱,留于燕,后子升迎归养三年,大年乙巳卒。次夫人颜氏、黄氏,空坑败,黄陷,走至兴国宝石寨,投崖碎身而死,士人葬之,今庙于彼;颜亦陷,死于崖洲,亦庙于彼。子二、女六,俱卒,遗命以侄升子为嗣。国朝景泰中都宪韩雍,请加赠谥,录用子孙。命赐谥忠烈。事实俱载宋、元史鉴及公传记诸篇,又有正气歌传后。今建大宗祠于广州城东,蒙太祖高皇帝表为天地正气古今一人。”
在抗元斗争中,文天祥的直系亲属除夫人欧阳氏外全部壮烈牺牲。因此,嗣子文升子便成为文天祥唯一的继承人。文升子乃是文天祥大胞弟文天球的第三个儿子。族谱记载:“文天球,讳璧,字宋珍,号文溪,与兄天祥同中乡举进士累官至知广东惠州、户部尚书。”“生四子:隆、京、升、新子。”而对文升子的记载是这样的:“入继天祥之后。生于景炎戊寅正月十五日,号学山。辛已,父丞相狱中书付之,命治春秋。父丧,归庐墓侧,后闻母欧阳夫人犹在燕,泣誓曰:‘父骨既归于土,母生不得养,我则非子也。’元大德戊戌,往迎母,得之燕京。元仁宗即位,敕江西省臣以礼聘公,乘传入朝,献九经策。上悦,受所献,命中书颁制,授奉训大夫、集贤院学士。”“六月二十六日,至赣,以疾卒。延佑初,追赠大中大夫、蜀郡侯,谥文庄。配徐氏,封夫人,生三子:富、实、弘;生三女。”往下继续查阅、推算,到文平强这一辈,已经是文天祥的第二十四代的子孙了。
族谱昭示,文天祥的子孙除了留传在国内(江西、广东等地)的以外,有些已迁徙到北美州和马来西亚,而在马来西亚定居的共有四支,即:文天祥的第二十二代子孙文亚元,第二十三代子孙文有谭、文子情和文亚苟。正如前文述及的,由于文子情思念故乡心切,曾一度率全家回国省亲,方有获族谱、传家史的条件;加以文子情的儿子文平强等有高深的文化教养,又才能重视对先祖文天祥家世和思想的研究。“开始,我对这件事的认识并不充分,后来才逐渐理解:了解族谱和家史,就是掌握和研究华人的历史,特别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和爱国主义传统。” 文平强对我推心置腹地说,“原本我是研究人文地理的,退休以后,尤其是三年前担任华研中心主任后,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越来越大,几乎投入了晚年的全部精力,而且决心一直坚持做下去。可惜我因为长期在英国、马来西亚等英语国家读书和工作,汉语不精通,于是我努力学习汉文,现在已主要用中文来写作了,完成一篇论文,我还常常请汉文好的专家帮助修改、润色。有人对我们的工作意义不理解,觉得这些学术研究没有什么用处,但我认为,我们身在海外的炎黄子孙,是绝对不能数典忘祖的,每个华人、华裔都应该继承、发扬中国祖先和大马本地的华人优秀文化。”文先生坚信,他们的许多研究项目是有价值的,比如,他自己近年来对马来西亚华人人口的研究,就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我读过他的几篇学术论文——《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略论其进展与前瞻》、《马来西亚华人人口比率下降:事实与回应》、《马来西亚的华人新村:人口变化与应付措施》等,顾名思义,就可窥见其内容是非常贴近华人社会的族群事业和生活实际的。
不过,远在异国他乡的华人学者们,对于一些理论和思潮的岐见也会产生困惑。比如文先生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历史上的许多英雄豪杰,是在抵抗当时异族入侵的战争中涌现的,今天我们中国各民族已经成为一个大家庭了,还可以宣传那些民族英雄吗?有段时间,有的少数民族对歌颂岳飞的文艺作品不是有争议吗?我谈了自己的观点:对于过去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是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要站在当时当地人民的立场上,判断是非,分清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落后。要是一切都以现在的状况和原则去衡量古人、往事,那就没有伟人与罪人之别了。正如我们现在重视中日友好关系,决不能否定当年日本侵略我国的罪行,更不能抹杀抗日英雄的历史功绩。我说,岳飞精忠报国的思想和《满江红》那样的词章,是永远值得称赞的。同样,文天祥的爱国精神和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以及许多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如在狱中所写的《正气歌》,《过零丁洋》里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千古名句,从文天祥就义时的衣带中发现的“衣带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等等,这些金玉良言,难道不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吗?
文先生很赞同我的看法,我也被这位民族英烈后代的一片赤诚之心所感染。我们俩越说越投机、越有兴致,用罢午餐又一同回到办公室,继续海阔天空地畅谈。
临别前,我们俩照相留念。在选择背景时,文平强先生指着粉墙上悬挂的一幅彩色牡丹图,笑盈盈地说:“这张水墨花卉国画,我很喜欢。牡丹原为中国特产,是高贵和富丽的象征。我们就在这国花下面合影吧。”真是见微知著,处处都可显示一位海外赤子的爱国情结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