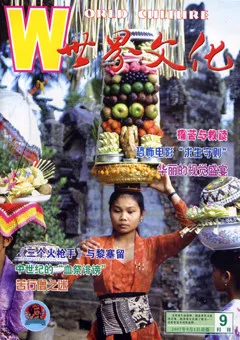明净,通往纯粹的道路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20世纪60年代以来视觉艺术中涌现出的“极少主义”思潮时,会发现托尼·史密斯、罗伯特·莫里斯等艺术家已经把 “极少就是极多”这句悖论式的箴言发展到了极致。虽然用“极少主义”这一概念来概括这些艺术家的特征并不甚完全,但至少显示了其总的特征和共同的目标,即采用极为简单的、通常是几何化的形式,并且具有鲜艳、饱满的“工业色彩”。在极少主义的雕塑中,再也见不到浪漫优雅的人物造型,极少主义雕塑家比亨利·摩尔、阿尔贝托·贾科梅蒂这样已将人物进行变形的大师走得更远,他们完全采用工业方式,制造简单明了的几何化造型,其庞大的尺度完全反映出新的工业时代的特征。
一
何以在上个世纪60年代涌现出这样一种不可一世的后现代主义的极端形式:中立、机械般的无我与浪漫、对对象进行彻底的抛弃并用夸张的方式反映着时代?作为一种艺术思潮,我们在分析“极少主义”的缘起与生发时,必须从其时代特征与艺术史的沿承这两个角度去思考。
首先应当看到,此时人类社会已挺进到“后工业”时代,一个工业技术的白昼。正如1962年“新现实主义者”展览的目录中所写:“在欧洲,同在美国一样,艺术家正在自然里寻找新的方向。所谓当代的自然,就是机械的、工业的和广告的洪流……日常生活的现实如今已变成了工厂和城市。在标准化和高效率这两个孪生的标记之下所产生的外向性,是这个新世界的规律……”与彻底打破了生活与艺术的藩篱的波普艺术家一样,一部分年轻的雕塑家亦感触到后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变化,并运用彻底的工业材质和手段予以表现。
其次,“极少主义”作为人类在现代、后现代情景下艺术探索的一条表达途径,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艺术史的沿革及同时代其他艺术、哲学和文化思潮的影响。“纯形式”一直是现代主义者们所追求的真理,在20世纪初充斥了科学、文化和整个艺术领域的革新。艺术不再模仿任何具体的物质形象,但要以它自身独立的和抽象的形式作为表达和探索的媒介。早在1920年7月15日, 柏林先锋派的汉斯·勒克哈特就在一篇传阅通讯中写到:“纯形式是这样的形式:超然于所有装饰,从直线、曲线和任意形状的基本要素中自由形成。”也就是说,抽象艺术被赋予为时代的象征,成为那个时代精神的真正表现。极少主义作为现代主义的真正终结,其来源可追溯到欧洲的构成主义、至上主义等现代抽象艺术,并在对抽象艺术的突破中寻找自己的根源。
同时,“极少主义”的思潮又关系到美国上世纪60年代波普艺术等反欧洲传统的艺术理念,可以这样说,在极少艺术的作品中汇聚着两种截然不同又明显相关的创作方法——其一是抽象性绘画极端精简的形式:追求艺术的净化,只保留不能再减的必要因素;其二,是波普艺术家表达的新叙述方式:在高雅艺术中使用日常生活中普通、简单、不经修改的事物,寻求直接表达的方法。
的确,正如美国美术史论家L·史密斯在其著作《1945年以来的视觉艺术》中所概括的,战后西方美术的发展趋向于“从极端的自我性转向相对的客观性;作品从几乎是徒手制作转变成大量生产;从对于工业科技的敌视转变为对它产生兴趣并探讨它的各种可能性。”“极少主义”作品以其静默巨大的存在凸显着后现代美术的以上特点。
二
“极少主义”的雕塑革命中,以戴维·史密斯的作品最具代表性。在史密斯看来,除了空间维度这一因素外,绘画和雕塑从来都不是分离的。作品《哈德逊河风景》像是用金属做的线描,尽管雕塑是以二维平面构成的,但透过镂空的空间看自然的风景时,作品便带出了无穷的深度和色彩的运动。当我们面对他的代表作品如《zip》、《立方体》时,会感受到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所指出的雕塑的特质—— 一个支配着周围空间的虚幻的能动的体积,虚幻空间的力。其构图取决于更为先验的重复和连续,立方体的排列焊接不给人的心智和情感留有余地,但又有一种近乎庄严的单纯,其内在的沉默力量使人怦然心动,如同金字塔造型的简单不会削弱其感染力,反而强化了它的伟岸雄奇。其中的立方体犹如生命体的有机部分一样维持着自身,奋力保持着自身的结构,各种视觉元素向四面八方无限的延伸、生长,给予以其为中心的视觉空间以生命。在这个意义上,雕塑强化了感觉空间的生命力,使我们感觉并意识到空间的生命和力量的存在。
另一位代表性的“极少主义”雕塑家是卡尔·安德烈,在材料的选择上,他避免使用光洁可人的材料,而是采用朴实的砖块、枕木、原色的铁板等,而且只保留其没有光泽和悦目色彩的本色。起初他还对材料进行一些雕琢,到后来干脆连这一点点的修饰也放弃了,他所做的只是把材料摆成一定的形态而已。“我认识到我所雕刻的东西正是雕塑本身,我现在不是雕刻材料,而是用材料雕刻空间。”他的作品摆脱了雕塑的垂直因素,通常只是将砖块、圆木、金属等普通之物平铺在展厅的地表,无言地躺在观众的脚下,其结构给人一种与房间的真实透视相冲突的透视感,人与雕塑的关系改变了,当脚踏上去时,可以感知其不同的质感和导热性,以此来改变人们的观念,使艺术变得平凡而谦卑,他说:“我喜欢的作品是这样的,它和你共处一室,但不来妨碍你,你想忽视它们就可以忽视它们。”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像自然物一样存在,可以在自然的情况下自然地消逝。这种无为的态度更是来自于他对《道德经》中“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思想的推崇。
三
以上我们简单地介绍了“极少主义”雕塑中代表性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及其主要作品的特点。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这些雕塑家的创作和艺术品的形式特征,即:
1.大刀阔斧的缩简,运用单纯的几何形体;
2.大胆地对工业新材料进行运用;
3.以纪念性的尺度来进行工作;
这些作品运用最基本的形式实体,冷静但不傲慢,沉默而不喧嚣,在最大限度上突现出“极少主义”艺术家的美学追求。
首先,“极少主义”雕塑十分强调雕塑本体与其周围空间的连续性。一件艺术品是一个三维空间的中心,是一个支配着周围空间的虚幻的能动的体积,环境从它那里得到了全部比例和关系。同时,“极少主义”也更加强调作品与环境的有效结合。在后工业的现代,众多抽象化的建筑是抽象艺术的完美背景,而简单的几何形体作为人们熟悉而又易于记忆的形象,为迷失在钢筋水泥的现代丛林的人们树立了一种纪念体量的抽象心理地图,而非用“自然主义”的饰面掩盖人造的环境。
其次,“极少主义”对受众的阐释和对话的要求也极大增强了,极为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很好地描绘作品的尺寸、形状、色彩的设计,但若观赏者不是在它们的周围,穿越它们、接近它们或处在它们之中,就无法去领会和解释这些艺术品。“极少主义”作为抽象的造型艺术,其本身是非阐释性的,这就为多元的对话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如果我们从哲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分析“极少主义”的那种把对象简化到极致以突现出事物本质的倾向,可以看到,包括整个现代派艺术都完全抛弃了前人所熟练运用的艺术形式,发生这种倒退的原因,正如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所指出的:“可以在他们的基本心理因素中去寻找……这与我们的整个文化状况有关,艺术家变成了社会的局外人,创造文化剩余物的人,他们所感受到的仅仅是所发生的事件的形式和结构。处于这种孤独的精神状况下所做出的观察,也可能会有助于敏锐的洞察力的形成,因为从现实的后退和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就是退步或与世隔绝,一个有经验的观察者,在后退了一定距离后,他观察到的事物往往是事物的更为本质的和更为明显的特征,而那些偶然性很强的细节部分都被省略掉了。”这种对纯粹本质的直接把握是这些优秀的现代派绘画和雕塑企图通过抽象而要达到的目的 。“现代派艺术家运用精确的几何图形的目的,就在于更为直接的去表现那些隐藏着的自然结构的本质。而现实主义的艺术,则是再现这种自然结构在物质对象和发生在物质世界的各种事件中的表现形式,而它的本质则是间接的揭示出来的。而这些抽象的艺术形象,却能够直接的揭示事物的本质。不管它们多么抽象,只要它保留了那种与科学公式不同的艺术感染力,它就是有效的表现形式。”
的确,面对“极少主义”的作品时,我们感受到一种原初的纯粹和神秘,如同先民的“巨石阵”,彰显出人类以其巨大的精神力量在生存的土地上矗立丰碑的尝试,用几何的韵律的手段使空间拥有其自身的地位。这样的一些雕塑家,以其理性淡漠、克制自我,宗教般的虔诚、贵族般的优雅,一种极度简化的精神力量,追求一种不可言说的纯粹艺术体验,力图将艺术品从深度阐释的陷阱中解救出来,以理性甚至冷漠的姿态来抗击着浮躁一时的、夸张的、精神分裂式的社会思潮,以其回到简单质朴的无为的尝试,对抗着异化文明。他们给予观众的始终是淡泊和明净、强烈的工业色彩以及静止之物的冥想气质。
现今,极少主义,这股崛起于上世纪60年代的艺术实践风潮,已经以其简约明了的风格迅速渗透并影响了包括建筑、园林景观、室内设计等各个领域。纯净、流畅、清晰的线条、几何学的造型、宛如东方文化中冥想气质的宁静氛围营造……极少主义艺术一以贯之地砥砺繁琐美学、摒弃琐碎修饰,在越来越拥挤的城市角落为浮躁的都市人留出一份纯净的心灵空间。归返简致素朴的明净与纯粹,这,应该是极少主义艺术在今天依旧焕发独特魅力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