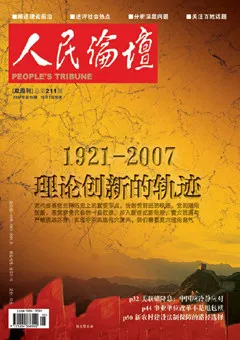当生存权遭遇规则
说到生存权,也许有人会问,在今天,人们的生存权会存在问题吗?我们难道对生存权不尊重吗?
孤立地看,社会快速发展到现在,生存权的确不存在什么问题,它还常常被人们放在很高的位置予以赞美。但在联系和比较中看,生存权的位置并不高,还经常被漠视。
今年5月,沈阳一位16岁的贫困女学生,在一整天粒米未进的情况下,虽然明知不对,但饥饿万分的她还是没禁得住酥香可口的面包的诱惑,在便民店内将面包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在被店主发现并屡次宣称要把此事向学校告发后,觉得无脸面对他人的这位少女,选择自杀来终了一切。在遗书里,她这样写道:“我当时真的很饿,我也知道不好,但是我真的很饿。”
这个例子虽属极个别,但能很好地说明生存权和其他权利之间的关系。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这位少女做出了属于人的本能的选择,看见解饥的面包而伸手。尽管这个举动被赋予了一个词汇叫“偷”,她这一伸手,就损害了他人的财物不能侵犯的权利。
但在少女伸手的这一刻,在她的心里,生存权是明显高于后者的。令人悲痛的是,她把尊严视为高于生命,但没了生命,生存权焉附?
而在那位店主看来,他的面包被偷,偷者就应当受到惩罚。他只知道维护自己的权利,却失去了对人的最基本权利的尊重。设若他不是如此不分清红皂白,而是细心问询,将心比心,悲剧或可避免。
或许,店主对人的生存权的漠视源于他的无知,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有些制度和规则等却不应该如此无知,执行这些制度和规则的人不应该如此无知。
什么是生存权?尽管自生存权产生的那一刻起学术界就争论不休,但有些观点至少是有共识的。邓小平曾说:“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人权就是生存权。在旧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根本就没有生存的权利。”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生存权的对象不仅仅指生活极度困苦,难以生存的人,它还包括那些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弱者和处于经济文化等方面困境中的人。最低的生存权就是维持生命存在的权利。生存权也是发展的,今天的生存权还指维持生命的生存质量的权利。
遗憾的是,我们有一些制度和规则对生存权并不尊重,执行有关制度和规则的人对人的基本生存权并不尊重。比如,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矛盾,其深层次原因就在于城市管理规则与小贩们基本生存权利之间的冲突。
正是基于对生存权的尊重,我们的制度规定“撞了不白撞”,司机不负交规的法律责任,却需担负人道责任,必须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这体现的恰是一种进步。
我们的社会是人的社会,一个社会越发展,越应该尊重人的基本权利。我们不仅要出台各种具体制度直接保障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其他各项具体制度都应当处处体现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甚至为其网开一面,给予相当的宽容。这正是法的人性化的一面,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具体体现。
常常想起母亲给我讲的那个大饥饿年代的故事。那时是大集体,家家都有人饿病在床。生产队长带领群众去收割稻谷,结果没有一个人不在偷偷撸稻子。那时母亲她们大热天都穿夹层裤,把裤脚系紧,撸下来的稻子就都偷偷地从裤腰塞进夹层里。母亲说,父亲那时患浮肿,要不是用这个办法,父亲早就饿死了,哪还有你们。语带自豪又有无奈。
其时,生产队长又怎么不知大伙在这么干?大家又怎么不知这么干违法?但是,在人的求生欲望面前,在人的生存权利面前,人的本能总是指导人们干合理不合法的事,从而保障人的生命的延续。
在特殊时候,生存权对一般规则与制度具有冲破力,让我们警醒和反省的,恰恰应当是对生存权的尊重与敬畏,和对一般规则的深思。(作者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