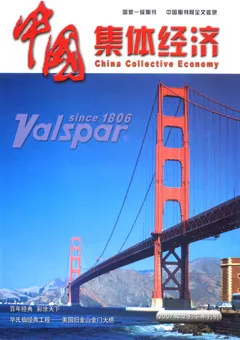组织执行力及其中国语境
摘要:在中国语境中,组织的原型是经纬交织的编织工艺。执行的原型是赶赴现场抓捕罪人。组织执行力的三大误区是组织执行力迷信、组织整体功能失衡、组织思考力缺失。在古老的《易经》智慧中可以找到对治之方。
关键词:组织;执行力;中国语境
组织的执行力,尤其是商业组织的执行力,是当下中国管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如何提升组织执行力?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能否产生实效?这些都要考察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语境,通过对组织执行力进行原型分析,才能彻底的了解。
一、组织及其中国语境
要探明“组织”本源,须考察汉字语源,探寻蕴涵在汉字文本中的组织原型。“组”字是形声字,金文从糸,且声。《说文·糸部》云:“组,绶属。其小者,以为冕缨。从糸,且声。”“组”字从糸,本义为宽丝带。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当中说:“属,当作织,浅人所改也。组可以为绶,组非绶类也。”就是说,许慎的原文应作:“组,绶织也。”这一校正对于探索“组织”的原型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段玉裁又说:“织成之绶,材谓之组。……大为组绶,小为组缨,其中之用多矣。”“组”字从糸,是强调它是以丝编织的,有编织义;“组”字且声,则是探寻“组”的声符示源义,即声符隐义。且字古形体象神主牌位,乃祖字初文,表达先民的祖先崇拜,权力来自先王列祖,对权力的渊源的回溯就是“组”的深层语源义指示给我们的原型意蕴。
“织”同样是形声字。篆文从糸,戠声。《说文·糸部》云:“织,作布帛之总名也。”“织”字从糸,本义为制作布帛。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经与纬相成曰织。”指的是细致精密的编织。“织”字戠声,它的声符表示源义来自声符“戠”的本义。“戠”是兵器上的饰物。在声符隐义的层面,“织”这种细致精密的制作工艺需要变化纹理图案以作装饰。纹理图案作为符号,是先民用来表示丝制品的用途、风格、档次不同的个性化区别所作的标记。纹理图案的个性化风格是“织”在深层语源义中的原型意蕴。
“组织”连言,较早的词例有《吕氏春秋·先己》汉高诱注:“组读组织之组。夫组织之匠,成文于手,犹良御执辔于手而调马口,以致万里也。”这里“组织”是指经纬相交,织作布帛。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这里“组织”是指织成的织物。观察“组织”的词例,其在中国语境中的原型是经纬交织的编织工艺;“组织”对权力渊源(授权)的回溯和它对个性化风格(区别性)的要求则是“组织”原型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当中的哲理性意蕴。上溯传统,下开新风,正是“组织”原型本具的内在规定性的呈现。
明了“组织”原型及其在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意蕴,对我们理解严肃而抽象的组织理论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组织是个人之间的“编织”,具有复杂的交往关系。在组织当中,授权实际上有纵横两个维度:横向上,领导者的权力来自组织的所有成员;纵向上,领导者的授权来自传统,这里的传统既包括组织的传统,又包括组织所在的更大的组织的传统。组织领导者的授权来自传统,因而组织行为必须内在包含“祭祀”行为所具备的如下两重性,方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合法性:其一,“祭祀”也就是将组织行为及其成果呈现在祖先及天地面前,接受传统及自然的检视;其二,“祭如在”,传统价值观必须在组织行为中获得与当下生活的共时性。这就是说,组织行为必须“慎终追远”,创新必须与传统有自然和顺畅的承接关系,新旧交融,守旧开新,“其命维新”。
二、执行力及其中国语境
执行力这一概念,意谓对执行的效果有一个评估的尺度与工具。因此对“执行”的原型意蕴的探索至为重要。“执”字是会意兼形声字。甲骨文从丮,丮是跪着的人,“执”字从丮,本义为捕捉罪人。《说文·丮部》云:“执,捕罪人也。”“执”字从丮,是强调捕捉、逮捕这一动作,它所针对的对象是罪人,这就限定了“执”字在上古汉语语境中的刑罚、刑法之义类。而“执”字声,则揭示了它的声符示源义。透过声符示源揭示汉字理据,这就是许书“亦声”的理论内蕴。即手铐。跪着的人双手戴铐,失去行动自由,意味着“执”是一种严格的控制行为。从“执”字的深层语源,可以明确“执”的原型意蕴乃是定向、定位的严格控制。
“行”字是象形字。甲骨文像十字路口形。《说文·行部》:“行,人之步趋也。”十字路口的存在就是为人之“行路”而设,“人之步趋”将趋往何方,“行路”的选择又将承担怎样的因果,这正是人之为人和命运之为命运的基本意蕴。概言之,“行”意味着选择与抉断,停在十字路口的脚步仿佛蓄势待发的箭,射往何方,关系重大。“行”的深层语源启示给我们的原型意蕴即为选择、抉择。
“执行”连用,较早的词例是汉刘向《列女传·黎庄夫人》:“黎庄夫人,执行不衰,庄公不遇,行节反乖。”这里“执行”是指坚守节操。唐元稹《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追得所没庄宅、奴婢文案,及执行案典耿琚、马云亮等检勘得实。”这里“执行”是指承办、经办。观察“执行”的词例,联系其深层语源义中的原型意蕴,则可得出如下认知:“执行”是赶赴现场捕捉罪人,这是“执行”在中国语境中的原型;“执行”要求透过选择与决断,实行严格定向、定位的控制行为,并对此行为承担后果,这是“执行”原型在历史文化语境当中的哲理性意蕴。坚守节操的“执行”和承办、经办的“执行”正是“执行”原型本具的内在规定性在道德与事功两个向度上的展开。
理解“执行”原型及其在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意蕴,就有可能帮助我们勾勒出本土执行力理论的基本架构。执行怎样才能是高效的?在组织中,执行与权力的关系是什么?执行的前提是什么?它与个体责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在“执行”原型中,执行者不仅仅是与执行对象之间建立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从选择对象,到分辨对象,再到锁定对象,全过程都是在组织中进行的。在交互性的组织网络当中,执行权力既有承续性,又有风险性。根据执行权力的承续性,它是决策权力的承接与延续,必须对决策权力负责;根据执行权力的风险性,它可能造成各种无法完全预料的后果,必须对执行对象负责。评估执行的效果,从来不是简单地进行单一环节、单一视角的评价,而是对执行力在组织的整体结构中的表现进行综合立体的考量。这是今日研究组织执行力特别是商业组织执行力时尤须特别注意的。
三、组织执行力:误区与对治
在今日中国的商业组织中,执行力被相当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视为提升效益和改善性能的关键。他们相信,只要执行力得到提升,企业就会摆脱困境,在竞争中胜出,即所谓“赢在执行”,却往往陷入组织执行力的误区。
(一)组织执行力迷信
组织执行力第一大误区即是组织执行力迷信。当人们认为组织能否在竞争中取胜完全取决于执行力的状况,他们及他们所领导的组织就已经陷入了执行力迷信的误区之中。其症结在于,组织的领导者并不明白执行力承担的功能是什么。在组织的运作中,执行只是重要环节之一,其前提是组织决策。在执行之外,与之平行的是组织监督;在执行之后,相继而行的是组织绩效的评估和组织运作的纠错。执行力的强与弱远非决定商业组织成败的关键性因素。此误区的危害在于,倘若商业组织的执行力被强调到不恰当的程度,人们就很容易忽略组织决策、组织监督、组织绩效评估和组织运作纠错等关键环节,从而使组织的运作出现故障。事实上,前无正确的组织决策,后无完善的绩效评估,组织执行力的片面强化将可能与组织效益和预期成反比;失去有效的组织监督和组织运作纠错,组织执行力越强,组织就越危险。
在中国历史文化的语境当中,应如何避免“组织执行力迷信”的误区?依据《易经》智慧,可从“旅”卦的卦辞当中得到启示。“小亨,旅贞吉。”《彖辞》上的解释是:“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古代君王的旅行皆以祭祀活动为期,且伴随始终。因此“旅贞吉”就印证了前文所述“组织”的原型意蕴,构成一种随时随地向人文传统与天地自然敞开的开放性。阴柔得到中位,在外边的阴爻能顺从于阳刚的阳爻,这里指处于误区中的组织能够顺从于人文传统和天地自然。静止而能够附丽于光明,取法于人文传统和天地自然。人文传统和天地自然的悠久与广大,意味着拯救小气度需要大格局。这就期待组织领导者的个人修炼,以及组织整体的不断更新了。
(二)组织整体功能失衡
组织执行力第二大误区可称为组织整体功能失衡。倘若组织的领导者由于主观认识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组织执行、绩效评估的功能偏强而其余各环节如组织决策、组织监督的功能偏弱,就会导致组织整体功能失衡。此误区的症结在于,组织能量淤阻于某一环节,整体能量运行不畅,失于疏导,而致实者益实,虚者益虚。必会致使绩效评估功能过盛而失轨,运作纠错功能过衰而无力,而过盛的组织绩效评估必然偏颇遂利,过衰的组织运作纠错必然软弱无能,从而致使组织整体功能失衡。此误区的危害在于,组织能量淤阻倘不及时得到疏导,必会在某一时刻出现局部爆发,并因组织结构的崩溃而导致组织毁灭。
在中国历史文化的语境当中,对治“组织整体功能失衡”误区仍要求助于《易经》的智慧。在“噬嗑”卦的卦辞中,我们读到:“亨,利用狱。”《彖辞》上的解释是:“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其本义是牙齿的用力咬合,在此可读解为果断的决定和行动。因此“利用狱”在这里就意味着用强有力的手段迅速解决问题。阳刚阴柔分别运动而能光明,端赖阴阳整体结构的平衡。震雷闪电相合而且显彰,意味着结构内部能量的良性流动与汇合。所以才说“柔得中而上行”。打开能量淤阻,疏通能量通道,才能使“柔得中而上行”的良性能量流动成为可能。期待组织经营者和管理者痛下针砭,泄实而补虚,导源而畅流,以重振组织生机与活力。
(三)组织思考力缺失
组织执行力第三大误区是组织思考力缺失。组织思考力,即组织思考的功能与绩效。组织思考不仅仅是领导者的思考,它是“编织”在组织之网当中的每个独立个体的思考。组织思考又不同于组织决策,它所思考的范围不仅限于组织发展的方向和组织行为的框架。它是贯穿于组织从决策、执行、监督到绩效评估和运作纠错的每一个具体环节之中的。组织思考力的缺失,直接影响到组织执行力的质量与效能。此误区的症结在于:组织的领导者误将组织思考等同于组织决策,认为组织执行与组织思考无关,从而轻视甚至排拒执行环节的组织成员对组织思考的积极参与,形成了领导者对组织思考的垄断。没有了充分参与、脑力激荡和观点制衡,领导者的思考力必然日趋萎顿和缺失。其危害在于:倘若组织思考力不能够对组织执行力提供有效的支撑,执行环节的组织成员又如何能创造性地和卓有成效地执行任务?仅就执行环节而言,如何能够执行得更经济、更高效、更迅捷,也始终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经验式的激情型的且不可持续的执行只会给组织带来不可控制的潜在危害。吉林大学赵雨先生在评价名著《日瓦戈医生》时曾说:“黑暗的力量以光明和胜利之名收缴了普通人独自和理性地反抗不公正的权利,于是黑暗吞噬黑暗,暴力遭遇暴力,混乱中普通人踉踉跄跄地跟随着,渐渐变成了混沌的人,甚至沦为疯人。”(赵雨:《读〈日瓦戈医生〉三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大学人文》第6辑第65页。)商业组织和公共组织的道理是共通的,如何以思考的方式避免成为“混沌的人”甚至“疯人”,从而避免将组织整体拖入混乱和崩溃,这是值得包括经营者和管理者在内的每一个组织成员深思的。
如何对治“组织思考力缺失”?依据《易经》智慧,可参照“临”卦的卦辞来谋求解救之方。“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彖辞》曰:“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什么是“至于八月,有凶”?因为八月阳衰而阴长,组织思考力属阳刚而不足,对整个组织的命运来说,自然是“有凶”了。组织思考力的阳刚本性,注定它应浸漫而长大,喜悦而顺从,居中而照应,亨通而中正。在组织功能的每一个环节都应当彰显组织思考的存在。回归中国历史文化语境的组织执行力顺“天”而合“道”,生命力自然是无穷的。
*本文为云南师范大学校级资助项目。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