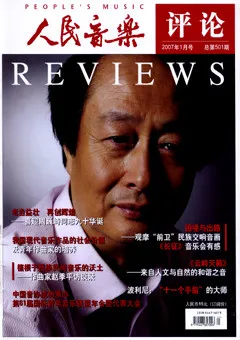中华乐派的新世纪共建
一、 关于“乐派”
中华乐派如何在新世纪共建?
这“建”,并非“建立”,而是“建设”之意。正在建设的乐派,是上世纪萧友梅、马思聪、冼星海等诸位先辈所抱“乐派”理念在新世纪人文条件下的延伸。
要建设的,是什么样的乐派?是个半截子的?是那种四分五裂的?是那种嚣张短命的?还是要一个完整长存的乐派?!
对于“乐派”概念的理解,至今尚有分歧。这分歧若不影响建设实践的方略倒也不妨求同存异,但若对实践方略有所干扰,那就最好及早辨清。
按照欧洲学界的习惯,“乐派”概念的内涵包含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有其代表作,二是有这些代表作的作者群体,三是由他民族的评论者对这些代表人物的代表作予以承认。这样的“乐派”,好比采集成束的花,而不是花圃里的花丛,其存在是狭窄的,其成立是被动的。
然而,在新世纪之初我们来谈论的乐派建设问题,却既突出了文化的自觉主体意识(主动性),又强调了深厚的土壤根基(广阔性)。有些学者虽然不同意“乐派”概念包括其赖以立足的根基,却承认这样的底座是不可缺少的;这看法就跟“四大支柱”的建设方略有了共同语言。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有了这样的共识: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多元一体的存在。由此引发的思考是:中华乐派在新世纪的建设是否应当跟这存在相适应呢?在这多元的共同体中,有为数众多的民族人口数量较少,由于地处偏远,其音乐文化的状况在几十年前还鲜为学者们所知。这众多音乐文化品种在中华乐派建设过程中地位如何?作用如何?难道不是我们思考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吗?像朱践耳这样的知名作曲家,在上世纪就开始深入学习研究这些民族音乐文化,这样的精神是值得褒扬的。对这些民族音乐文化的采集、考察、整理,在上世纪编纂“五大集成”时已着手进行,在新世纪还要持之以恒。再进一步,是否应当思考如何从这些民族成员中挑选新生力量,提供条件,让他们有机遇成长为作曲家呢?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有过许多机会亲眼见到、亲耳听到富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许许多多声乐、器乐品种的鲜活表演,为其特异风貌的鲜艳所震惊。这些事象,可以说,大体属于表演艺术层面;但是,按照民族民间音乐固有的表演原则,那并不是单纯的二度创作,而是往往闪烁着一度创作的火花。这些火花是现场即兴迸发的,并不预先写谱,事后也往往不留谱稿。正因为如此,这样一来的一度创作火花往往被学者们忽略,其茁壮的生机就被埋没了。这样的一度创作火花也并非偶然的昙花一现,而是由深远的乐脉所支持的,具有民族与地方特色的文化传承方式,这传承是悠久的自然存在。当代的音乐教育体制岂可弃之不顾?岂可以彼此断裂为荣?中华乐派的新世纪建设,岂可对这样的音乐文化事象不闻不问?若遵从欧洲学界使用“乐派”一词对惯守的概念篱笆,把这一大层面的鲜活文化事象拒斥于“乐派”界限之外,难道是合乎学术公正的吗?!
概括地问:建设乐派的方略,要的是自然成长还是揠苗助长?若要后者,可以只顾“评”,着力于“选”和“扬”,可以不顾教育体制,不顾遗产保护,不顾体系化梳理,不顾音乐表演艺术在各地区、各民族的活态存在。若要前者,那就要懂得培土保墒、施肥、浇水,就不可不致力于理论、教育、表演、作曲四大支柱相互间的活性连结,以求得各方面军分工奋斗前提下的文化整合。
二、 四大支柱相互的活性连结
新世纪中华乐派在成长过程中将陆续涌现出代表人物、代表曲目、代表作品、代表论著。然而中华乐派立足的基本点在于整合,整合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从宏观视角来看,中华乐派包含四大支柱:理论、教育、表演、作曲,整合的持续过程也就是四大支柱相互之间连结交融的过程。为此,应及早探寻四大支柱相互间活性连结的机制。
教育是关键。近代现代的音乐教育体制上世纪从欧洲移植过来之后,其教学内容尚未适合中华音乐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现实需求。这体制又以放射的方式影响着其它三大支柱的状况,在相当程度上阻碍着民族音乐文化自觉主体意识成熟的进程。因而,反过来,其它三大支柱都正在面对这一关键发出强烈的诉求,期待着音乐教育体制的更新。
更新的目标如何?理论是先导。理论包括音乐学、技法理论与基础乐学。理论层面所提出的改革目标是否恰当,取决于理论研究是否采取脚踏实地的态度、是否运用科学的方法、是否具备理论的逻辑结构。作为理论研究成果的目标意识,能否朝着正确的方向唤醒音乐文化的自觉主体意识,也取决于上述三者。
音乐表演艺术,包括声乐与器乐表演艺术,还包括运用肢体面部表情语言的指挥艺术,是植根的土壤。从根须向枝叶输送养分的管道必须通畅。中华56个民族多元一体的传统音乐文化,在表演实践中的鲜活存在与传承动势是新世纪中华乐派的生命源头所在,这源头活水对于音乐教育体制的持续诉求,是音乐教育改革更新的强劲动力。
音乐创作实践,包括群众性与专业型的创作,包括民俗现场即兴与通过谱稿实现的创作,是发挥众多个体创造性的探索开拓行动。其成败还取决于善否发扬传统音乐文化的潜藏活力,有否足够厚实的主体意识教学修炼历程的奠基支撑,能否凭藉高水平的表演过程与广大听众互动互应。其成败也是对音乐教育体制健康水平的检测。这又从文化意象的角度对音乐教育体制提出了热切的诉求。
唯有确立四大支柱相互间的活性连结机制,方能使新世纪中华乐派各方面军的努力得以有效整合,得以作为一个整体屹立于世界音乐文化之林。
赵宋光原星海音乐学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于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