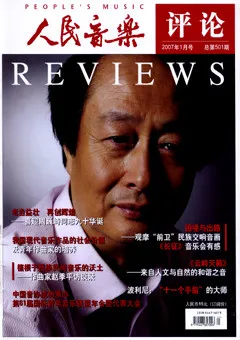建设“新世纪中华乐派”
从2003年8月《人民音乐》发表了我们的《新世纪中华乐派四人谈》以来,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人民音乐》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学院曾分别先后于2003年9月、2004年10月两次召开了有关这方面的座谈会。三年来,一些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章,亦陆续散见于音乐报刊上。为了使大家的看法、意见能更近距离地自由碰撞、沟通,我们在中国音乐学院院领导的支持下,召开了这次“论坛”。在这里我们向中国音乐学院院领导及所有参与筹备工作的中国音乐学院的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现在,我们就“新世纪中华乐派”这一论题谈一些看法。
一、历史的回顾
社会背景:
二十世纪已经过去。
人类世界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乱创伤,又经历了战后从工业文明到信息革命的经济高速发展,进而面临“经济一体化”的格局。
中国在整个二十世纪,经历了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急风暴雨,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自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高速发展、文化空前活跃的时期。
音乐状态:
统治世界乐坛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俗称“西方”)专业音乐,在经历了三百年左右的发展,历经古典主义——浪漫/后浪漫主义——印象主义等几大块时期,终于走到了现代主义(二十世纪前半叶)、后现代主义(二十世纪后半叶);虽还未失去其对世界乐坛的强大影响力,但随着东方、“南方”各民族音乐的兴起,其影响已远不如前。与其相反,东方、“南方”各民族音乐的全面发展与兴起,形成了多元化的世界音乐的新格局。
中国音乐从二十世纪初叶清末民初算起,经受了西方音乐四次大输入:世纪之初;二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八十年代。在梁启超、沈心工、李叔同、黄自、萧友梅、聂耳、冼星海、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音乐先驱以及当代老一辈音乐家的倡领下,中国音乐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冲破文化禁锢主义的桎梏后,更是一发不可收地迅猛发展:专业院校源源不断培养出大批人才,一支量多质高的专业队伍早已形成;理论研究多元竞荣,创作表演蜚声国际乐坛;国民音乐教育空前普及,群众音乐生活空前活跃;专业与业余共荣,传统与现代并存等等。应该说,西方专业技术理论的引进与输入,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没有上世纪的“四次大输入”,也就没有中国乐界辉煌之今日!然而,在今天欢呼“一片繁荣”、享受“丰硕成果”的同时,我们必须冷静地看见“四次大输入”的一个致命的负面效应:20世纪在中国大地乐界上进行的是一个强弱势不对等的交流!强势一方无可还手地被全盘接受,弱势一方还来不及准备好就在许多领域一败涂地、溃不成军——以至忘了自己的根,一味照搬西方(从美学理念直至具体技术理论)!严重的还不只是具体的技术模仿,而是心理的顶礼膜拜!如此就必然留下了一系列心理上、专业上的“软伤”和“硬伤”;当然,不可否认,有些虽随着时代的发展,已在不断变化(如,50年代成立民族音乐研究所,60年代号召“民族化”,专业院校也设置一些民族、民间音乐课程,特别是在近二十年,由于国内外大环境的巨大变化,中国音乐界本体意识空前觉醒,可以说已基本上进入了一个东西方兼容并蓄、不带偏见、各显神通、理性思考的时代……),但应该说,还没达到“质”的、根本上的变化;因此,伴随着各领域取得的不可估量的巨大成就,乐界上述种种(“技术理论上对西方的照搬模仿”、“心理上对西方的顶礼膜拜”等)也还有许多一直延续(或曰“残留”)至今。它已成为中国音乐要在二十一世纪有一个质的飞跃的巨大障碍!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它是历史的局限,也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必然!我们谁也不怪,谁也不能怪!我们只是要做我们这一代音乐人义不容辞应该做的事:接过这一棒,在前辈们开创的事业上来认真清理、分辨、疏导、研究、补充、建设……
二、面对的现实
世界乐坛
历史以其不可逆转的脚步,迈进了二十一世纪。透过纷纭繁杂、千姿百态的表象,我们还是能看清世界乐坛的总体概貌:
西方乐坛,基于彻底的个性解放的现代、后现代音乐虽早已打破古典传统的垄断,但蕴涵着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古典音乐、浪漫主义音乐及其传统,仍然根植于全社会。流行、古典等多种形态、体裁的音乐流派并存,各行其是,各有所归!
东方乐坛,追逐西方的专业理论与技术的狂热和民族本体意识的不断觉醒,使得东方各国出现了许多既具有现代意识、技法又具有强烈的本土情结的理论家和作曲家(诸如,日本的武满彻,韩国的尹依桑等)。至于掌握了顶尖西方技术的器乐和声乐表演艺术家就更如雨后春笋!“南方”乐坛(诸如环太平洋诸岛国),其音乐也正以其原生态的旺盛生命力和专业音乐家的不断加入,而愈益蓬勃发展。
我国乐坛
在世界乐坛纷纭繁杂的背景下,当前我国乐坛亦不能例外。一方面是各种音乐思潮“百家争鸣”,各种音乐技法、唱法“百花齐放”,可谓一片繁荣,实际也确有极大发展!另一方面是经济大潮猛烈地冲击乐界:心气浮躁,急功近利;不重根本,只顾眼前;不练基本功,一切为获奖……可谓泥沙俱下,良莠难分。可以这样说,当前我国乐坛既具有提出“新世纪中华乐派”这一理念的需求,也具备建设“新世纪中华乐派”这一目标的可能!
三、未来的展望
站在这世纪的门槛前,面对这匆忙如过眼云烟的世事和五光十色的东、西方社会,多少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扑面而来:到底什么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到底什么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不错,西方音乐有它辉煌的过去,也有它繁华的今日,但,这一切能替代我们吗?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当然,我们是明确的:我们既不是民粹主义,也不是虚无主义。我们的历史使命应该是:面对这浩瀚的传统(东方的、西方的),学习、掌握并继承传统中的精华,努力结合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有独立见地地、持续发展地建设“新世纪中华乐派”,走出一条中华乐人之路。如果把我们的视角放到世界范围来审视,“新世纪中华乐派”的发展与壮大,不仅是复兴中华民族的总体需要,也是对全人类音乐文化的一种贡献!
所以,在2003年8月,我们四人共同提出了“新世纪中华乐派”这一理念,并且在众人的关心与建议下,逐步充实完善出一个提纲(见附录)。当然还需要不断“充实完善”——特别诚挚地希望在座诸位和一切关注“新世纪中华乐派”的中华乐人,以主人翁精神共同来“充实完善”它(从“理论基础”直到“具体操作”等方方面面)。有人说我们想探讨这些问题是“理想主义者”。其实,真正严肃的艺术家,一定、而且在当代社会更应具有这种“理想主义者”的追求、意志与品格!有人认为这是新时代的“乌托邦”。其实,“新世纪中华乐派”并非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