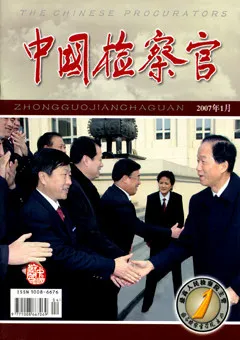论单纯“利用”式犯罪
内容摘要:单纯“利用”式犯罪,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一些案件,主观方面,对他人的先前行为一般持肯定的态度,即在了解并认同其他人的先前行为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犯意。其客观方面,把他人的先前行为作为自己犯罪行为的有利条件消极地加以利用,从而实施自己的犯罪行为。
关键词:“利用”式犯罪共同犯罪 承继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案件,行为人在他人斗殴的过程中,临时起意趁机拿走斗殴者身上财物逃跑,犯罪嫌疑人见被害人被他人灌醉后,对被害人的财物顺手牵羊等等。这些案件的基本特征是:1.后行为人与他人无通谋;2.后行为人单纯地利用他人的先前行为或先前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为自己的行为服务;3.他人的先前行为(不一定是犯罪行为,也可以是合法行为)并不是后行为人在同一犯意下所引起的;4.先前行为与后行为通常能结合成《刑法》中的复合行为犯罪。在本文中,笔者试对这一类单纯“利用”式犯罪,阐述自己的观点。
甲某与乙某无通谋,甲某见到乙某抱住丙某殴打,甲某趁机拿走丙某腰间价值2000元的手提电话逃跑。对甲某夺财行为的定性,主要有两种观点:1、抢劫罪,认为甲某的行为应承继乙某的暴力行为;2、抢夺罪,认为甲某只单纯“利用”丙某不能反抗的情况而公然抢夺。
第一种观点的理由大致有两种:(1)片面共犯论,虽然后行为人与他人事前没有通谋,但后行为人了解他人的先前行为,并利用他人的行为或其行为的结果实施自己的行为,在先前行为的主观故意上行为人与他人是一致的,可以看作后行为人有单方面的意思联络,由于后行为人对先前行为的认同及利用,使得其先前行为实际上成为后行为人的共同行为,与片面共犯相类似,应比照片面共犯处理;(2)间接正犯论,后行为人以他人的行为或其行为的结果作为自己实施犯罪的工具,实际上间接利用他人实行犯罪,类似于间接正犯,应比照间接正犯处理。以上的共通点是将他人先前行为的性质加入到后行为人的行为中去评价。即后行为承继先前行为的性质。
第二种观点的理由,认为后行为人只是单纯地利用他人的行为或结果而犯罪,后行为人与他人并没有共同犯意,并不构成共同犯罪,那么后行为人当然就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对先前行为负责。即后行为不承继先前行为的性质。
上述案例,后行为人实际上是单纯地利用了他人的行为而为自己服务,这一类型案件的争论点就在于如何评价这种“利用”,利用他人的行为是否就等于承继他人的行为?
一、“利用”的性质
要弄清利用他人的行为是否就等于承继他人的行为的这个问题,就要了解什么是“利用”。刑法上的危害行为,是指由行为人的心理活动所支配的危害社会的身体动静,它具有三个基本特征:1.体素,危害行为是行为人的身体动静;2.心素,行为人的身体动静是由行为人的心理态度所支配的;3.害素,由行为人的心理态度支配的身体动静,必须对社会具有危害性。单纯“利用”式犯罪中的“利用”,笔者认为它是“使事物发生效能”的意思,属于刑法学上的“静”行为。该种“静”行为也是由行为人的心理态度所支配的,这种对心理态度的支配,表现在行为人实施行为时对其状态、条件的选择或所持的态度。而这种“静”行为的害素则是从属于后行为,由后行为本身所决定。
相对间接正犯利用他人犯罪中的“利用”,单纯“利用”式犯罪的“利用”是一种消极的“利用”,它是从属于后行为的,并无独立性,也就是说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为。举例说明:护士甲某利用病人乙某被医生丙某正常治疗下麻醉晕迷的状态,拿走其财物。在这里,甲某选择了在乙某晕迷的这个条件实施取财行为,对其麻醉晕迷的状态持肯定的态度,“利用”是取财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利用”是行为,但从属于取财行为,是后行为的一部分。没有后行为,也就没有“利用”可言。而间接正犯中的“利用”则是积极的,指的是行为人“用手段使人或事物为自己服务”的意思,与“消极的利用”最大区别在于,积极“利用”是行为人对被利用的人或物使用了手段(也可以说实施了某些行为),所以这种积极的利用具有独立性,是整个危害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二、“利用”的比较分析
后行为人单纯地利用他人的先前行为是否就承继其先前行为的因素,对其后行为与先前行为作综合评价呢?笔者认为不能。下面试以两种相类似于单纯“利用”式犯罪的犯罪类型来比较分析。
(1)主张间接正犯论的,将后行为的“消极利用”比照成间接正犯中的“积极利用”是错误的,因为“消极”与“积极”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后行为的性质。上文已论述了单纯“利用”式犯罪的后行为人的“利用”是消极的,是从属于后行为的。笔者认为,在行为人单纯地利用他人行为而犯罪的犯罪类型中,由于并不是后行为人的积极行为所导致他人实施先前行为,行为人对他人不起支配作用,他人的行为不受行为人所控制,其性质就与其实施行为所依存的“时间”、“地点”等犯罪环境相同一样;对于后行为人来说,他人的先前行为就只是实施后行为的客观存在的犯罪前提(条件)而已。危害行为是犯罪构成的核心要件,其时间、地点之类的“犯罪环境”是行为的存在形式。虽然少数犯罪要求在特定的犯罪环境下实施,但实际并不是对犯罪环境的要求,而是对危害行为本身的要求。也就是说,在单纯“利用”式犯罪中,他人的先前行为作为后行为的犯罪环境,不影响后行为本身的性质。而间接正犯中的被利用的他人行为是由行为人所引起的,行为人对他人起着不同程度的支配作用,他人行为实际上就等同于行为人本身的行为。在间接正犯中,被利用的他人行为也就理所当然地被间接正犯所“承继”了,即后行为与先前行为是作为一个复数行为来看待的。因此两种类型的犯罪中的后行为并不能互相比照。
(2)主张后行为结合先前行为共同评价的片面共犯论,实际上也是不正确的。在片面共犯中,帮助犯是为了帮助实行犯,为完成实行犯的犯罪目的而创造条件,有单方面意思联络。而单纯“利用”式的犯罪中的后行为人只是为了自己的犯罪目的,并不是帮助他人;所谓“利用”,只是后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所持的态度,对于犯罪环境的认同或者选择,并不能说是意思联络。又以护士甲某利用病人乙某被医生丙某正常治疗下麻醉晕迷的状态,拿走其财物的例子来说。甲某对乙某被丙某麻醉晕迷的状态是持肯定的态度,如果持肯定的态度就等于意思联络的话,甲某就与丙某有意思联络,甲某与丙某就成为共同犯罪,导致的结果是客观归罪。所以说,单纯“利用”式的犯罪中的所持肯定的态度不等于意思联络,当然不属于共犯犯罪的类型,后行为与他人先前行为也不能结合成整体来评价。诚然,这两种类型的犯罪行为及危害结果都是一样,仅是“为他人”与“为自己”的主观不同而导致的行为的定性不同。原因在于,片面共犯中的帮助犯的帮助行为是从属于实行犯的实行行为,是一个犯罪目的下的复数行为,因此要结合成一个整体来评价;而单纯“利用”式的犯罪中的后行为在一定程度利用了先前行为,但这种利用是消极的利用,后行为与他人的先前行为并不是统一于一个犯罪目的,而是基于两个犯罪目的而各自实施的行为,两者是独立的个体,因此是分开来评价的。
综上所述,单纯“利用”式犯罪中的后行为人与他人无共同或单向的意思联络,二者不是共同犯罪。后行为人只是消极地利用他人的先前行为,没有积极地引起他人的先前行为,不是间接正犯。单纯“利用”式犯罪中的后行为人与他人实际上是同时犯或先后犯。他人的先前行为引起的客观状态,只是后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环境,只是作为实现后行为人犯罪目的的有利因素而存在,并不影响后行为的性质。从刑法的因果关系角度上看,对于后行为产生的“结果”来说,他人的先前行为只是“条件”,并不是后行为人所作出“原因”,条件可以起到制约原因的作用,使原因加速或延缓引起结果的发生,但条件本身不能直接决定和制约结果的发生与否,也不能改变其原因自身的性质。而且该“条件”并不是后行为人所引起的,因此不能将“条件”(他人的先前行为)代入到“原因”(后行为)中去评价,也就是单纯“利用”式犯罪的后行为并不承继他人的先前行为。
责任编辑:苗红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