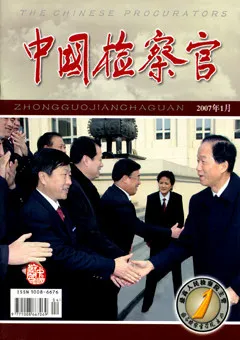从“世纪争产案”证据采信谈笔迹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
内容提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鉴定结论作为法定七种证据之一,也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然而,实践中对各种证据应如何进行审查判断,法律没有也不可能作出更为详细具体的规定。因此,实践中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方式在不同司法机关、不同案件承办人之间各有不一。这不可避免地会严重影响该类证据在案件中的作用发挥。笔迹鉴定与其它类物证鉴定技术相比,由于存在一定特殊性,固对其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似有更难之处,因此,对其审查判断也应遵循其特点规律。否则,就会走向或盲目迷信,或无所适从的歧路。本文结合一起民事案件的证据采信,就笔迹鉴定结论审查判断及相关问题谈一些个人浅见。以期增进交流,澄清认识,促进工作。
关键词:“世纪争产案” 证据采信 笔迹鉴定 审查判断
一场民事官司审判惊动了港属三级法院。一份遗嘱真伪认定决定了400亿港元的归属继承。历时8年,耗资上亿,创庭审纪录。扑朔迷离,一波三折,最终以内地“铁三角”而著称于世的笔迹鉴定专家的鉴定结论,未能被法官采信,香港法院终审法官最终以普通法的举证责任和一个已去世的在场人的证言等证据(人称“环境证供”)为依据而决定了案件的结局。对此,笔者颇感有些问题值得思考。
一、“世纪争产案”综述
早年投身香港房地产业并成为亿万富豪的王德辉曾两次遭遇绑架。首次绑架发生于1983年4月13日至19日,其妻龚如心向绑匪支付1100万美元赎款后最终获释。1990年4月,王第二次遭绑架,龚于当月14日交付6000万美元赎款,但丈夫未能安全回家,其后绑匪被捕归案,供称早将王投入公海。
龚如心从此成为华懋集团最高首脑。沉寂数年后,她于1994年起大规模进行房产收购,短短数年,令华懋集团资产大增。由于王德辉的失踪, 1997年引发了其父王廷歆与其妻龚如心争夺遗产的“世纪大战”。
王德辉曾于1960年、1968年在律师见证下订立两份遗嘱。首份遗嘱将其财产平分予妻、父,并称若与妻有子嗣,则妻所继承遗产系以信托人方式代子女持有。1968年,王在第二份遗嘱中改变初衷,指明其父为遗产唯一继承人及执行人。王廷歆正是依据后者,要求继承儿子资产。
本案的关键证据是龚如心于1999年9月提供给法庭的一份遗嘱。遗嘱共4页,以中文写在4张牛皮纸上,每页均有王德辉本人签名,并有王家当时的管家谢炳炎的见证签名。遗嘱3页内,均声言将所有财产留给爱妻龚如心,而在第二、第三页上则表达了王对自己父母、兄弟姐妹的“失望”以及对龚如心家人的“讨厌”,禁止龚将遗产分与他们。最后一页上,则仅有王对龚的一句表白“one life one love”(一世爱一人)。
对此遗嘱原告王廷歆(王德辉之父)则认为是龚如心伪造,并立即报警称龚伪造文件。而遗嘱见证人谢炳炎虽声称亲见王德辉在遗嘱上签名,但谢在开庭前离港后在内地病逝,无法出庭作证,仅留下书面证词支持龚。
为赢得官司,原告王廷歆专门从美国、加拿大各请一位专家分别对该遗嘱进行笔迹鉴定,香港警方也委托本地一笔迹专家进行鉴定,都一致认为“谢炳炎”的签名并非谢本人所写;而对于“王德辉”的签名则分别作了“并非”、“很可能并非”、“可能并非”王本人所写的结论。而龚如心委托的是中国刑警学院贾玉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物证鉴定中心徐立根教授和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詹楚材研究员,这三位均是国内文检鉴定领域的顶级人物,人称内地“铁三角”。三位专家共同出据了遗嘱上“王德辉”、“谢炳炎”签名均是其本人所写的肯定结论。
然而,尽管如此,令人遗憾的是,2002年11月,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主审法官在长达500余页的判词中指出,双方有关遗嘱真实性的举证各有各理,且笔迹鉴定本身并无绝对科学标准。在此情况下,法庭决定采信“环境证供”——王德辉对父母孝顺,并无原因突然憎恨父亲,修改遗嘱将父亲排除在受益人以外;且王德辉生性严谨,断无在遗嘱中自曝隐私的可能(庭审中,双方曾各曝对方隐私)。同时,在法庭颁布的判词中,提出1990年3月12日的遗嘱(龚如心提供的遗嘱)有9大疑点,如该遗嘱并非由律师办理、遗嘱的用字有可疑、遗嘱没有推翻1968年遗嘱(原告王廷歆提供)的条文、遗嘱见证人谢炳炎的证供可疑、王德辉不会用近乎无墨的墨水笔签遗嘱等,由此法庭得出该份遗嘱是伪造的结论,龚遭败诉。2004年6月,高等法院上诉法庭3名法官以2比1又裁定龚上诉失败。直至2005年9月16日,香港终审法院才判决龚如心上诉成功。但终审法官们认为,由于双方笔迹专家对该遗嘱签名真伪各存疑问,不能构成一致压倒性结论,据此推断遗嘱伪造,仅是一种无法证明的“阴谋论”。终审法官认为,谢炳炎尽管未能出庭作证及接受盘问,但其生前提供的证供前后一致,指自己曾亲见王德辉在1990年3月12日的遗嘱上签字并要求自己作为见证人,证词清晰无可置疑。据此,终审推翻原判,裁定龚如心胜诉。随之,龚如心所受到的“伪造、行使假遗嘱、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等三项刑事指控也得以被香港律政司宣布撤销。
如此看来,本案龚如心所以能胜诉,似乎与遗嘱上的“王德辉”、“谢炳炎”签名笔迹鉴定无关。但纵观全案的审理过程,在一、二审阶段,中、外专家围绕遗嘱上的“王德辉”、“谢炳炎”签名笔迹鉴定之争,始终是案件的争论焦点。只不过到终审阶段,法官们抛开了笔迹专家的鉴定结论,采信了谢炳炎的证词等“环境证供”才了结案件。
上述情况使笔者不禁产生了以下猜想:假如鉴定结论无关紧要的话那为何在一、二审阶段双方当事人下了那么大的力量对笔迹进行鉴定?如果“笔迹鉴定本身并无绝对科学标准”这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在其它所有物证鉴定领域是否存在绝对科学标准?本案双方笔迹专家对该遗嘱签名真伪确实“各存疑问”,“不能构成一致压倒性结论”吗?法官采信笔迹鉴定结论在双方鉴定专家存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必须要“构成一致压倒性结论”才可采信吗?本案不以鉴定结论为主要证据而以一个已不在世的人的言词证据为主要证据来证明遗嘱的真实性,这样的采信方式是否科学可靠?我们应如何看待笔迹鉴定的科学性?如何对笔迹鉴定结论进行科学有效地审查判断?……。弄清这些问题或许会对今后的司法实践有一些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对本案相关问题的一些个人浅见
(一)对本案遗嘱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是辩明遗嘱真伪的重要途径,也是最佳途径
案情所示:本案的关键证据是龚如心于1999年9月提供给法庭的一份遗嘱。遗嘱共4页,以中文写在4张牛皮纸上,每页均有王德辉本人签名,并有王家当时的管家谢炳炎的见证签名。而谢炳炎虽声称亲见王德辉在遗嘱上签名,但谢在开庭前离港后在内地病逝,无法出庭作证,仅留下书面证词支持龚。
这些情况表明:本案检材(有争议的签名)为多份,并且为两个人各有四个签名,数量较多,可供鉴定的笔迹特征必然较多,因此鉴定中对检材特征规律的把握性和可比性一定较强。这比平时笔迹鉴定中常常遇到的少量字的鉴定相比难度应当不是很大的。而且除笔迹鉴定以外,还有一个已不在人世的在场见证人的证词佐证,因此,选择笔迹鉴定手段来证明案件事实,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也应是最佳途径。然而事实上,本案终审法官却绕开了笔迹鉴定,转而采采信了一个已无法当庭质证的言词证据,这实在令人有本末倒置之感。虽然这其中可能是因为笔迹鉴定在中、外专家之间存在一定争议,但是如果将这些证据及案情分析再与内地专家的资质及所作肯定的鉴定结论来综合评断,其证明力和判决的说服力岂不更强?
(二)笔迹鉴定和其它物证鉴定一样,“本身并无绝对科学标准”,但并不影响其科学性和证明力
但凡研究过笔迹学或接受过笔迹鉴定专业知识培训的人都应知道:笔迹作为人类书写活动的一种客观文化载体,是有其客观实在性、个体特殊性、客观反映性和书写规律的可认知性的。笔迹学原理认为,人类的书写活动是在其生理机理和心理机理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当人的书写动作链形成以后,每个人就会形成自身独特的笔迹特征,而这就为笔迹鉴定进行同一(或不同一)认定提供了可能。但是由于笔迹在形成过程中所受到的主、客观因素影响较多,使得具体的笔迹形态可能产生较大的变异,而这也就为笔迹鉴定带来了一定难度。也正是这个因素使得笔迹鉴定与其它检验门类相比主观分析的因素较多(如法医伤情、指纹识别、人相识别、DNA鉴定等)。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在实践中不同鉴定人对于同一检案,由于采用鉴定方法、手段和思维分析方法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鉴定结论。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否认笔迹鉴定的科学性,因为笔迹学研究还表明,一个人的书写动作链一旦形成,若想人为改变几乎不可能,受客观环境因素影响也好,摹仿他人笔迹也好,都不可避免地会保存自身固有的习惯特征。只不过这种习惯特征要通过一定量的笔迹特征来表现而已。因此,我们也绝不能因笔迹鉴定主观分析因素较多这一点来完全否定笔迹鉴定的科学性,更不能因为中外笔迹鉴定专家存在意见分歧就以“笔迹鉴定本身并无绝对科学标准”为理由而否认其科学性。否则,如果连高等法官们都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笔迹鉴定,如果大多数人们都这样认为,那笔迹鉴定这门物证技术的存在意义就值得探讨了。
本案原审法官在判词中,提出了“笔迹鉴定本身并无绝对科学标准”这样的论断。这或许是终审法官避开笔迹鉴定转而采信言词证据等“环境证供”的重要原因。是否存在这样的标准?如果说“笔迹鉴定本身并无绝对科学标准”这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在其它所有物证鉴定领域是否存在绝对科学标准?笔者以为,在物证鉴定领域,每一门鉴定门类都有其理论基础和操作标准(或规范),但绝对的科学标准是不存在的,因为人类包括对自身在内的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是在不断摸索中前进的,以往被人们认为是正确的、科学的东西,可能到现在可能又被我们认为是错误的。现在我们认为是正确的、科学的东西可能在未来又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也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规律。以物证鉴定来说,任何一项标准都是人为制定的,人在制定标准时必然要受一定的主观思想支配和客观因素影响,因此不可能不犯错误,也就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程度。如法医伤情鉴定,虽然各类伤情都有一系列的详细标准,但在实践中为何也会出现基于同一伤害事实不同鉴定人会作出不同的鉴定结论。其它如物证痕迹鉴定、指纹鉴定甚至于DNA鉴定,虽然客观性指标较多,但谁又能保证百分之百的鉴定准确率呢?至于说笔迹鉴定虽然在检验形式上与其它鉴定门类有所差别,也没有一个可供比照的具体标准,但仅凭此就称其“本身并无绝对科学标准”显然是不公正的。相信真正了解笔迹鉴定的人也不会产生这样的评判。
(三)正确认识本案中、外笔迹鉴定专家的意见分歧
由于本案金额巨大,判决结果影响深远,故双方聘请的专家都是国内、外顶尖的笔迹鉴定专家。本来,依正常情况,对于本案检材的鉴定是不应该出现相反结论的,但事实上却出现了这样的结果。究其原因,是外方专家不了解中文汉字的具体写法和特征规律,过分强调机械比对,而忽视对检材、样本特征的辩证分析。众所周知:中文汉字的书写与外文书写有很大区别,其章法结构复杂,蕴含的文化信息相当丰富,如果不懂汉字的书写规律,不懂中华文化,就不能全面掌握其中的各种信息。而这样的人对汉字笔迹进行鉴定,只能通过表面所见的有限特征,机械的比对来作结论。可想而知,这样的结论会有多大的可靠性。相反,就以为本案作鉴定的众多内地笔迹专家来说,他们都是学者、教授级的人物,对中华文化及汉字笔迹的研究都有很深的造诣,是本领域的学术带头人。这样的资深专家所作的鉴定,并且是三名专家共同的结论,如果没有权威性,那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而且继贾教授等三位笔迹鉴定专家之后,内地一批具有颇深资格的笔迹鉴定专家又分别赴港对该遗嘱签名鉴定进行了复核,也都得出了完全相同的鉴定结论。这足以说明内地专家的鉴定结论是科学的,是可以作为主要证据使用的。
三、笔迹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
我国《民事诉讼法》将鉴定结论纳入七种证据之一,但又规定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是对鉴定结论的程序性要求,也说明必须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判断。而实践中应如何进行审查判断,法律上并无具体规定。但本着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审查判断鉴定结论,尤其是笔迹鉴定结论应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采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要审查鉴定人的鉴定资格、鉴定能力和鉴定水平。
鉴定资格是鉴定人具备鉴定知识和技能并获得认可的法定条件,也是首要条件,而鉴定能力和鉴定水平是鉴定人的能力条件,也是至关鉴定人信誉和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因此,审查判断鉴定结论,首先要审查鉴定资格、鉴定能力和鉴定水平。
本案中,中、外鉴定专家的资格、水平应当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外方专家一点中文知识都不懂,甚至连汉字怎么写都不知道,从这一点来说就不具备对中文汉字的笔迹鉴定能力,因此,其鉴定结论的可信度首先就应大打折扣。
其次,要审查鉴定方法手段是否科学,鉴定理念是否正确。
从中、外笔迹鉴定的检验原理上说,都应遵循书写动力定型和笔迹形成特征规律原理。但在具体操作上,从本案反映情况看,中、外专家在方法手段上是有区别的。我国内地专家采用的表象分析与内在原因相结合的辩证分析方法,而外方专家则采用了表象分析与机械比对的方法。在鉴定理念上,我国内地专家遵循的是“不为钱做事,只为科学结论服务”、“行业声誉至上”等原则。而外方专家是否也遵循了这样的原则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其从事鉴定工作30多年,曾办过多起大型案件的经历上看,在本鉴定中似乎不应坚持与我国内地专家相反的鉴定意见,但事实上却如此,我们不能不想象是利益和金钱发挥了作用还是论证方法出了差错?
第三,要结合案情,综合分析,合理解释双方争议焦点,果断采信正确的鉴定结论。
笔迹鉴定结论是建立在对笔迹特征的准确发现、客观分析、合理解释基础之上的,实践中由于情况的复杂性,不同鉴定人出现相反的鉴定意见是正常的。但是经过争论,专家意见在多数情况下也是能够达成一致的。如果达不成一致意见,作为法官或者案件承办人,可以通过争议双方说理充分程度、持相同观点专家的人数、解释疑点合理性等多方面因素来准确判断哪一方的鉴定结论是正确的。还可以通过案件中的其它证据来佐证哪一方的鉴定结论更有证明力。
本案中,坚持完全否定结论的只有外方专家一人,其余两位也只是部分否定或可能否定,而我国内地专家三人从始至终都是一致的肯定结论,更有后来我国内地许多笔迹专家的复核意见也都对肯定结论给予支持,这从人数上就已占了绝对优势。并且贾教授还出庭作证19天,对本方鉴定结论进行了全面、详细论证,向法庭解释了种种提问。再从案情上看有谢炳炎证言佐证,终审法官对谢炳炎证言的真实性也进行了客观分析。因此,无论哪一方面说,我国内地专家的鉴定结论是客观属实的。但令人遗憾的是,终审法官们还是未予采信。
综观全案,依笔者看来,终审法官们判决龚如心胜诉,如果全部抛开笔迹鉴定结论,则只需适用普通法的“举证责任倒置”这一条也就够了。而若要使判决更具说服力,就应当将经质证理由更充分正确的鉴定结论与现存的“环境证供”相结合来综合判断,这样才更加符合唯物辩证思维的科学精神。
四、对我国笔迹鉴定工作改进提高的几点建议
从本案的笔迹鉴定过程、最终结果及专家出庭作证的情况看,虽然我国的笔迹鉴定总体水平在国际上早已处于先进地位,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国笔迹鉴定领域在某些方面还存在需进一步改进提高之处。
1.在我国司法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和与国际接轨日益紧密的大趋势下,鉴定人出庭作证已难于避免。因此,有关管理者和领导机构应重视对鉴定人在这方面素质的培养提高。如加强培训与交流,适时、适当地搞一些模拟性出庭作证等。
2.利用多种方式,加强对笔迹鉴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从根本上克服实践中某些鉴定人存在的拜金主义和功利思想等;
3.在笔迹鉴定领域普及推广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如计算机统计分析技术、图像处理技术、网络传输技术、演示示证技术等,努力从形式到内容上不断改进鉴定工作,努力提高鉴定工作质量和水平,提高鉴定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综上所述,香港“世纪争产案”证据采信情况,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问题和思考,也令我们看到了在笔迹鉴定领域存在的一些需改进提高之处。本文所提出的观点及认识因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