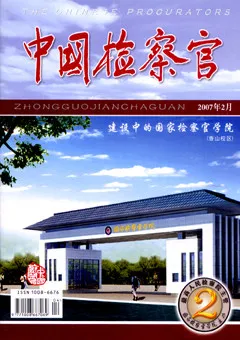二审检察员出庭之法律地位
内容提要:出席二审法庭的检察员首先应是一种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以审判监督的眼光来审视全案,在此前提下来决定是否继续支持公诉,或是支持辩护意见,辩解理由或上诉理由,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关键词:二审检察员 公诉人 法律监督
2005年8月2日下午4时许,被告人吴务光、吴务荣俩兄弟来到一网吧,碰见被害人叶某,吴务光与叶某因琐事发生争执,后吴务光持刀刺中叶某左胸,吴务荣持刀刺中叶某左小腿,致叶某死亡。尸检报告证实,叶某系被锐器刺伤胸部,致心脏破裂,因心包填塞、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两被告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两人均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检察院没有抗诉。
本案有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物证、书证、鉴定结论等证据予以证实,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符合“两个基本”的要求,但本案仍存在以下争议焦点:
第一,持刀杀人的故意是谁提起的
公诉机关的起诉书认定是吴务荣提议的,一审判决也认定是吴务荣提议的,但吴务荣一直予以否认并供认是其哥吴务光提议的,吴务光有过一次吴务荣是犯意提起人的供述,但随后包括在一审庭审中都供述是自己提议的。证人文晓峰有两份证言,第一次证实是吴务光提议的,第二次证实是吴务荣提议的。证人曾勇证实是吴务荣提议的,而在一审庭审中吴务光和吴务荣均对此均提出异议。
第二,对两被告人是否要区分主从犯
公诉机关建议对两人不区分主从犯,一审判决也没有区分主从犯,对两人都判处死刑。吴务荣上诉时提出致命伤不是其所刺,自己只是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不应判处死刑。
一、二审检察员出席法庭履行职务的法律地位
对于本案,出庭检察员在法庭上该如何发表意见,是支持公诉机关的意见,抑或支持上诉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正当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这就涉及到一个检察员在二审法庭中履行职务的法律地位问题。
(一) 二审检察员出席法庭法律地位之分歧
关于二审检察员出席法庭履行职务的法律地位问题,长期以来理论界、实务界均有很大争议,认识尚不统一,这也是束缚二审检察员出庭履行职务的瓶颈之一。目前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检察员出席二审法庭不再具有公诉人的身份,而只有法律监督者一种身份,行使法律赋予的审判监督职责。他们认为无论是上诉案件还是抗诉案件,二审审理的都是一审尚末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其解决的是一审判决是否正确的问题,这就要求二审检察员根据法律规定对一审判决确认的事实及审判程序是否合法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提供合议庭评议时参考,而不是站在公诉人的地位对下级检察院的起诉书进行评价。第二种观点认为,检察员出席二审法庭的法律地位因当因案而异,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上诉二审案件,检察员出席法庭仍然负有支持公诉与审判监督双重任务,他的法律地位仍是国家公诉人;对于抗诉二审案件,检察员出席法庭的任务只是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他的法律地位是法律监督机关的代表。他们的理由是上诉案件虽然一审程序结束了,但由于上诉人的上诉,案件的审理还没有结束,上诉的直接表现是不服一审判决,但也对公诉意见提出了辩解和异议,因此公诉任务并末完成,应该在二审中继续支持公诉。而抗诉二审案件则不同,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是由于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有错误,其针对的是一审判决而不是被指控的一方,因此其不再具有公诉的任务,检察员出席法庭是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提出抗诉意见,通过二审使案件得到正确审判。第三种观点认为,检察员出席二审法庭与出席一审法庭的法律地位一样,其仍然是国家公诉人,仍然担负着支持公诉和执行审判监督的双重任务。他们认为不仅上诉案件需要继续支持公诉,在抗诉案件中,抗诉虽然是针对一审判决和裁定提出来的,但其与被告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二审所做出的判决或裁定都要从被告人身上体现出来,特别是对于重罪轻判的抗诉,就更具有支持公诉的性质。因此他们认为不论是在上诉案件中还是在抗诉案件中出庭检察员都具有支持公诉和审判监督双重任务,但在上诉案件中侧重于继续支持公诉;在抗诉案件中侧重于实行审判监督。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中关于二审出庭检察员具有支持公诉和审判监督的双重任务的看法,但认为在二审中应以审判监督为主线,以继续支持公诉为辅,其法律地位应作为一种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出现,因此不适合再称之为国家公诉人。《刑事诉讼法》将出席二审法庭的检察人员定义为检察员而不是公诉人,并不仅仅是称呼的改变,还应有其实质的内涵。二审的设立就是为了及时纠正一审的错误,使案件得到正确的判决,因此二审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而不是简单重复一审的工作。对于出席二审法庭的检察员来说,在法庭调查阶段,需要查清案件事实以决定是否要进一步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在法庭辩论中,不仅要评议抗诉理由以决定支持哪些、撤回哪些,还要评议上诉理由和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对正确的予以肯定和支持,对无理的进行批驳,更要对一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评议,以决定是否提出改判意见。因此二审是对一审的全面的评判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检察员应对全案有一个客观的了解和把握,本着公平、正义的执法观在法庭上发表意见。可见,出席二审法庭的检察员首先应是一种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以审判监督的眼光来审视全案,在此前提下来决定是否继续支持公诉,或是支持辩护意见、辩解理由或上诉理由,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二)本案的适用
根据笔者的上述观点,受理本案后,笔者仔细阅卷并提审了上诉人,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1. 庭前与主审法官进行意见交换
积极与主审法官取得联系,告知我们阅卷后的基本观点,主要是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吴务荣为犯意提起者证据不充分,相关证据之间的矛盾得不到合理排除,二审中应对这一情节进一步查实。由于证人文晓峰提供过两份证言且存在矛盾,申请通知文晓峰在二审法庭中出庭作证,证人曾勇的证言在一审中受到两上诉人的当庭质疑,辩方提出重大异议,也应通知其出庭作证。同时我们积极联系证人文晓峰和曾勇出庭作证事宜,曾勇初步同意出庭。
2. 参与法庭调查,积极进行讯问、询问和当庭质证
在二审法庭上,检察员就有争议的问题详细讯问了两上诉人,上诉人吴务光仍供述是由自己提议的,上诉人吴务荣也说不是自己而是其哥吴务光提议的。在对证人曾勇进行询问时,其仍证实是听到吴务荣首先提议的,为证实是否属实,检察员建议让证人和两上诉人当庭对质,经对质后,双方仍坚持各自的观点。而证人文晓峰则没有出庭作证,且没有说明具体原因。
3. 发表检察员意见,表明立场
经过二审的法庭调查,本案的事实和证据状况都已很清楚了,审视全案,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检察员发表了如下意见:一是证人文晓峰在前后证言相矛盾的情况下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根据相关规定,其证言不能采信。关于上诉人吴务荣是否为犯意提起者,各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得到合理排除,一审判决认定吴务荣是犯意提起者证据不充分,属认定事实错误。二是不能认定吴务荣是犯意提起人,被害人致命伤不是吴务荣所刺,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一审判决不分主从犯不当,吴务荣关于自己系从犯的上诉理由应予支持。三是对上诉人吴务荣量刑畸重,根据其在本案中的地位和作用,应减轻处罚,吴务荣关于量刑畸重的上诉理由正确,应予支持。四是一审判决对两上诉人的定罪准确,对上诉人吴务光的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两上诉人其他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4. 列席审判委员会,听取审判意见
根据省人民检察院和省高级人民法院会谈纪要达成的有关协调机制,检察员随同领导列席了审判委员会,听取了审判委员会对该案的讨论意见,审判委员会上基本同意检察员的意见,认为认定吴务荣是犯意提起人证据不充分,不能认定;根据本案案件和证据情况应认定吴务荣为从犯;一审对吴务荣量刑偏重,可改处12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上诉人吴务光维持原判。
通过以上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本案有对公诉的支持,但更多的、贯彻始终的还是对一审判决的审判监督。为查清本案事实,检察员申请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在法庭上积极讯问、询问和组织证人与上诉人当庭对质,在此基础上发表了认定吴务荣为从犯,对其减轻处罚的检察员意见,对上诉人的正当上诉理由给予了支持,这是履行审判监督的职能的必然要求。同时关于两上诉人的定罪和吴务光的量刑问题,检察员又明确支持了公诉意见和一审判决,对不合理的上诉理由予以了驳斥。可以看出这两种意见并不矛盾,是在全面审视本案证据和案件情况下作出的正确选择,是对本案客观、公正的评判,因此审判机关对这些意见也基本予以采纳。
二、立法建议
在司法实践中,不论是上诉案件还是抗诉案件都会出现上诉理由、原审被告人辩解或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有些确实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公诉意见不一定完全正确的情况,这时如果片面地强调支持公诉,就会使出庭检察员面临一种尴尬的局面。当然这与个人对法律的理解有关,但与法律本身的不完善也不无关系。目前的《刑事诉讼法》第15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一审法庭的任务是支持公诉,从而明确了出庭人员在一审中国家公诉人的法律地位。虽然该法第188条规定,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和二审法院开庭审理的公诉案件,同级检察院都应派员出庭,但没有明确出庭人员的法律地位和作用,从而导致了理论界的争议和实践中的不同做法。
为此,笔者认为应一步加强二审检察员出席法庭履行职务法律地位的立法研究和探讨,对《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的规定进一步明确,早日确定检察员在二审中法律监督者的地位,才能使出席二审法庭的检察员充分发挥其作用,切实履行好审判监督的职能,进一步做好支持公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