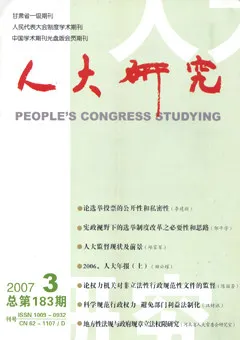业主维权、政治参与与城市基层民主的前景
业主是通俗的称谓,明确地说业主是指自有住宅的所有人,从法律的角度也可称之为财产权利人,业主维权行为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作为财产权利人的法律权利。但是若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业主维权行为就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政治学界对这种行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发,认为这种行为关联到中国的现代化、和谐社会的建设、稳定的社会秩序、民主政治的发展、基层社会的架构、基层公共治理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其中,政治学专业人士最关心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景。一般的政治学常识告诉研究者们,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础是广泛而且有实质效果的政治参与,大部分公民有比较积极的参与态度,参与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投票表达自己的偏好从而影响政治选举和政治过程。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率一直很高,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壮大使得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在下降,甚至政治冷漠有蔓延的趋势。
近年来,全国一些主要城市住宅社区发展速度相当快而且规模日渐庞大,以北京和深圳为代表的业主维权活动经常发生,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有的学者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乐观地认为业主维权必将大大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然而,要判断业主维权与民主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必须对基层社会的诸多影响因素有全面的了解才可以进行客观的评论。
当前,业主维权的案例已有不少,然而业主们的维权行动是否促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促进了多少?曾经参与或主导维权行动的业主有多少成为政治参与人士?业主维权能否成为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增长点?根据目前有限的经验和观察,对其现实价值和意义恐怕不容乐观估计。
第一,维权人士考虑的主要是私人利益,尽管其中带有公共性的成分、有为社区业主服务的理念,但是最终还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在历经波折获得成功之后,多数参与者便不再参与与自身利益之外的其他事务。即便未能取得效果,多数情况下也只能考虑以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而不会转化为一种政治诉求。即使诉诸政府部门、人大或者政协等机构,解决问题的难度依然很大,他们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十分有限。有观点认为,经历业主维权后,会表现出“作为有产者的业主们极大的政治激情和行动能力”,认为“业主群体参选(人大代表) 背后是经济变革带来的私有财产的确立以及社区形态的出现”,“他们在捍卫财产权的过程中很自然地产生了寻求政治渠道的诉求,经济变革与政治演进连为一体”。 其实仔细推敲一下便会发现这个观点存在问题:事实上业主们维权首先想到的不是政治渠道,而是法律手段,是与开发商、管理处斗法;其次,即便有个别业主冀图通过政治渠道来影响规则,他也必须想办法进入公共政治层面,或者通过影响有政治身份的人物来加以干涉。纵观北京、深圳业主参选人大代表的案例,可以知道能够由维权业主转变为影响公共政策的政治参与者是极个别现象。
第二,维权人士分属不同的单位和职业,物权以外的利益无法统一,而且他们的利益目标即使能拢和也是短暂的。维权活动是业余活动,带有自愿的性质,甚至还要牺牲一些私人利益、需要有所付出。他们的活动也是非职业化的,参与维权也只是短时的。徐勇在比较城市社区和农村自治的环境时说:“虽然城市社区自治发展的环境比较宽松,但与村民自治相比,也面临社区参与不足的问题……在城市,居民的经济利益与其工作单位密切相关,与社区的关联不直接。在缺乏经济利益的牵引下,城市居民对于社区公共事物缺乏足够的参与热情,这在公共意识较为薄弱的现阶段中国,尤其突出。”
第三, 维权人士最初只具备各自专业领域的知识,与物权、维权有关的知识是在参与的过程中逐步学习领会的,逐步掌握了一些技巧,知道如何依法维权,对法律内容的钻研及其精神的领会是比较深刻的。相比之下,业主们维权时所表现的对法律的尊重、对法律的精通,超过了房地产商、物业公司乃至政府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倒是物业公司和开发商经常性地曲解法律、践踏法律。
而对于政治性参与,维权人士们显然缺乏相关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也显示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对政治性参与抱有一种戒备心理。所以,他们极少会将维护社区公益的热情转化为政治参与的热情,也很少考虑通过政治参与来彻底维护自己以及更多人的权益。由于政治体制的封闭性,他们知道进入政治领域并非易事,而且那些身处政治体制之内的人们也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政府部门的监管软弱无力、司法过程的冗长繁琐也使维权人士们失去对政治的信心。他们身上所显示的政治冷漠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
第四, 单位社会对社区政治氛围的形成也是一种障碍,使基层民主难以在社区中得到生长的机缘。业主们主要的社会政治活动基本上是在单位中发生完成,而社区里的活动参与者主要是老年人和家庭妇女。他们由于知识的限制、身体健康的因素等不能很好地参与社区维权,也不可能从事政治性的参与活动。要培养社区的民主意识,必须将单位社会中的政治功能转移到社区里,使业主们能从参与社区公共事物中培养民主意识和参政经验,从而有个别人成长为具有现代政治知识和参政技能的政治活动人士,关注更大范围乃至全国性的公共事物。
第五, 社区的住宅功能也限制了基层民主的发展。现在的小区主要是住宅社区,承担的社会功能、政治功能相对要少。住宅区域内的事物毕竟有限,业主的权益并不限于小区之内,而是延伸到了小区之外。业主们的诉求指向一个大于小区的区域社会,这是一个由医疗保障、教育设施、生活购物、图书馆、体育馆、派出所等内容构成的公共服务体系。这些问题就不是一个住宅社区的参与可以解决的。如果说政治参与的目的主要是对公共事物的发言权,那么基层民主的单位范围就不能局限在住宅社区里,而应该是一个“公共服务体系区域”,一个范围较大的功能社区。因此,社区的概念就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了。一般来说,住宅区域的自治,即业主委员会的社区治理是不太难实现的,但是超越住宅小区的“区域自治”难度就大了很多。小区事物也许不是什么政治问题,但是“区域公共事物”就一定是政治问题了。显然,基层民主的生长点究竟是落足于“住宅小区”还是“区域功能社区”就需要讨论。“住宅小区”是私人利益的集中地,“区域功能社区” 是公共利益的集中地,参与时所关注的问题自然有差别。
当然,业主维权可以为一些有理想的人提供一个训练参政能力的场所,但是政治参与者并非一定要从社区业主中产生,其他任何领域都有产生的可能,也都能获得参政的经验。上述几点说明,市场经济是否能成为政治民主化的前提或者推动力值得进一步探讨,但是一个开放的体制下所形成的自由空间才是促进政治参与的真正且惟一的前提。业主维权之所以能够在各地展开,是因为宪法规定了城市居民自治的权利;而维权之所以艰难是因为目前对物权的规定和保障还不明确,从而被开发商和物业公司(甚至还包括政府主管部门)割裂了业主自治的空间。
通过观察业主维权、业主参选人大代表的一些案例,我们也能够欣喜地看到当前体制下参与者的活动空间在扩大,这个体制也试图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下为参与者创建一个平等的政治平台、提供平等的参政机会,政治参与活动中所揭示的问题促进了规则的改进,这是以业主身份参与竞选所产生的不可忽视的贡献。住宅小区和维权业主的出现,说明市场经济使得社会结构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然而市场经济只是促进体制开放、逐步扩展自由空间的诸多因素之一,所以若依据开放程度来判断城市基层民主发展的前景,还是不容乐观。
(作者系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