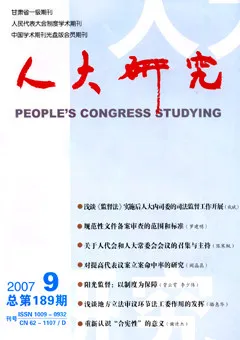重新认识“合宪性”的意义
在宪政时代,“合宪性”成为政制生活的一项基本原则。根据宪法对立法、行政、政党行为及国家政治运作中其他特定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制度始创于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马伯里诉麦迪逊判例,在1920年奥地利的立宪中得到发展,二战后众多国家通过宪政改革纷纷采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达到高峰。伴随于宪政的发展,合宪性审查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宪政实践机制[1],已为百余个国家所采纳,成为“宪政制度最显著的特征”[2],并不断彰显其深刻的时代意义。而今,合宪性审查制度走过两个世纪的历程,其间所展示的发展态势及蕴含的历史规律,对于我们领会“合宪性”在宪政建设中的意义是有益的。
一、世界性发展及渐进过程
合宪性审查的制度实践自19世纪初生成之后,便不仅在美国,而且逐渐在世界范围得到了发展。一方面,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交流与互动的空前扩展,美国的制度模式(司法审查模式)为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丹麦、瑞典、印度、智利、洪都拉斯、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60多个国家所采制;另一方面,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摩尔多瓦、马其顿、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南斯拉夫、斯洛伐克、捷克、韩国、泰国等纷纷创制奥地利的制度模式(宪法法院审查模式),合宪性审查的历史走出跨越性的一步。如今,越来越多国家通过宪政改革创建这一制度,“合宪性”作为一项基本的宪政原则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我国近年来对合宪性审查的强烈呼声同样回应了这一世界趋势。
然而,这一世界性趋势并非一蹴而就,长达两个世纪的历史昭示着一项宪政制度的生成、实践与成熟所需要的渐进性——这一过程遵循了事物发展“曲折而前进”的一般进路。就以美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发展为例,伴随显著的公共认同与域外影响,它成为当今世界的典范,然而,在美国,合宪性审查首先不是一个结论,而是一个过程,该制度世界性发展的诸多品性在这一过程得到展示。
首先,它是一部宪政思想史,在思想碰撞中发展。在美国,制宪会议期间便围绕这一制度的确立与否展开过激烈论争,因意见分歧较大而未能在宪法中予以创制。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的论证堪称经典:“无疑,所有那些设计成文宪法的人们都将其设想为形成民族的基本与首要的法律。因而,所有这类政府的理论一定是,一项与宪法相抵触的立法法律是无效的,这项理论在本质上和成文宪法相联系,因而被考虑为我们社会的基本原则。”[3]然而,合宪性审查的思想共识并未就此形成,马歇尔的意见遭到以吉布森大法官为典型的诸多诘难[4]。尽管如此,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历程并没有因此停滞,合宪性逐渐成为包括美国在内多数国家宪政生活中的重要理念。时至今日,在美国,合宪性审查被视为司法部门在政府体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基础;在世界范围,合宪性原则最终得到普遍认同,合宪性审查制度被作为宪政制度的一部分加以继承,而且至今也没有任何东西驱动人们去拒绝它。
其次,它也是一部宪法判例史,在实践探索中发展。在美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构正是通过一系列宪法判例逐渐完成的: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判例确立联邦最高法院宣告国会立法违宪的横向审查权,维护了权力分立制衡与法治主义的宪政精神;1810年弗莱切尔诉派克判例确立对州立法违宪的纵向审查权,1816年马丁诉亨特的承租人判例进一步确立关于各州立法违宪问题上的统一审查制度,以此维护了联邦主义和法制统一的宪政精神。在世界范围,诸如日本最高法院1966年积极维护合宪性的全国邮电工会东京中邮判例、法国宪法委员会1971年保障人权的结社自由判例等。显然,如果没有合宪性审查的世界性实践,“合宪性”也难以成为今日人们政治生活的重要原则。
二、专门化发展及权威品格
伴随世界性发展,合宪性审查呈现另一种态势,即制度的专门化发展。1920年奥地利创设了由专门的宪法法院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制度模式,这一模式在二战后的欧洲和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亚洲得到迅猛发展。宪法法院审查模式的出现与普及,使得合宪性审查成为宪政体系中具有系统性、独立性的一项制度。同时,在采制司法审查模式的国家,合宪性审查制度的专门化发展同样得到体现,从美国之后几乎所有国家是通过宪政改革将合宪性审查加以制度化并确立该制度的专门性。到了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在世界范围已形成普遍共识:合宪性审查成为宪政国家不可缺少的制度,它的作用和意义越来越变得不可替代。
合宪性审查的权威品格在这一过程不断获得提升。无论在采制宪法法院审查模式的国家,还是采制司法审查模式的国家,合宪性审查权威的集中化倾向都相当明显。例如,在法国,宪法委员会对议会两院的规章在施行之前行使具有决定意义的合宪性审查权;在日本,基于1969年阻止下级法院行使审查权的“平贺信函事件”,合宪性审查的分权化特征逐渐减弱,最高法院行使着终极的审查权。这种权力集中运作的倾向孕育着合宪性审查权威性的增长。实际上,两种合宪性审查模式殊途同归,其终极价值都在于维护宪法的权威,实现宪政的意义,难怪乎有学者指出,“合宪性审查不能分而行之:或者可以分散于一个统一的法院系统内——倘若整个体系都在某个单一最高法院的终局权威之下的话,或者必须使其着落于一专门宪法法院。”[5]故而在分权化的合宪性审查体系中,务必要求能够确保此种“权威”品格的配套因素存在。在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美国遵循先例制度对于调和不同主体合宪性判断之差异的意义,也不难理解日本宪法第八十一条直接设定最高法院享有终极合宪性审查权的内在缘由了。
三、模式分化与价值融合
制度背景和文化差异使然,各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及其历程各显特征,合宪性审查发生模式分化。在美国,马伯里诉麦迪逊判例只是一个契机和标志,深层原因在于其独特的文化背景与历史条件,立宪前司法审查实践雏形早已存在,又深受分权理论、自然正义理念、清教思想和普通法优越思想影响,并最早展开立宪政治,这些因素都是欧洲大陆国家所不具备的。法国在1902年和1925年,德国在1925年,意大利在1947年都曾试验过司法审查模式,结果乏善可陈[6]。在法国,历史上的1799年宪法和1852年宪法就设立“元老院”专门审查法律是否与宪法相抵触,1958年宪法确立宪法委员会合宪性审查制度,1974年扩大审查提议主体为内容的改革使宪法委员会开始发挥积极作用,逐渐显示了合宪性审查集中运作的适应性和制度合理性。作为特定制度与历史、社会、文化因素的综合物,如前所述,合宪性审查历史发展的转折性轨迹集中展示为二战之后的模式分化:审查主体的司法机关与宪法法院之异以及审查权力的分散与集中配置之别,它以二战后世界范围的宪政重建为契机和宪法法院审查模式的广泛采制为标志。
然而,模式分化并未阻止价值追求的趋同性以及彼此的交融发展。尤其上个世纪后半期以来,不同模式以及不同国家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之间日益形成一种互动效应:制度原理趋同,模式界限有所减缩,彼此借鉴、吸收和交织发展,合宪性审查制度变得更具开放性、包容性。无论是司法审查,还是宪法法院审查,都基于合宪性控制原理以及宪政、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而运作,有学者指出,“现代人类就是尝试集合不同法系之英知,想将这问题谐和:‘合宪性’之理念于制度,予以处理;亦即确认不必遵从违反宪法之法律和命令之权利。”[7]在任何国家,合宪性审查制度总是在规律性与特殊性的共同作用之中发展。例如,日本在二战后受美国影响导入司法审查模式,植根于大陆法系文化之中,其实际上的合宪性审查基于观念、制度与文化的诸多因素而颇具兼容性、开放性,“日本的实际做法最终还是表现出明显的特色,例如分权化的合宪性审查到1975年就名存实亡,最高法院实际上一直在发挥宪法法院的作用;但却并没有采取抽象性审查的方式,而是通过具体诉讼案件的判决进行部分问题的审查;另外,审查的重点从立法转移到防止行政权力侵犯人权的方面;在整体上倾向于司法消极主义,等等,似乎介于美国模式和战后德国模式之间”[8]。
实际上,合宪性审查作为一种有效的宪政实践机制,模式的差异并未妨碍其功能共性的发挥和普遍价值的实现。一般来说,每种法律制度都蕴含着普遍的价值观念、社会需求和由人类公共体验的经验法则,合宪性审查制度的交融发展正是体现了人类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追求。“人类对不公平、不合理、反自然、反人道的法律和命令的不服从和排拒,是人类努力奋斗不息的恒久问题”[9]。这一人类为之努力奋斗不息的“恒久问题”便是不同合宪性审查模式之间价值融合的根源所在。它们共同追求一种“合宪性”,实现公平、正义、民主、人权,实践宪政的意义。因此,模式分化乃至国别差异固然不可忽视,但合宪性审查的价值共性更值得关注,因为,那是人类普遍的价值共识和观念认知,凝聚了人类历史发展与制度文明的结晶,我们没有理由将之丢弃,对于这一制度所秉持的“合宪性”精神,我们没有理由不予继承发扬。合宪性审查不仅仅作为一个历史结论,它更是一场正在推进的宪政运动,其制度构造的价值时至今日已广为认同,制度运作理念也渐获共识,“合宪性”业已成为当代宪政建设中的应有之义。
四、宪政性与现代意义
合宪性审查制度总是伴随于立宪政治与宪政民主的历史进程。它在美国的起源与美国近代立宪政治息息相关,它的世界性发展更是与现代立宪主义紧密联系,二战带来的“宪政反思”和战后的“宪政革新”是其制度与理念拓展的关键。它以维护宪法的至上性为直接出发点,宪法也成为其制度合法性与权力运作的根据,这与19世纪以来的宪政主义有很大的历史联系。合宪性审查回应了宪法成文化、宪法刚性化、宪法效力至高性和宪法的可保障性(宪法司法化)等意义,捍卫了“自然正义”和“真正的法”。其实,早在远古时代,亚里士多德就启发人们对违反“自然正义”的法律和命令拒绝服从,西塞罗则明确指出不得企图背离“真正的法”是人类立法的一项神圣义务[[10]。由于显著的宪政属性,合宪性审查被考虑为宪政社会的基本原则加以实践,其理论逻辑便在于:保障合宪性,落实宪法精神,防止法治与民主运作偏离宪政轨道,实现宪政的价值与意义追寻。两个世纪以来,合宪性审查已深深烙上了宪政的品性。
随着宪政的发展,这一宪政实践机制日益彰显了它的时代意义。如果说,“立法的发明是人类曾有过的成就之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成就,是立法最大限度地将人类命运交到了人类自己手中”[11];那么,在现代宪政语境下,则是合宪性审查,最大限度地确保将人类命运交到了人类自己手中,并在最大限度上尊重人类自身的尊严。现代社会,民主与人权作为宪政的核心主题,深刻凝聚着人类自身的尊严,它们不但是合宪性审查的原动力并作为制度构造的主线,更是其制度运作的价值目标。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权力行为特别是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已成为社会变革以及宪政发展的主要驱动装置。例如,“二战后,欧洲各国重建政治制度,尤为重视保证尊重基本人权。宪法法院的一个个判决,催生了人们对宪法和基本人权的尊重,这种尊重以前就根本没存在过……和二战以前的情形相比,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一转变无人能够逆转。”[12]又如,德国旨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诉愿制度以及保障政党行为民主性的政党合宪性审查制度由于功能显著而逐渐成为现代意义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模板”。近年来,我国法学界以“齐玉苓受教育权案件”、“非典时期的知情权问题”、“孙志刚事件”等法律事件为契机强烈呼吁合宪性审查,更是着眼于这一宪政实践机制在宪政民主与人权保障方面的意义。
合宪性审查所孜孜追求的,正是通过保障此种合宪性来实现宪政的意义,它对于处在宪政发展中的中国尤为重要。尽管今天看来,在理论上呼吁建立中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似乎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但是,这决不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事实上,无论从制度建设还是从理念培养的维度审视,摆在我们前面的路途依然漫长。
参考文献:
[1]谢进杰、石静、王斌:《作为宪政实践机制的合宪性审查》,载《行政与法》2005第11期。
[2]E.S.Corwin. Judicial Review[J].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Vol.8).1932.
[3]【美】保罗·布莱斯特等:《宪法决策的过程:案例与材料》,张千帆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4]北京大学法学院司法研究中心编:《宪法的精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0年经典判例选读》,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5页。
[5][12]【法】路易·法沃斯:《欧洲的违宪审查》,载《宪政与权利》,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75、54页。
[6]Mauro Cappelletti. The “Mighty Problem” of Judicial Review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Comparative Analysis[J]. So.Cal.Rev.(53).1980.
[7]李鸿禧:《违宪审查制度之异质移植》,载《违宪审查论》,元照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409页。
[8]季卫东:《合宪性审查与司法权的强化》,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9]【日】佐藤功:《宪法的保障》,载《日本宪法体系》第1卷,有斐阁1968年版,第181页。
[10]【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11]【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77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