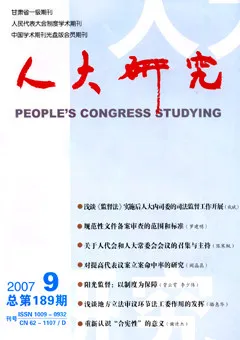《新民主主义论》并未初步形成理论形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研究毛泽东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具有重要的文本与实践价值。毛泽东何时首次提出“人民代表大会”概念,这似乎不成问题。理论界、学术界一般认为: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提出“人民代表大会”概念。由此推论:毛泽东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已初步形成理论形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然而,我们通过追本溯源的考证与分析,发现上述观点是一种基于版本原因得出的错误结论。
一、《新民主主义论》没有提出“人民代表大会”概念
众多著述指出: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最早提出“人民代表大会”概念。如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这一光辉论著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一个崭新的概念”[1]等等。其实,我们通过对各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及《新民主主义论》单行本的内容比对,可以得知:《新民主主义论》并没有提出“人民代表大会”概念。
问题主要产生于《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段话:“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字体下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用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与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2]确实,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的各版本毛泽东著作中出现“人民代表大会”概念之处。问题是,新中国建立后,在出版毛泽东的著述时,原文经过了若干改动。据考证,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做了三次修改,分别是1940年2月、1942年春、1952年4月[3]。新中国建立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及单行本《新民主主义论》都采用1952年经毛泽东修订的内容。那么,我们必须弄清,《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这段话是否经过了改动?回答是肯定的。正是毛泽东在第三次修改时改动了这段话。
1940年1月,毛泽东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发表了演讲。2月,该文以相同标题发表于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同月,延安《解放》杂志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标题发表。自此该文正式以《新民主主义论》行世。事实上,1952年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各根据地、各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或单行本《新民主主义论》这段话都没有出现“人民代表大会”概念,原话均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国民大会、省民大会、县民大会、区民大会直到乡民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用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与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4]与此相印证,谢觉哉在1945年1月27日的日记中引用了毛泽东这段话,除个别技术性的错漏外,也完全与此一致[5]。可见,《新民主主义论》中并未提出“人民代表大会”概念,它是毛泽东1952年改动而来的。
顺便说明,既然《新民主主义论》不享有“人民代表大会”概念的“首创权”,那么据笔者现所掌握的资料看,“首创权”当由《论联合政府》享有。《论联合政府》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最高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6]我们进行了认真核对,这段话中“人民代表大会”概念在建国前后各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及单行本《论联合政府》中都是一致的。
二、《新民主主义论》并未初步形成理论形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52年,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内容做了改动。那么,原有“国民大会”等概念与改动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概念之间,仅仅是文字表述上的不同呢,还是涉及实际含义的差别?如果是前者,那仅仅涉及“人民代表大会”概念的形成时间等;如果是后者,那就涉及理论形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形成时间等重大问题。兹事体大,不容不辨。
有人认为,毛泽东对其已发表的著述进行改动,往往只是一种不涉及原文思想内容变化的技术性改动。这种认识值得怀疑。举例说,建国前夕,毛泽东对苏维埃代表大会有了新认识:“‘苏维埃’代表大会。我们过去又叫‘苏维埃’,又叫‘大会’,就成了‘大会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7]根据毛泽东上述精神,建国后在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过程中,凡出现“苏维埃”字样,均作了改动。如将“苏维埃”改为“我们”,“苏维埃政权”、“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改为“政权”、“红色政权”、“民众政权”,“苏维埃代表大会”、“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改为“工农兵代表大会”,“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工农共和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等等,这些都反映了毛泽东乃至整个中共对革命政权有了新的重要认识,而不只是“技术性改动”。应当看到,毛泽东1952年对《新民主主义论》的多处改动中,既有涉及文字语气、标点符号、语法结构等技术性改动,又有关涉概念置换、内容修正等实质性改动。而将“国民大会”等概念改动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概念,明显属于后一类改动。
第一,从制度名称和基本内容看,抗战初期与中期的毛泽东继承了孙中山《五权宪法》与《建国方略》政体制度构想。孙中山将西方代议政体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相结合,为未来中国政治发展设计了蓝本。孙中山认为,中国政治发展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以县为自治单位,国民得选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选举议员以议一县之法律;凡一省全数之县都实行自治,则省为宪政开始时期;全国有过半数省份达到宪政开始时期,则召开国民大会颁行宪法。可见,在孙中山设计的基层地方自治与中央五权分立的政体制度架构中,国民大会具有显著意义。1929年,国民党政权公布《乡镇自治施行法》与《区自治施行法》,对乡民大会、区民大会的地位、职权作了法律规定;1936年,国民党政权颁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该法规定国民选举代表组成国民大会,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等,国民大会拥有创制、复决、修改宪法及宪法赋予的其他职权;省设省参议会,名额每县市一人,由各县市议会选举之;县设县议会、县政府,由县民大会选举之;市设市议会、市政府,由市民大会选举之[8]。由于缺乏制度运行的生态空间,也由于国民党政权“以党训政”的政治取向,国民大会等政体制度仅停留于文本层面,并未在中国现实运行。可以看出,无论从制度名称,还是制度的文本设计看,毛泽东与孙中山、国民党政权所提出的“国民大会”等制度是基本相同的。但有两点区别:毛泽东强调在民族危亡的抗战时期,相关制度“现在”就“可以”落实;在制度适用层次上,毛泽东则作了灵活与周密的调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倡导“中国现在可以采取的”政体制度是对《五权宪法》《建国方略》设计蓝本的理性回归,是对国民党政权现实政体制度的超越。但并未表述理论形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二,从毛泽东政体制度思想发展脉络看,抗战初期与中期的毛泽东客观理性地认同现实国民党政权政体制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民族矛盾超越了阶级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民族主义的情境下,中国社会政治格局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权再次走向合作,两党主导的政体、政治制度也由对峙走向趋同。由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政党体系中相对较弱一方,毛泽东主张在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区域放弃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推动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政体制度向国民党政权政体制度靠拢,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等政权目标。抗战前后毛泽东政体制度思想的变化,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一种价值不断向现实的妥协过程。1937年,毛泽东说:“国民大会要是真正代表人民的,要是最高权力机关,要掌管国家的大政方针。”[9]1938年,毛泽东认为,三民主义共和国“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除犯罪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护之……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这样一种国家,就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10]1939年,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11]1940年,“三三制”在陕甘宁边区与其他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1937年至1940年期间,毛泽东还倡导“三民主义共和国”。可见,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强调“国民大会”等完全符合他在当时的政体制度思想。
第三,从1940年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政体制度实践看,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政权建设没有出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践。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国民大会”等概念相当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概念,那么,我们很难解释一个文本与现实的悖论:为何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主张“中国现在可以采取”,但迟至1948年才在华北解放区出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奏与雏形[12]?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国民大会”等并不相当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在1940年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政体制度实践中,各抗日根据地始终实行的是参议会及“三三制”政体制度。毛泽东自己对此态度非常明确。1942年,毛泽东说:“不要把这里(指陕甘宁边区——笔者注)的参议会看成只是本区的参议会,而要把它看成所有华北华中各根据地的参议会的领袖。”[13]1944年12月,谢觉哉建议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更名,毛泽东回信说:“参议会改名,关涉各解放区,中央尚未讨论,请暂不提。”[14]事实上,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在1940年至1945年仍处于对未来政体制度形式的探索中,正如谢觉哉日记中所说:“新民主主义政体毛主席已给了原则的指示——民主集中制,但具体形式,究与其他民主国会相反或还有些近似,则有待于研究。”[15]
第四,从“人民代表大会”版与非“人民代表大会”版《新民主主义论》对比看,“人民代表大会”概念体现了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新认识,反映了毛泽东建国前后、尤其是建国初期的制度设计构想。1952年,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一文进行了较大的改动。这次改动吸收了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很多新看法、新思维,摈弃了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抗战特定时期的某些特定提法,契合了建国前后国内的政治形势与意识形态。如删去了“作为觉悟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就是各种革命的政党,其中主要的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一句;将“建立中国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改动为“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16]等。1952年的改动总趋势是更突出了对中国社会阶级本质的分析,强调了工人阶级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淡化了资产阶级与国民党的政治作用,彰显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如此背景下,毛泽东将其建国前后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构的设想带入改动实践中。建国初期,毛泽东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的适当形式。1949年,《共同纲领》确立了法律形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1年,斯大林建议中国共产党尽快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2年,毛泽东开始考虑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问题。明白这样的国内政治背景,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毛泽东对“国民大会”等概念的改动了。补充一点,在《新民主主义论》的那段话下,毛泽东接着说:“‘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与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与国体不相适应。”[17]“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一语,取自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这大概有助于我们理解“国民大会”等概念的真正含义。
可以说,毛泽东将“国民大会”等概念改动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概念,这透露出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思考、新解释,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以后来标准来诠释往昔事实,得出非客观与非科学的结论。历史事实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并没有初步形成理论形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三、《新民主主义论》在政体制度层面的价值考量
正如亚里士多德说:“政治(政体)研究……第一应该考虑,何者为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素质。第二,政治学术应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望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好政体。第三,政治学术还该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并研究这种政体怎样才能创制,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于久远。”[18]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所提出的“国民大会”等政体制度仍有重要意义,这主要体现于其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若干政体制度原则。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原则。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主权在民”取代了“主权在君”,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西方代议民主制度即为其理论的制度化形态。毛泽东吸收西方政治文明的精华,逐步提出国家一切权力归属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并将其改造为政权建设的根本原则。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19]在制度具体设计中毛泽东提出,中国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人民选举国民大会、省民大会、县民大会、区民大会、村民大会等,由国民大会及地方大会选举各级政府。应该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充分体现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思想。但是,《新民主主义论》中并未明确指出“人民”的内涵与外延,也没有过多论述人民的民主权利与民主制度设计。部分缘于此,我们说,《新民主主义论》并没有初步形成理论形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民主集中制是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原则。《新民主主义论》承继了毛泽东一贯的民主集中制思想。民主集中制范畴,最先是指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而后逐渐推演到政权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性质国家政权机关的一种重要组织与活动原则。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论述苏维埃政权问题时,将“民主集中主义制度”称为“新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等;在江西瑞金,中国共产党人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苏维埃代表大会;1937年7月,毛泽东说“政府如果是真正的国防政府,它就一定要依靠民众,要实行民主集中制。”[20]《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这种民主集中制政府,才能充分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并明确说:“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21]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将民主集中制与政体联系起来,是毛泽东政治实践中积极探索民主集中制的新认识。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相对于根本原则,民主集中制是一种浅层次的原则,是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22]。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并未设想出未来的国家的政体,但毛泽东已充分认识到未来国家政体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所以特别强调民主集中制,甚至将其与未来政体等同。顺便说明,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民主集中制。学界关于我国政体是民主集中制观点既违背逻辑推理事实,也不符合政体运行实践。事实上,在毛泽东的语境中,民主集中制有多种含义,既可指国家政治制度、政党组织原则,又可指政府工作作风、国家结构形式等。
总之,《新民主主义论》为后来毛泽东理论形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初步形成提供了理论储备,它对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政体理论探索具有重要意义,是毛泽东国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需特别指出,1945年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受到了其极大的影响,明显汲取了其思想养料。《论联合政府》首次提出“人民代表大会”概念,标志着毛泽东理论形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初步形成。
四、简短结论
正确结论基于精准的材料,原始版本对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至关重要。由于原版难觅,有学者早已指出:毛泽东著作可出两种版本,一为最后改定本,供学习宣传;一为原版本,或录有历次修订的版本,供理论与学术研究。这是非常必要的。正是透过版本的迷雾,我们才认定:建国后毛泽东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概念代替了原来的“国民大会”等概念。《新民主主义论》没有提出“人民代表大会”概念,并未初步形成理论形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注释:
[1]参见万其刚:《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1期。
[2]、[9]、[11]、[16]、[17]、[19]、[20]、[2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347、563、672、677、677、347、677页。
[3]参见方敏:《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修改》,载《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6期。
[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编印1940年版,第19页。
[5][15]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47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7页。
[7]《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8~1309页。
[8]缪全吉:《中国制宪史资料汇编》,台湾国史馆1991年版,第547~563页。
[10]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
[12]参见杨建党:《华北人民政府时期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之考察》,载《人大研究》2007年1期。
[13][1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7、249页。
[1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76页。
[22]参见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作者系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外政治制度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