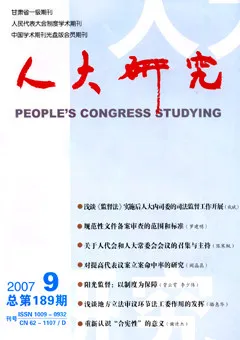浅谈《监督法》实施后人大内司委的司法监督工作开展
《监督法》颁布实施后,人大的内务司法委员会(或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如何做好司法监督工作,是人大内司委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新任务。通过学习《监督法》,笔者认为,目前人大内司委的司法监督工作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一、监督权的主体是常委会,人大内司委的司法监督工作实质上是协助常委会做好司法监督的具体工作
《监督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行使监督职权。 第五条进一步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实施监督。由此可见,《监督法》明确规定监督权的主体是常委会。对于专门委员会是不是监督权的主体,《监督法》没有规定。按照公法领域内法无明文授权就不能为的原则,专门委员会应当不是监督权的主体。《监督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常委会执法检查工作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具体组织实施。因此,从《监督法》来看,专门委员会是监督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部门,并不是监督权行使的主体。但是,专门委员会和有关工作机构是受人大或常委会委托,从事有关监督工作的具体事项,并在一定的监督程序中发挥作用。对此,必须明确认识,这是内司委开展司法监督具体工作(以下简称内司委的司法监督工作)的前提,也是探索和实践内司委司法监督工作新思路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内司委开展司法监督工作就必须创新思维,运用《监督法》赋予的新方法、新手段进行。
二、内司委的司法监督工作可分为三块进行
《监督法》共9章,其中第二章到第八章分别规定了7种监督手段及具体程序,即: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听取报告)、计划和预算监督、执法检查、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询问和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从这些规定来看,可由内司委具体组织实施并发挥作用的手段,主要是听取报告和执法检查这两项,而这两项恰恰是长期以来理论和实践界讨论并践行的人大监督工作的两大块,即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其中听取报告一般被认为是工作监督,执法检查一般被认为是兼有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双重属性。此外,多年来,一些地方人大的内司委还接受人民群众反映的涉法涉诉问题和案件,并转交“两院”处理。对这种情况《监督法》没有规定,但在有关说明和释义中,认为这不属于人大常委会集体行使对“两院”工作的监督职权,属于处理涉法涉诉的信访工作,这样做是可以的,《监督法》对此可不做规定。因此,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内司委的司法监督工作目前主要可分为三大块进行,一是听取报告,二是执法检查,三是处理信访。
1.听取专项工作报告是开展司法监督工作的手段
听取“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按说是司法监督工作的一种老办法、老手段,但是过去对于听取报告这种监督形式缺乏明确的规定,听取报告基本上是听得多,说得少;肯定成绩多,指出问题少;审议泛泛而谈多,事先了解情况少;听完转交意见多,跟踪落实少。与以往不同的是《监督法》针对这些情况,赋予了听取报告这种方法以新的内涵。对此,《监督法》第二章第八条至第十四条作了具体规定,形成了一套完整、周密的程序。第八条规定了听取报告的选题范围和向社会公开的原则。第九条规定了确定选题的6个来源。第十条规定了听取报告前进行先期调研这一程序。目前一些地方在操作中,把先期调研的时间确定为最迟在常委会听取报告前的一个半月前进行。第十一条规定了常委会听取报告前,将调研意见汇总,交“两院”研究并在其报告中作出回应。第十二条规定“两院”的报告要在常委会会议举行的20日前向内司委征求意见,并在修改后于常委会会前10日送交常委会。第十三条规定了报告人是谁。第十四条规定了“两院”对常委会的审议意见,必须处理并在征求内司委或有关工作机构的意见后,向常委会书面报告反馈。常委会还可以对专项工作报告作出决议,“两院”应当在决议规定的期限内,将执行决议的情况向常委会报告。
目前,参与《监督法》草案起草的一些成员、全国人大的专家学者撰文把听取报告定性为一种类案监督,就是开展对“两院”的工作评议。因此,《监督法》实施后的听取报告和《监督法》实施前的听取报告在法律上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如果在工作中严格按照《监督法》的规定去做,工作量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工作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监督的力度只可能加大,而不可能削弱。
2.执法检查是开展司法监督工作的重要形式
《监督法》肯定了执法检查这种监督形式,并进一步规范、明确,以加强执法检查工作。《监督法》第四章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七条对执法检查的内容和程序作了规定。但从这些条文来看,执法检查这种监督形式在内容、程序和具体操作等方面与听取报告这种监督形式大体上是一致的或近似的。《监督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执法检查的选题范围和第八条规定的听取报告的选题范围是一致的,同时第二十二条还规定参照第九条(即听取报告确定选题的6个来源)确定执法检查的选题。而第九条第一项规定的听取报告确定选题的途径,就是“执法检查当中发现的问题”。因此,从《监督法》来看,目前,听取报告和执法检查这两种监督形式,实际上都不单纯是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而是都兼有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两种特征,是两种特征的混合,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
《监督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执法检查组提出的执法检查报告必须包括“对有关法律、法规提出修改完善的建议”。这个看似过细的规定,在以往是不明确的,也是容易被忽视的,过去的一些执法检查报告往往缺失这一重要内容。因此,这一规定是区别执法检查与听取报告两种形式的一个标志。但是,从总体上看,执法检查与听取报告的区别界线并不十分明显。根据《监督法》的规定,在听取专项工作报告当中,也很难不涉及“一府两院”的执法情况,所以,听取报告决不单单是工作监督,执法检查也不单单是法律监督。这也给人大内司委(或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在安排一年的工作时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如何妥善安排好内司委的工作量,即向常委会提出听取报告和执法检查的建议时,要根据精力和时间,统筹安排,提出有关内务司法方面的报告或检查,由常委会听取或进行检查。无论是听取报告还是执法检查,均不宜安排过多,以确保集中精力搞好检查、听好报告。此外,由于《监督法》没有明确规定专门委员会可以单独进行执法检查,专门委员会进行的执法检查实际上应该以常委会的名义进行,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执法检查。所以,专门委员会在年初安排工作时,不能再安排以专门委员会名义进行的执法检查,只能安排类似于常委会执法检查的“执法调研”,但是这种“执法调研”也不能多,以确保集中精力,具体组织实施好有关内务司法方面的常委会听取报告和执法检查。
对于以专门委员会名义听取的有关部门的报告,可以做适当安排,但也不宜多。从这种报告的性质来看,应该属于有关部门的工作汇报,但由于专门委员会并不是监督权行使的主体,其实质是属于专门委员会进行的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因此,专门委员会的“执法调研”,可以与以专门委员会名义听取的有关部门的报告结合起来进行,以使对某一方面的工作或执法情况调查研究得更深入、全面。
3.处理信访是开展司法监督工作的经常做法
如前所述,本文所讲的内司委的司法监督工作是指内司委协助常委会开展的司法监督的具体工作。多年来,内司委作为人大的专门委员会之一,对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反映的涉法涉诉问题、或者常委会分管副主任批示的群众反映的涉法涉诉问题,转交“两院”依法处理,作为启动“两院”内部监督机制的一个渠道,起了积极作用。这种工作不但很具体,而且是经常化的。但是这被一些专家学者称为“个案监督”,笔者认为这是不对的。这种做法并不是由人大常委会集体行使监督权,涉法涉诉问题和案件也是由专门委员会转交“两院”依法处理,并不附加任何意见,因此,这实际上并不是“个案监督”,而属于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
这种日常性的工作并不违背《监督法》,也符合现实情况的需要,应当继续做好。目前,一些省级人大常委会根据工作需要相继成立了信访局,如何处理好与信访局在这项职能上的交叉关系,是人大内司委在工作上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规范的问题。笔者认为,内司委不能把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拒之门外,但也不能全部大包大揽,否则与专门委员会的职能是违背的,可以考虑进一步规范有关工作程序,除将信访转交“两院”等有关部门外,有些也可以转交信访局,由信访局具体督促办理。信访局也可以将一些涉法涉诉的信访,通过常委会的分管秘书长或一定的程序,提交内司委研究、提出法律方面的意见,按照《监督法》第九条的规定,为常委会确定听取报告和执法检查的计划提供参考。同时,也使人大的涉诉信访工作与《监督法》衔接起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得到符合《监督法》的规范化处理。
(作者单位:山西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