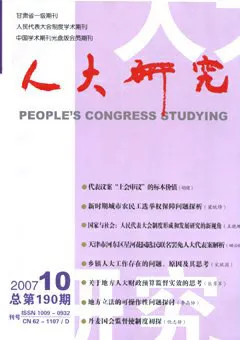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据权威部门的统计资料显示,自1998年以来,环境纠纷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递增,光是2006年仅投诉到环保部门的环境纠纷就达40多万件[1]。但是这些纠纷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的比例却低得可怜。由于坚持运用法律武器反对环境污染在实践中遭遇法律制度障碍,加之缺乏相关配套制度建设和维护公益的国民素质及诉讼意识做支撑,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发展态势非常低迷。以下是2000年以来颇具影响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2000年12月30日,300名青岛市民以经过青岛规划局批准的在音乐广场北侧建立住宅区的做法,破坏了广场的景观,侵害了自己的优美环境享受权为由,将市规划局告上了法庭,一审败诉;
2001年10月17日,东南大学法律系施建辉、顾大松两位教师以观景台的建设破坏了“其享受自然景观所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为由向南京市中院起诉市规划局,要求其撤销对紫荆山观景台的规划许可,法院未予受理;
2002年6月,杭州农民陈发庆以行政不作为将余杭区环保局告上法庭,认为环保局没有对制造粉尘、噪音的石矿企业进行处理,法院判决驳回起诉,2003年12月陈发庆又以同一事由将浙江省政府和浙江省环保局告上法庭,法院不予受理;
2003年2月,杭州律师金奎喜向杭州市西湖区法院起诉市规划局,要求撤销老年大学项目许可证以保护西湖景区名胜,法院不予立案;
2005年12月6日,我国著名法学家贺卫方等6名北大师生就松花江污染事件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环境公益诉讼,但至今无果。
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05年,全国曾发生了多起具有轰动效应的环境权公益诉讼案件,但这些被视为“典型公益诉讼”的案件无一获得胜诉,最后的结果不是不予受理就是被驳回。于是,自2003年以后就很少看到这种公益诉讼了。倒是无极剧组破坏西双版纳景致事件及“圆明园湖底防渗漏工程”得到令人欣慰的行政处理,环保斗争中诉讼途径遭此冷落, 实属一个法治社会的悲哀!也是中国环保的悲哀!在目前的法律体制下,环境公益诉讼就如暗夜里微弱的星火,几乎不能让人看见希望,纵然也可能引起一定的轰动效应,但它是否能够长期持久仍然充满变数。要想使其成星火燎原之势,有必要修改现行法律,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做好相关配套制度建设。
(一)相关法律制度的修改和完善
1.修改相关法律规定,拓宽环境诉讼的原告及诉之利益的范围
为避免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三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制约和诉之利益的限制,建议在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设专章或者在《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尤其要明确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受理条件、诉讼范围、审判程序,赋予任何公民、团体以及国家机关以环境诉权,并将诉之利益扩展到人身、财产以外的美学、景致和生活舒适等利益。
有学者担心过分扩展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和诉之利益会导致滥诉、诉累并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主张把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限制为国家检察机关,只给公民和团体踊跃参与和举报申诉的权利[2]。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就我国国情而言,人们没有西方“好讼”的传统。即使在本人利益受到侵害时,也往往倾向于非诉讼方式解决,因而不可能热衷于为与本人利益无关的问题而打官司,更不要说面对绝对强势的污染企业,胜诉几无定数。公益诉讼不是经济人行为而是社会人行为,是一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在市场经济中,社会人是相当稀缺的资源。所以“实现公益诉讼制度不会带来‘诉累’和‘滥诉’,即使将来国人有了提起公益诉讼的积极性,那也是值得庆幸的事,根本用不着为此忧虑。”[3]
尽管以上“根本用不着”的结论可能有点武断,但不可否认我国公益诉讼要从今天这种凤毛麟角的局面发展到“诉累”的地步尚需相当时日,过早地考虑预防“诉累”反倒不利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即使有一天确实发生滥诉,完全可以通过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和判例解决。正如美国,其环境公益诉讼已经由无人问津的起始阶段发展到成熟的“诉累”阶段,所以通过判例限制原告资格以防止滥诉。
2.修改诉讼法中有关规定,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独特的诉讼费缴纳制度
我国诉讼费依据诉讼标的额实行累进制,虽然法律规定败诉方承担诉讼费用,但一般情况下,原告应预交诉讼费。实践表明,该规则使公益诉讼特别是集团诉讼在我国越发没有生存空间。在诉讼标的额较大(环境公益诉讼通常都是如此)的诉讼中,当事人要向法院付出高昂的费用。另外,公益诉讼的原告不是为了或都不只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如果要对所有诉讼标的额缴纳诉讼费,就是让他替真正的(或者其他的)权利主体承担诉讼风险。这是不公平的。在走向法治的时代,减少诉讼费用事关民众对法院以及法律的态度。法院收费高昂,当事人望而生畏,将愈发加剧民众畏诉、厌讼的心态(虽然有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缠诉、诉累),势必使通往正义之路愈来愈窄,妨害依法治国战略的实现。在美国,联邦政府对诉讼提供巨额财政补贴,法院只收取微不足道的讼费,对绝大部分“贫困当事人”都是免交讼费,而且美国联邦法院一律是按件收取受理费,从来不考虑争议金额。这显然很利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启动。
为了鼓励和支持公益诉讼,现在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一是诉讼费用保险。保险公司在保险人发生诉讼时,根据职业估算为保险人支付诉讼费用。实质是一定范围内缴纳保险费的人在为个别的保险人之诉讼承担费用。二是成立公益诉讼基金。从每件胜诉的公益诉讼案件的罚金中提留一定比例作为公益诉讼基金,同时,基金会还可以接纳社会捐款。公益诉讼的原告在提起诉讼前可以向基金会申请公益诉讼费用。环境公益诉讼是原告对抗强势实体,风险大、成本高,为更有效地和环境污染抗争,以上两种做法很有借鉴价值。
3.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只规定了六种特殊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尽管理论界一致认为应在环境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但却无相关法律依据。在实践中,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异常困难,原因是环境污染损害一般是在污染发生一段时间后才会显现,废水、废气和噪音变化迅速,等到事后取证时已时过境迁,所采集的样品与污染发生时相去甚远。加上人们普遍缺乏证据保全意识,物证往往受到人为破坏。另外,环境污染侵权作为工业化的产物,往往涉及高科技,而受害者大多没有此类专业技能,加之加害者出于对工艺流程、专有技术保密的需要可能阻止原告取证活动,这都增加了原告举证难度。同时由于发生危害的复杂性和说明危害发生机制的困难性,使受害人对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人是否有过错等也难以举证。所以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应当明确规定,只要当事人能证明损害或损害可能的实际存在,就算履行了举证责任。我国2004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环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这是我国立法的一大进步。
(二)环境公益诉讼的相关配套制度建设
1.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激励机制
20世纪初,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说:“当今法律制度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在实体法上,而是在程序法领域。”[4]21世纪初的我们依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控制污染的直接方法就是停止之诉,但它不能实现原告在经济上的期待,对起诉者又缺乏经济上的奖励。如果只要求人们一味奉献,势必损害他们的积极性。因此在这个领域实行人为的补贴,以保护人们参与的热情。
在这方面,美国的做法很值得借鉴。早在1914年的反垄断法规中,就有损害赔偿三倍化的规定,无论谁(指原告资格)都能向违法者请求三倍于损害的赔偿额。这种惩罚性的赔偿对于滥用权利的大公司是“强制性的教训”[5],法律允许胜诉原告从赔偿金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奖金。当代表集团所属全员的当事人胜诉时,法院有权从该集团所获得的利益总额中提取合理比例作为起诉者的奖赏。这些举措极大地调动了环境公益诉讼者起诉的积极性。
2.加大环保组织的培植力度
环境公益诉讼面对的往往是强势的污染企业或者环境行政机关,单个人很难与之抗衡;因其复杂性、专业性,起诉者须付高成本,承担高风险,耗时费力,普通公民很难胜任,只有培育专业专职的环保组织,才能给环境公益诉讼以有力的组织保证,使该诉讼真正收到遏制污染之初衷。
我国环保组织力量薄弱,目前还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环保组织在民政局注册的门槛过高,限制过严,这都不利于我国环保组织的发展。整个兰州市,在民政局登记的环保组织只有一家:环保产业协会,近年来只做些务虚的工作,面对严重的黄河污染,从未发动过一起公益诉讼。也难怪,中国现有的环境公益诉讼没有一桩是由环保组织发起的。而国外则截然相反。在美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经典案例Storm King一案中,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The Nature Resources Defense Co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