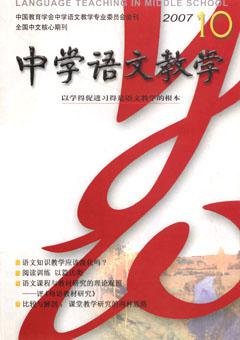反思之后的回归
陈钟梁
一
本世纪开始的短短几年里,可以说是我国课程改革的探索、创新过程中新思想、新理念、新模式层出不穷的时代。“观念”为“理念”所代替,“策略”为“方略”所替代。“结构”变成了“框架”,“板块”转化为“模块”……当然,应当充分肯定这些概念、名词、术语所蕴涵的时代先进性和理论深刻性。马克思曾经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一次新见解,都包括了这门科学术语的革命。”但是,仅仅停留在语词间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任何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及由此应运而生的课程、标准、教材和教学模式、教学方法,都必然有其不完备之处。在其优点充分展现的同时,缺点与不足也会逐步暴露。
几年过去了,需要进行一番认真总结,冷静反思。
二
2004年新春伊始,《中国教育报》曾连续发表几篇文章,提醒正在推进的课程改革切勿把知识与能力对立起来,指出了这种对立的危险性。其中有:
《重视能力:对 轻视知识:错》
《让知识与心灵对话》
《课程改革需要怎样的哲学头脑》
……
其实,这几年语文知识缺位现象在教学中表现日趋严重。读到初三了,学生在修改自己作文时,头脑中丝毫没有动宾搭配得当的意识。高中生全然不知什么是复杂单句,什么是多重复句。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文中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精辟论述的这个长句,近200字,学生根本不知道从何着手分析其中逻辑关系,只能囫囵吞枣。靠眼下语文课常听到的习惯语“整体把握”“用心去体验”“用生命去感悟”,又怎能解决问题?
如果说基层执教老师更关心字、词、句、篇等语文基础知识,那么,学术界比较关注的是有关文章学、文学鉴赏、文学批评以及美学原理等普通知识。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从上世纪最后几年到本世纪初关于知识教学的批评与反思始终没有停息过。继1997年《北京文学》关于语文教学“误尽苍生”的大讨论以后,2005年徐江在《人民教育》2005年第9期发表《中学语文“无效”教学批判》,对语文教学效率问题又一次提出了质疑。
无法否认,当前不少语文课热热闹闹,空空洞洞,知识缺位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课程改革提倡个性化阅读、创造性阅读,可是,支持这些现代化阅读方式的相关知识,却显得有些滞后、过时。课堂上我们常见到的文学欣赏课是:一方面在运用一些令人感到高深莫测的学术话语,另一方面依然陶醉在旧有的知识体系之中。孙绍振教授在2001年发表的《改革力度很大,编写水平太惨——初评新版初中、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一文中说道:“语文教育界关于文学的概念至少落后二十年到五十年。”事实也正是这样,小说除了被拧干了的“人物、情节、环境”三个概念外,好像已经没有多少知识可教了;诗歌在感知、背诵之外,似乎只有体裁(为绝句、律诗,几种词牌名称)、押韵、对仗等屈指可数的而且极为表面的知识;散文,也只有“行散神不散”“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托物言志”等似知识又似套话的几句说法,以不变应万变;戏剧除了“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套路简介,再不见其他知识了。
一方面是知识的匮乏,一方面是知识的老化,这就是当前语文教学在知识问题上遇到的两大困境。
韩雪屏先生在《呼唤语文教育本体研究的回归》一文中说道:“不结实的知识概念体系难以支撑高大的教育理念的框架。华美的理念外衣将终究覆盖不住苍白虚弱的躯体。多年来,关于语文教育的研究,更多的是在观念层面上运转,而没有真正触及语文教育改革的实质——知识的除旧布新。”李海林先生在《评当前语文课程改革的非理性倾向》一文中也谈到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不是要改掉“语文知识”的教学,不是要把“语文知识”本身驱逐出语文教学内容的范畴;恰恰相反,我们需要的是开发新的知识,需要的是一个新的知识观。
韩、李两位专家谈到“知识的除旧布新”,即“知识观”的更新问题,这是一个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十分强的命题。这是一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十分强的命题。上世纪50年代英国著名学者波兰尼在《人的研究》一书中就指出,人类的知识有两类,一类是显性知识、一类是隐性知识,称之为缄默知识。而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96年发布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对知识的形态更作了明确界定:有事实知识、原理知识、技能知识与人力知识四类。前两类知识为显性的可编码的知识;后两类为隐性的只可意会不可编码的知识,也就是缄默知识。当前人们特别关注的正是这种不可言说的缄默知识。在语文学科中,不少一线教师身上蕴藏着大量宝贵的缄默知识。如何开发这份财富,使之用于教学,可能是新时代课程改革需要完成的任务。
语文教学过程中,既重视可编码的显性知识,又 关注不可言谈的缄默知识,才是唯物的辩证的观点。
三
新世纪推进的语文课程改革,无论标准制订还是教材编写,都有“质”的突破;但似乎对原来教学大纲与原来教材的研究不够,对老一辈语文教育家的思想精华汲取也不足。
进入21世纪,在课程改革精神观照下,出现了一纲多本的可喜局面。可惜从人教社到地方的语文教材,编写思路基本相似,皆以主题组织单元,人文性这条线鲜明了,而工具性这条线或隐或现,难以捉摸。这与教材编写思路有关。
以主题为单元编写教材,上世纪30年代就曾经有不少热心人尝试过。1938年,叶圣陶先生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做“既侵犯了公民课的范围,又离开了语文课立场,我不敢苟同”。当然,今天我们的改革,站在时代的高度,不需事必恭听,受到前辈“凡是”的束缚;但必须尊重并研究当年一些语文教育名家的实践经验与精辟见解。
课程标准规定“不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与完整”,这是完全正确的,应重视语文知识的可用性与实效性。但“随文讲解”却令一线教师深感疑惑,“知识随文走”,是否意味着可以把现有的语文知识“零敲碎打”地嵌入课文?那么,会不会因为选用了这篇文章而让学生有机会了解或学习到某些知识;而因为没有选用那篇文章就疏忽、遗漏了另外一些更重要的语文知识呢?语文学科到底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知识内容?有没有学生在多个不同学习阶段必须掌握的最基本的语文知识?语文知识在排列与呈现方式上到底有没有比较合乎实际的程序?这一切,不能不引起广大基层教师,特别是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专家的关注与思考。
在我们充分肯定新世纪语文课程改革的远瞻性、创新性的同时,还应当冷静回顾一下1963年出台的教学大纲。那个教学大纲也是一次不小的思想解放。当时,分管宣传、教育的中央领导陆定一同志来到人教社,问在场的语文编辑:“你们敢不敢只提工具性,不提政治性?”一言既出,四座皆惊。大纲对课文选材的要求,也只有四个字“文质兼美”。在当时政治背景下,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与魄力!
至于为了让学生扎扎实实打好语文基本功,教学大纲提出了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八个字。由于理解与实践偏差,也确实给语文教学带来过一定的负面影响,导致不少语文课嚼得过细过烂,甚至过死。但是,我们看到,为了建立“暂拟语法体系”,我们的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曾经付出怎样艰辛的劳动。志公先生晚年曾经说过:“我不能同意淡化语法的提法。语法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教什么,怎么教。教学大纲表述很精当:好学、易懂、有用。”吕叔湘、叶圣陶两位大师还身体力行,在百忙中整理、编写了《给中学生谈语法》等小册子。这种求实的精神与作风,值得我们后辈学习,并引以为荣。
教学大纲还十分重视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阐述中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语言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志功先生还亲笔写下:“字要端端正正地写,课文要仔仔细细地读,作文要认认真真地做。”叶老曾谆谆教导我们:“语文教育,首先是习惯的教育。”
上海一位90岁老人、著名教育家吕型伟先生不止一次地说:“不是经常听人说吗,老三届的质量还是不错的,这得益于1963年颁布的各科教学大纲,学生在校认认真真读了几年书,扎扎实实打好了学习基础。”
梁实秋曾经风趣地说:“新诗如果不与旧诗搭上界,新诗是没有出路的。”不知能否套用梁先生的话:新时期语文教学如果不与传统语文教学搭上线,新时期语文教学是没有出路的。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学习的革命》一书中的两句话:
我们确定,最伟大的真理是最简单的,最伟大的训诫是最易明白的。
大多数好的学习方法都是常规,但每个孩儿都通过许多这样的方法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