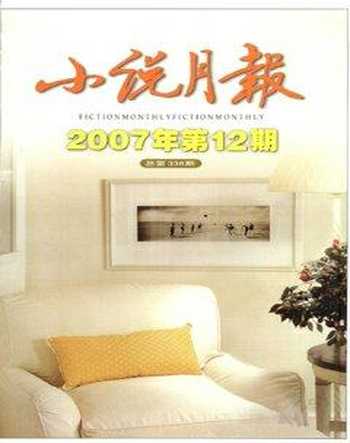东北平原写生集
鲍 十
东北平原写生集(短篇小说三题)
蓝旗屯
到目前为止,关成祥仍然是这一带活得最久的人。他的事情甚至上了县志,上面这样写道:
关成祥,满族,族姓瓜尔佳氏,四有乡对青村蓝旗屯人,1989年9月(县志截稿日)99岁。儿孙已相继早亡,现在同重孙子一家生活在一起。关老汉一生勤劳节俭,从小养成了早起捡粪的好习惯,至今仍未间断,寒冬腊月也是天不亮就起,直到满脸霜花地回到家,不咳嗽不喘,洗脸、吃早饭……
时间又过去十几年,关成祥还好好地活着,活得心平气和,不急不躁。但是若有人问起:“大爷您今年高寿啊?”他则必定回答:“我啊,今年九十九啦。”十几年始终如此,一直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说完朝你一笑。十几年他和从前一样,家里人吃啥他跟着吃啥,从不挑食,也不忌口。而且每天一早就悄悄从炕上爬起来,连灯都不用开,摸黑儿穿好衣裳,推开门,来到院子里,先到茅房去撒泡尿,回头再拎上粪筐,拿起粪叉子,然后慢悠悠地走出院子,来到街上。起初街上还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不过很快就好了,因为天色正在由暗到明,万物也在一点点变得清晰。
他在街上转来转去,搜寻着牲畜们遗留在房前屋后的粪便,这其中有牛粪有马粪有猪粪也有狗粪,发现后立刻叉进他的粪筐,叉得小心翼翼的。就是天不亮也没有什么关系,他照样可以发现他所需要的东西。因为他的鼻子会起作用,他会闻到它们的气味。而且不光鼻子,这里还有个感觉的问题。他的感觉是那么敏锐。他一路走过来,不论是墙角旮旯,也不论是牛粪马粪,甚至还离得好远,他就已经知道了。他就是有这个本事。当然他并不会因此而得意,这件事他已经做了几十年上百年,实在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他也熟悉蓝旗屯,这个自不必说。
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他生在蓝旗屯长在蓝旗屯……对他来说,这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当然,那时候的蓝旗屯绝没有现在这样大,也许只有十几间房子,周围连棵树都没有,孤零零地挤在那儿。记得最清楚的是在房子东边竖着一根高高的木杆,杆头挂着一面蓝色的三角形的旗子,旗子没日没夜地在风中哗啦哗啦地抖动。似乎这也正是蓝旗屯屯名的来历。不过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那时候他爷爷还活着,爷爷总说他是大清国的旗丁,是正儿八经的八旗营里的兵士,因为当年皇上爷选派壮丁垦荒种地,把他派到了这里(每人赏给两头黄牛),而他又是从蓝旗营里出来的,所以才成了蓝旗屯。
照县志的说法,蓝旗屯该是本地最早的屯落之一。
县志还说,清代以来,始终把东北视为“龙兴之地”,对这里实行封禁,禁止汉族进入,因此这里一直是满人(亦即旗人)的天下。后来由于关内地主对土地的兼并和灾荒等诸多原因,汉族流民(山东、河北等省)大规模拥入,当地官员视此情况,不得不数次上奏,要求解禁。自此,放荒买荒租荒以及私垦荒地者渐多,各类屯落也陆续出现……
直到现在,关成祥还能想见那面蓝旗的样子,呼啦呼啦的,没完没了地飘,越飘越有声色。还有他的大嗓门的爷爷,一天到晚,都能听见爷爷站在房子前边吆东喝西,声音传出去好远。爷爷那会儿还不到五十岁,可是已经显出了老相。爷爷身材高大,始终一身旗人的装束,常年穿着一件马蹄袖四开气的短褂,腰扎一条三指宽的板儿带,偶尔出去办事,也会穿一穿那件青色长袍,套着一件黑色的坎肩,看上去干净利落,只是腰有些弯了。爷爷脾气暴躁,尤其是在喝过酒以后,每到这时候,他都要气急败坏地骂人,而且会一直骂到骂不动为止,然后将脖子一缩,立刻呼呼大睡,鼾声如雷。
就在前几天,关成祥还隐约听见爷爷在高喉大嗓地骂人,骂声穿过空旷的岁月,直抵他的胸口。他当即惊醒过来,心扑通扑通地跳着,还出了一身的冷汗。他想爷爷这是怎么啦?难道又喝了酒不成?或者是他没有酒喝,跟他要酒来了?第二天吃过早饭,他就来到了他家的坟地,还特意带了一瓶今年过年关玉柱(他的重孙)给他买来他还没舍得喝的呼兰二锅头酒。他把酒全部倒在了爷爷的坟上,然后在那儿坐下来。他家的坟地如今就在他家的地边儿(承包田),是前几年才迁过来的,而且为了不耽误种地,并没有很大的坟包。但是这儿却埋着自爷爷开始所有已经故去的家人,其中有他的奶奶,他爹他娘,他的哥哥,他的老伴儿,他的儿子和儿媳妇,以及孙子和孙媳妇……因为他们人数众多(他有两个儿子,四个孙子),有的他已经叫不出名字了。
这儿是个安静的地方。虽说前几年在附近修了一条公路,常有各种各样的汽车跑来又跑去,但是因为有庄稼隔着,似乎一点儿声音也听不到,最多能看见它们一闪一闪的,很快就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他以前也常到这儿来,有时候是来干活儿,有时候是没有什么事,专门过来看一看。每到这时候,他都会生出很多的想法,这些想法乱七八糟的,并没有什么头绪,就像下雨天的水泡儿一样,总是很快地出现又很快地消失,快得简直没办法抓住。不过有一种感觉却是一贯的也是明确的,就是觉得他们并没有离开他。他们只是不再吃饭不再干活了,却还在想事儿,甚至还在说话,说起话来还是从前的样子,从前的声音,从前的语调,从前的脾气秉性,一点儿都没有改。
比方说,在他的感觉里,爷爷还是那么愤愤不平,看什么都不顺眼;爹则始终老实巴交的,一说话就吞吞吐吐,生怕惹得爷爷发脾气。说起来,他爹就是这么个人,一辈子活得窝窝囊囊,尤其是在爷爷跟前,说话都不敢大声。爷爷死后他爹有一次说:“这全是你爷爷把我吓的。”爹说他是爷爷最小的孩子,爷爷陕五十岁才生的他,而且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那之前爷爷给关成祥生了十几个姑姑,有的他连见都没见过,据说很小的时候就死去了),即便这样爷爷对他照样不好,抬手就打,张口就骂,后来他爹自己都娶妻生子了,爷爷还是这样对他,真是一点儿面子也不给。那时候爷爷已经七十多岁,打起人来仍然力气不减,还下手极重,不论手边有什么东西,都抄起来就打。爷爷是七十六岁那年死的,他好像得了什么急症,那天白天他还喝了一壶酒,可是当天晚上他就不行了。他爹后来曾经说:“那年头儿,这就算高寿了。”
爷爷死后十几年,他爹也死了。爹死时只有四十岁。关成祥至今记得清楚,那一年是庚子年,那一年家家“跑毛子”。按照县志的说法,那一年应该是1900年。
有好多好多次,关成祥梦见过他爹。其实不光他爹,他梦见过他们所有的人。但是他并不为他们而伤心,这是真的。他知道这是人人都要走的一条路,这他早就想明白了。他只是觉得他们有话要对他说,每个人都是这样。他尽力让他们说,听他们说,跟他们说。他觉得他有这个义务。有时候,他会感觉口干舌燥的,然后醒过来。当然,他们当中有他喜欢的人也有他讨厌的人。比方他最讨厌他二儿子的媳妇,以前他称她为“老二家的”。老二家的没别的毛病,就是胡搅蛮缠不讲道理,另外还爱占点儿小顺宜。如果她想找他说话,他就爱理不理的,有时候还会训她一顿。
这天早上,关成祥又出来捡粪。天色朦朦胧胧的,街上只响着他一个人的脚步声。家家户户都紧紧地关着院门和房门。他一个一个院门走过去,每走过一个院门就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声“这是老赵家”,或者,“这是老钱家”。他知道屯里的每一家,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不光知道他们的现在,还知道他们的过去,知道他们是哪一年到蓝旗屯来的,知道他们在这里经历了多少代,每代都有哪几个人物,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脾气秉性,比如谁老实厚道谁奸懒馋滑还爱偷别人家东西,谁干过缺德事谁行过善事,其中哪些事使他们一辈子没脸见人,以及谁家的男人偷过谁家的女人,他们的事情又怎样在屯子里传来传去,最后如何弄得这个女人喝了农药……
他知道的不止这些。谁家经历过什么大事了,谁家跟谁家哪一年因为什么事打了一架都动了镰刀了,谁家的小子哪一年娶的媳妇、哪一年跟他老子分的家了,谁家在哪一年盖了新房子了,他也都知道的。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都在亲身经历蓝旗屯的种种变故,屯里的事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与此同时,他也亲眼目睹了蓝旗屯由小到大的变化过程,一家变成两家,一间房子变成两间房子,似乎眨眼之间,就变得这么大了,原来只有几户人家,现在都快有一百户了。
这期间有出生的,有死去的,而他还活着。
活着捡粪,捡了粪上庄稼。
要想庄稼长得好,粪肥不能少。
这时候,天色渐渐明亮起来,蓝旗屯的模样也越来越清楚。如今正是深秋,临街的土墙木质的院门以及房子的屋檐都散布着一粒一粒白亮的秋霜,这会儿也看得见了。接着谁家打开了房门,门声在空气中颤动着,很快又有人在街上走动,偶尔还轻轻咳嗽一声。屯子睡了一夜,现在醒过来了。关成祥停住脚,把粪筐放在地上,腾出手抻了抻衣袖。凭感觉他就知道,现在他的粪筐已经满了。抻过衣袖他重新把粪筐拎起来,在手臂上挎好,然后向家里走去。
他走得很慢,一边走一边四处撒眸,看看还有没有牲口的粪便。走着走着,突然看见街边的墙角有件东西,上边沾着一些尘土,还挂了_层霜。拿起来一端详,是一个塑料的物件儿,又圆又扁的,中间儿有条缝,就像冬天卖的柿饼儿。这东西他可从未见过,便想这是个什么玩卷儿呢?在衣襟上擦了几下,擦掉上面的霜和尘土,感觉挺光滑的,这才意识到也许是件小孩子摆弄的东西,于是顺手揣进了衣兜。
关成祥回到家,把捡来的粪倒在后园子的粪堆上,拍着衣襟进了屋。他进屋时关玉柱的媳妇正在忙早饭。玉柱媳妇说:“太爷回来了?咱这就吃饭。”关成祥答应一声,朝他住的西屋走去。随即听见玉柱媳妇提高了声音对着东屋说:“你俩还不快起?太爷都回来了!”
只听东屋有人说:“起来,这就起来!”
关成祥走进屋,脱下外衣,又走出来,洗了手脸。待他做完这些,来到饭桌跟前时,只见关玉柱和关小宝已经坐在那儿。关小宝是关玉柱的儿子,那年不是五岁就是六岁,小东西黑漆漆的,看见关成祥连话都没说。
玉柱媳妇端来了饭菜,大家开始吃饭。快要吃完的时候,关成祥想起了早上捡到的那个东西,走进屋,从外衣兜里取出来,托在手上说:“我早上捡的,你们看看是啥。”
别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关小宝一把抢了过去,他瞪大眼睛说:“呀!悠悠球儿……”
郑官屯
郑官是一个人。
这人名叫郑兰斋,清宣统二年(1910年),他是该县的哨官,手下统领着八十几号弟兄,住在县城东门的兵营里。兵营四周有围墙围着,内有十几间瓦房,人们把这里叫做东大营。那时候,每隔十天半月,就见他骑着一匹矮小的花马,带领兵士们急三火四地拥出了营门,朝城外的什么地方扑去。一见这种情况,行人会立刻纷纷让路,他们知道,这准是哪儿又闹胡子了。
胡子又叫绺子,这是当地百姓对土匪的叫法。
当年匪患成灾。据郑官掌握的情况,仅在本地活动的绺子,就有十几股之多。他们时聚时散,无事则散到民间,一有行动便积聚起来,特别难对付。每股多则上百人,少则数十人。且每股都有报号,诸如“天照应”、‘青山好”、“黑手”、“天帮”、“四海”、“孟团”、“王团”等等。其中最有名的一股报号为“老疙瘩”,人数最多,差不多百十号人,人人手里都有家伙。郑官以前和“老疙瘩”交过几回手,大致知道他们的底细。
这天掌灯时分,郑官得到情报,腊月初十夜里,“老疙瘩”将到本县许大房子屯的许家大院来“做活”,他们的人已经在那儿踩过点儿。
郑官不是本地人,他原籍湖北枝江,说起话来又尖又细,叽里呱啦,十句总有五句听不清楚,背地里常被当地人叫做郑南蛮子。郑官本是一介书生,他原是光绪年间的举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奉调来到本县。当时这儿还没有设县,叫××分防。最初他在分防经历(清代官职名)手下办理文案,后因原来的哨官在剿匪中不幸战死,他才受命领了这个“肥缺”。
郑官这年三十余岁,生得面皮白净,尤其脸上那一双美目,总是饱蕴着浓浓的诗情,经常给人顾盼生辉之感。那时他已经娶妻并生有一女,不过妻女都在湖北老家的父母身边,他家在那儿有一处田庄。虽说他当了哨官,可骨子里还是个书生,平素仍以读书为快事,诗书礼乐,诸子百家,偶有闲暇便手不释卷,且常常不停地摇头咂嘴,回味无穷。现在他独自一人住在东大营一间宽大的房子里,一切琐事都有人照顾,除了公事不得不办,余下的时间他都在读书。他心里很清楚,让他做这个哨官,实在是勉为其难。同时他也知道这个职务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又不傻。
他当然不傻。
情报送到郑官这里时,郑官正在他房里看一本《孟浩然全诗》。孟是他半个乡党,他对他一直特别看重。房里有些冷,炉火已经奄奄一息,他懒得叫人添柴,便将一条棉被裹在了身上。听来人说完情况,他心里不由咯噔一动,不过并没马上说话。他放下手中的书,又借着微弱的灯光看了看皇历,今天已是腊月初九,心想不就是明天嘛!坐着没动说:“我知道了。”
来人等了片刻,见他不再说话,悄悄打个“千儿”,向门外走去。刚走几步,又被郑官叫住了,回头一看,见他将一根手指按在嘴上,先是“嘘”了一声,随即说道:“别走漏风声。”
看上去很滑稽也很可笑。
来人不敢流露这种感觉,马上应道:“是。”
来人转回身,走了,已经走到了门口,郑官突然说:“站住!瞧我的……这次一定要剿灭他们……”
来人吓了一跳,站住了。
郑官对他挥了挥手,说:“好了,你走吧。”
到了第二天,也就是腊月初十,天黑以后,郑官骑上他的花马,带着八十名弟兄,静悄悄地出了城,向许大房子奔去。依他的判断,三十多里的路程,不消一个时辰,他们就赶到了。
后来有人说,那一天冷得邪乎。
那一天确实冷,小北风儿刀子似的,割着人的脸。田野上的积雪在月光下泛着白光,看上去无边无际。偶尔还响起一声长长的狼嚎,让人听着瘆得慌。这时候,“老疙瘩”的队伍正稀稀拉拉地走在雪地上,看似十分散漫。他们一律穿着牛皮乌拉,走起路来嚓嚓作响,又轻又快。每个人都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有人腰上扎着麻绳,还把狗皮帽子的帽耳朵拉下来系在了下巴上。时间长了,帽子四周(包括眼睫毛)已经挂了一层的霜。
这时有人说:“妈的这熊天儿,咋这么冷!”
马上有人接着说:“我这儿带着烧酒呢,要不你抿一口?”
先前那人说:“得,我还是等完事儿再喝吧。”
说话的两个人一大一小,这包括身材也包括语声儿,大的身材高大,小的单薄瘦小,大的声音粗哑,小的还带着一口的娃娃腔。这大的就是“老疙瘩”的头领,他们称作当家的。其实他的名字就叫老疙瘩。不过这并不是他的大名。在东北,老疙瘩是专门用来称呼家中最末一个男孩子的。这样看老疙瘩显然只是他的小名或乳名了。老疙瘩的名声如此之大,人人都说他心狠手黑,当年他只有二十六岁。
过了一会儿,老疙瘩说:“喜子你想喝吧?想喝你就喝。”
喜子说:“我可不喝,辣烘烘的。再说我也不冷。”
喜子就是那个小的,那年他十五岁,因为长得瘦小,看去还没有十五岁大。喜子是个孤儿,他说自己命硬,把爹妈给克死了。那时候他才七岁。此后他就成了一个小叫花子,衣裳破破烂烂的,一年也不洗一次脸……他说我不饿死就不错了,哪有工夫洗脸?喜子九岁那年,有一次老疙瘩跟几个兄弟上城里闲逛,在窑子门口遇见了他。喜子说他那天特别惨,一天没整着吃的,眼看就饿死了,多亏当家的给了他两个大馒头。喜子当时就对老疙瘩说,往后你给我当爹中不中?老疙瘩看他挺机灵,领上他出了城。
喜子一直很讨老疙瘩的喜爱,他啥话都乐意跟他说,偶尔还会逗逗闷子。
两个人肩挨肩地走在这支稀稀拉拉的队伍的中间儿。
走着走着,老疙瘩又说:“你小子太嫩,还不知道这东西的好。人活着就两件美事儿,一件是酒,再一件是娘们儿……知道吗?”
喜子说:“不知道。”
老疙瘩说:“慢慢你就知道了,这东西不用教。以前我也不知道,如今不全知道了?不过这里有个铺衬,你先得想法儿让自个儿吃饱喽。饭都吃不饱,哪还有心思想别的?”
喜子说:“那倒是。”
老疙瘩说:“吃饱了不算,人还得要面子。我这人就最要面子。别的不说,有人一提老疙瘩这仨字儿就哆嗦,还花那么多银子买我的脑袋,这就是面子。”
喜子说:“那你怕不怕?”
老疙瘩说:“怕不怕都没用。反正谁都有那么一天儿,迟早的事儿。我心里有谱儿。人活一世,要不窝窝囊囊一辈子,谁都能照屁股给你一脚,就像我爹那样。要不你就浑作乱闹……你没看这世道,你不怕他他就怕你,谁硬气谁是爷。”
喜子这次没吱声。
老疙瘩接着说:“娘的这帮狗头狗脑的东西,你要是一熊,他都恨不能把你嚼了,骨头都不带吐的,根本就不把你当人看……”
老疙瘩停了一下说:“……哎,喜子你上前头问问二爷,许大房子还有多远。我觉着差不多了。”
喜子答应一声,快步向队伍前边走去,一会儿他回来了,喘着粗气对老疙瘩说:“眼看就到了。都看着屯子影了,黑糊糊一片。”
老疙瘩马上兴奋起来,同时心里特别紧张,肠子都一抽一抽的,甚至直想撒尿。这是他的老毛病了,每次行动都有这种感觉,这些年来一直如比。这样过了片刻,他说:“给二爷传话儿,咱们打西头儿进去……照老规矩,不到万不得已,别伤人……”
二十分钟以后,这里发生了一场激战。战斗是在许大房子屯的屯头儿打响的,战斗特别混乱,不过都很英勇,许多人纷纷地倒下去,倒下去的人都在哗哗地流血,声音就像山泉一样清晰可闻,越流身体越冷,一直流得脑子一片空白。激战持续了一个时辰,双方共有五十多人被打死。天一亮,但见五十多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屯西的坡地上,每个人的身下都铺着一片血水结成的冰。
在辨认尸体的时候,有人发现了郑官。
郑官的死轰动一时,大家都知道××分防的哨管叫“老疙瘩”给打死了。这件事也惊动了各级官府。后经多方协商,将郑官及其他战死官兵运至城郊义地安葬,将死匪就地掩埋。并且造了一块石碑,雕着七个大字“郑官兰斋战死处”,立于许大房子屯西。这样,许大房子屯就变成了郑官屯,直到如今。而且,一旦有人来到这里,他们必定要讲这个故事,讲郑官屯是怎么怎么个来历,听起来颇有意思。
后来老疙瘩也死了,只不过比郑官晚一些。
1932年(伪满大同元年,那时候日本人已经占了东三省)8月26日,下午四时许,有一支八百人的队伍突然包围了被日本人占领的昌五城(当时的县城),并对城里发起攻击。他们赤裸上身,狂呼乱喊,打的是“三省抗日义勇军”的旗号。就在他们即将攻进城去的时候,日本人的援军到了。日本人前后夹击,义勇军死伤多人,余下的迅速溃散。日本人特别恼怒,战斗结束后,割下了所有战死的义勇军的脑袋,用铁丝串在一起,挂在城墙上示众。
脑袋周围飞舞着成千上万只苍蝇,黑压压一片。
其中有两颗,一颗是老疙瘩,另一颗是喜子。
张步屯
据付彩云老太太自己讲,她是在伪满洲国康德八年(1941)嫁到张步屯来的,那年她还不满十七岁。丈夫要比她大得多,当时五十多岁了。成亲的第一天晚上,丈夫的肚子一直在“咕噜噜咕噜噜”地响,吵得她一宿都没睡着觉。开始她以为他是在闹肚子,后来才发现他天天这样。这准是因为他老了,她暗自猜想,人一老就啥都不中用了。不过她明白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在这之前,她爸已经从丈夫家里驮去了两麻袋高粱,还揣走了一沓绵羊票子(伪满洲国纸币)。
不管咋样,往后我再也不会挨饿啦!她这样安慰自己。
付彩云说:“那年月,女人就这样啊!”
丈夫名叫张步青,剃光头,出门时戴一顶瓜皮礼帽,窄脸,下巴上长着一些稀稀拉拉的花白胡子,两边脸上一边一块高高的颧骨,小眼睛,看上去似乎只有一道逢儿,然而眼神儿却特别地锐利,嘴唇薄薄的,总是紧紧地抿着,而且总是很少说话(当然不是不说话,他又不是哑巴)。
那时候,付彩云总是有些怕他。后来她发现,其实不光她一个人,家里头别的人也是怕他的。在付彩云之前,他已经有了两个老婆,除此之外,他还有儿子和儿媳妇,还有孙子和孙女,加到一起,少说也有十几口子了(因为儿子儿媳妇和孙子孙女都不止一个),大家住在一个大院里,他们之中无论谁,见了他都“溜溜”的,就像耗子见到了猫,哪怕他无意间咳嗽一声,他们也会吓得一哆嗦。那些年纪小的小孩子,甚至会“哇”的一声哭起来,他却理也不理。
照付彩云老太太的说法,她丈夫张步青是个性格很怪的人,别看他整日整日的不说话,实际脾气暴躁得很,发起火来地动山摇的,而且特别犟,就像有人说的,是属于叼着屎橛儿给他麻花都不换的那种人,就是说,认死理儿。付彩云说她亲耳听到过,他的前两个老婆背地里都叫他犟驴,简单些便说成“那驴”,那驴长那驴短,付彩云每次听到都会心一笑,她说她们说得对。
付彩云说,当时老张家是这一带有名的大户人家儿,好地就有上百垧,自家还开了一处油坊和一处烧锅(酒坊),除此之外,还在县里开了一处粮行,一处杂货店,专卖自家出产的东西,年年进的钱都“海海”的。屯子里更不用说了,房子都是青砖的,除了正房还有厢房,少说也有几十间,四周都有高墙围着,墙外建有炮台,里头住着炮勇,炮勇人人有枪。整个张步屯,他家就占了一大半。
张步青家财大势也大,看来这是没有问题的。
尽管他家有钱还有势,可是张步青却没有多少大财主的样子。除了付彩云,另外几个当年见过他的人也是这么说的。比方他的穿戴,除去那顶瓜皮礼帽(还有一件冬天穿的羊皮大氅),不过就是衣裳干净一点,没有补丁,他的穿戴和屯里的许多人几乎没什么两样。而且,夏天的时候也喜欢挽起裤脚,这当然是为了干活方便。据说他每天都要干活的,逮住什么就干什么。即便没什么活干,他也这么一副样子:肩上扛着一把锄头,有时候在屯子里,有时候在田里,四处转悠。
那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四处转悠。他走一会儿站一会儿,一边还东张西望,总是一脸的心事儿,谁也说不上他在想什么。“多半在想怎样扩大他的家业。”付彩云和那几个当年见过他的人都如此猜测。
还有吃饭。吃饭他讲究吃半饱,就是说,吃到半饿不饿为止。一般只吃一碗小米捞饭,再喝一碗小米饭汤。菜也简单得很,一碟儿萝卜条咸菜是必备的,不过要用辣椒油拌一下,此外再加一个炖菜,炖土豆炖白菜炖茄子炖豆角等等,偶尔在里面放几块肉。因为是大家一起吃饭,要把菜分别盛在几只大海碗里,可是不论几只碗,菜却只有那么一个。这些事都是付彩云亲眼看见的。
问题是不光他自己这样做,他要求别人也这样做。有一次(当时付彩云嫁过来没几天),全家人正在吃饭,吃着吃着,他突然大声说:“吃饭别吃得太饱,吃到八分饱就行了……少吃一口谁也饿不死!”当时谁也没吱声,只有付彩云吃了一惊,她抬起头四处一 看,发现每个人都在看她,明白这是说给她的。后来她才知道,这话他早就对别人说过了。
那些年这儿还是日本人的天下,县里住着日本人的军队,日本人当着本县的副县长(虽然不叫副县长,而叫参事官,实际却是一回事),还当着警务局的指导官、警察署的警政,反正什么事儿都是他们说了算的。
当年不是有个满洲国嘛?满洲国的皇上叫康德。早先年有个大清国,大清国有个乾隆爷有个慈禧皇太后,他们就是他的祖上。听说二十年前康德就当过一回皇上,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最多四五岁,好像叫宣统,住在北京的大殿里,后来叫什么人给撵跑了。往后就来了一帮日本人,他又第二回当了皇上。不过不在北京住了,换了一个地方叫新京,新京离黑龙江不太远,那儿现在叫长春。他们说他这个皇上可不好当,说他处处得听日本人的管。
“这些事儿都是我从老辈人那儿听说的,不知道真假。”付彩云补充道。
付彩云还说了一件事儿,说就在她嫁到张步屯的那年秋天,庄稼刚刚上场(就是刚从地里收回来),有一天,从山河镇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镇公所的办事员,一个是警察署的“白帽箍”,“白帽箍”挎着匣枪。他们说镇上有事,把张步青叫走了。那时候常有这种情况,一旦有什么事,就派人过来叫他,他又是张步屯的甲长,动不动就会被叫去一次。
不过这次好像有些不同。他们走的时候是贴晌时分,直到天黑他才回来。而且,和以前相比,这次的状态也大不一样。一进家门,他就破口大骂:“这些狗操的王八羔子,欺负到我头上来啦!我苦巴苦业挣下这份儿家产,他们说拿去就得拿去!说拿多少就拿多少!天底下还有没有王法……”
他脸色青紫,脑袋和双手,还有嘴唇和胡子,都不停地哆嗦,没等骂完,就一头栽倒在院子里。当时家里人都在院子里,有大人还有几个炮勇和长工,大家本来正在等他回来吃饭,这时马上乱作一团,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随即有人喊道:“别愣着!救人要紧!”
还有人喊:“掐人中!快!掐人中!”
于是有人掐他的人中,还有人进屋含了一口凉水,“噗”地往他脸上一喷。过了一会儿,他总算哼哼着睁开了眼睛。人们七手八脚,立刻把他抬进了屋。
缓过劲儿来以后,他才说出了事情的原委,日本人要建开拓团(就是要在这儿种地建屯子),要征他四十垧熟地。
他瞪着眼睛说:“娘的四十垧啊!还一个大钱不给……要不咋叫征呢!”
付彩云说,从此张步青就病了,一病十几天,天天在炕上躺着,人也一天天往下瘦,几天就瘦得不成样子了,看着让人可冷。家里给他请了大夫,说是急火攻心,抓了很多药,药都是付彩云给熬的(那会儿没有药片儿,都是草药),一天熬一副。药汤子又黑又苦,盛在一只二大碗(碗的一种,比大碗小,比小碗大)里,眼瞅着他“咕嘟咕嘟”灌下去。
那一阵儿不论哪儿都是他的药味,药味就像小虫子一样,墙角旮旯都能钻进去。光药味不要紧,家里还处处笼罩着一种说不上来的恐怖的气氛,让人老是提心吊胆的,说话走路都得小心又小心。怎么说呢,就像家里死了人。这也是一种味。两种味道混在一起,把人压得气都喘不上来。
这期间日本人已经把地占上了,而且沿着划定的地界儿钉了好多的木牌。这消息是张步青的儿子带回来的。张步青有两个儿子,他们都亲眼看见了那些木牌,上面还写着日本字。不过这件事他们没有马上告诉张步青,怕他受不了。在付彩云的感觉里,这两个儿子都不像张步青。
张步青的病总算一天天见好了。一天晚上,他让付彩云去叫两个儿子。儿子们一前一后来到张步青的屋子,其中一个说:“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家有枪又有炮的,我看咱就别吃这眼前亏了……”
儿子还没说完,就被张步青打断了,他大声吼道:“孬种!”
因为病还没有全好,吼过之后他喘息了一会儿,半晌才平静下来,说:“这件事儿我想好了,我要上新京找皇上去。我要去告御状。不管咋说,这满洲国还是他皇上的吧。我就不信讨不回这个公道……这件事宜早不宜迟,明天我就走。”
第二天他真的走了。他是上午走的,走的时候戴着那顶瓜皮礼帽,儿子们给他套了一挂马车,车上铺了一条棉被,还带了一名炮勇。
付彩云说:“想不到,这一去他就送了命……”
关于张步青,县志上是这么说的:
“张步青,旧时本县山河镇西郊有名的乡绅地主,社会影响颇大,人送外号‘张老步,所住自然屯被称为‘张步屯。此人性格倔强……伪满康德八年,日本侵略者指名收其良田四十垧,为日本人专用。张执意不从,公开与日伪势力对抗,被捕入狱。释放后又去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告‘御状,伪新京高等检察院见其是地方乡绅,不便加罪,于是采取两面手法,明则好言相劝,暗则捣鬼下毒,致使其中枢神经损伤,1942年(伪康德九年)归里后不久即死去,时年五十六岁。”
后来付彩云嫁给了屯里的一个农民,当时东北已经光复了。她和现在的丈夫生了两儿一女,如今儿女们早已各自成家。付彩云现年七十七岁,满头的白发绾在脑后。
这时已是傍晚时分,红彤彤的晚霞映照着天空。老太太坐在她家大门口一个木墩儿上,正在慢条斯理地纳鞋底儿。这会儿她抬起头,朝西天看了一眼,抱歉地笑笑说:“不能再跟你唠了……该给老东西整饭去了……”
说着话儿站起来,离开我,慢悠悠地向院子里走去。
【作者简介】鲍十,男,原籍黑龙江省。已出版长篇小说《痴迷》、《好运之年》,中篇小说集《拜庄》、《我的父亲母亲》、《葵花开放的声音》、《鲍十小说自选集》,日文版小说《初恋之路》等,有作品在台湾地区发表。中篇小说《纪念》被改编成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现居广州,在某杂志社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