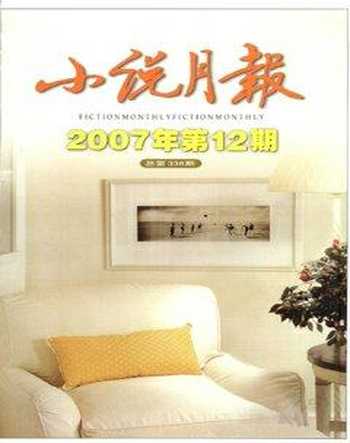桔梗谣
忠赫放下电话,心脏怦怦怦地跳着,他的手发麻,抽了两下,才把纸巾从盒里抽出来,吸掉眼窝里的泪水。
忠赫到衣橱里找了件新衬衫,拆包装时,手指头被大头针扎出了血,血滴黏稠,像颗红豆。新衬衫折痕明显,浆过的衣领卡着后脖颈,忠赫又脱了下来,换回了平时穿的旧衬衫,弯腰穿鞋的时候他动作有点儿急,脑子里面忽悠一下,眼前有些发黑。“慢点儿,慢点儿!”他提醒自己,扶着墙壁慢慢直起身。
春吉不在家。退休以后,她跟小区里另外几个女人组成了麻将小组,每天三四个小时,在几家轮番打打。在他们家打麻将时,春吉总是留朋友们吃饭,冷面啦,野菜酱汤啦,蔬菜肉丝面片啦,她兴致高昂地让人吃这个吃那个,哪怕是盘炒土豆丝,好像经过她的手之后,就变成了世间难寻的美味。
忠赫想象不出秀茶如今的模样儿。在朝阳川的时候,他家和秀茶家隔得不远,房前屋后种着几十株梨树,每年梨花盛开的半个月里,他们会被一场阳光晒不化的大雪掩埋住,天黑以后忠赫站在自家窗口朝秀茶的房间望去,她有时是雪国里的仙女,有时则变成灯笼里面的灯芯。四十年过去了,他的腰围变过好几个尺寸,头发灰白像黎明的天色,好在,他的腰杆还是拔得直直的,这是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每天走路一个小时的馈赠。
在候车室的门口,在嘈杂的声音、难以形容的味道以及流动的色彩中间,忠赫还没从出租车下来就看到了秀茶,穿着紫灰色套装,和以前一样苗条,肤色也还是白得像豆腐,皱纹没把她变丑,把她变温柔平实了,像穿旧揉皱了的棉麻布衣服。忠赫胸口闷闷的,像压上了石磨——以前在朝阳川时,他家院子里就有一盘,清晨或者傍晚,他和秀茶常坐在石磨边儿上做作业。高中毕业以后他们也还保留着在石磨边儿看书的习惯,大多是从县图书馆借来的小说,里面写些什么他早就忘了,但他记得秀茶边看书边哼的歌儿:
白色桔梗花啊紫色桔梗花,站在山坡下,花像海洋从天上飞流而来,漫山遍野,凝神细看,白色桔梗花啊紫色桔梗花。
“忠赫——”
秀茶的微笑近在眼前,但转眼就浸到了湖水里面。忠赫抹了一把泪水,秀茶的眼睛里也泛起一片水雾。
秀茶参加了她所在城市的夕阳红艺术团。在第四候车室里,有她二十九个同伴。“我们刚从长白山旅游回来,在这里换火车。”
他们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忠赫带秀茶去了候车室旁边的咖啡座。那里卖的咖啡是速溶袋装咖啡,忠赫把服务员叫来,又要了两杯铁观音。他还点了牛肉脯、鱿鱼丝、话梅,“这个茶太硬,稍微吃点东西,要不胃会不舒服。”
秀茶笑了,“你还是那么细心。”
“你怎么找到我的?”他问她。
“想找总能找到。”她说。
他很惭愧。他没找过她。但他从没忘记过她。有好几年的时间,每晚临睡前一个小时,他给妈妈按摩手臂和腿脚,老太太翻来覆去地回忆朝阳川的陈年旧事,忠赫能在妈妈提到的每个人身后、每件事中间看到秀茶。“累了吗?”他离开时,老太太问他。或者是,“天天这么按来按去,还要听我唠叨,烦死了吧?”
“我愿意给妈妈按摩到一百岁。”忠赫真心真意地这么说,这是他跟秀茶相处的时间,怎么会累、会烦呢?
忠赫难得发脾气,但春吉训斥女儿时除外。每次女儿透过责骂眼泪汪汪地朝他转过脸,他都会看见秀茶的委屈,他用更阴沉更难看的脸色回应春吉,拉着女儿出门,带她去饭店吃饭,买礼物给她。
“小时候我很恨你,”儿子有一次对他说,“你对妹妹好得恨不得含到嘴里,而我就像你要吐出去的什么东西。”
“女孩子当然要娇惯一点儿。”他说。
他从小就习惯了对女孩子好。他跟秀茶上学时,碰上泥泞难走的路,他都是背着她过去的。她伏在他的背上,让他想起一只收拢翅膀的鸟。春天的时候,忠赫给秀茶编蝈蝈笼,为了把干玉米秆破成细条,手指头划出好多道细口子,洗手时疼得龇牙咧嘴的。有一年端午节,他给秀茶采染指甲用的酸浆草时,被蛇咬了,幸亏是草蛇,毒性不大,他妈妈吓得半死,抱着他的腿用嘴往外吮毒液,吮得嘴唇都肿了。秀茶的父母在旁边看着,挓挲着手帮不上忙,被忠赫妈妈的身体语言羞臊得满脸通红。
忠赫的妈妈二十一岁守寡,独自把忠赫带大,供他读书到高中毕业。忠赫的衣服永远是干干净净的,哪怕只有一套衣服,也是晚上洗好晾干,早晨干净整齐地出门。
老太太一辈子只对忠赫提过一个要求:娶春吉。
“我喜欢她的大脸盘儿,福相。”老太太说,“屁股也长得好,能生出好孩子来。”
如老太太所言,春吉生了两个好孩子。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春吉像发面的面团儿一样越来越浑圆,睡觉时呼噜打得一嘟噜一串儿的,忠赫常会梦见自己站在秋天的稻田地里,风吹稻浪,像涛声一样响亮,他变成了稻草人儿,破衣烂衫,伸着胳膊,眼看着秀茶从田埂上走开却叫不出声来。
去年刚退休的那几个月,忠赫着了魔似地想念秀茶家的豆浆。那间老豆腐房光线昏暗,地面上水渍渍的,刚点出来的豆腐在豆腐包里颤颤巍巍地抖动。豆浆装在粗瓷盆里,他和秀茶往里面撒几粒糖精,每天上学前喝得肚子胀胀的,打嗝时嘴里有一股豆香味儿。忠赫跑遍了城里所有有豆浆卖的地方,发现那股鲜嫩的味道再也找不到了。
“嫂子好吗?”
春吉和忠赫结婚那天,秀茶是以他妹妹的身份,拿着木瓢,隔着喜桌——让一对木头鸳鸯,一对蒸熟的、嘴里叼着整支红辣椒的公鸡母鸡,各种糖果、水果、鲜花,还有十几种糕饼摆得满满登登的——朝新娘子伸过来,春吉把一大捧糖果扔进去。后来忠赫听说,秀茶把糖讨来后钻进树林,一颗不剩地全吃光了。她把糖纸用熨斗熨平,折了个鸳鸯放在家里的窗台上。
秀茶结婚时,忠赫天不亮就起来,跟另外几个小伙子一起在院子里打打糕,刚蒸熟的糯米米粒晶莹剔透,像颗颗泪珠,他们用的木锤三斤半重,要几万锤才能把这些泪珠打成死心的一团。
秀茶的男人姓尹,是部队转业干部,虽然年轻,但自有一股慑人气势。他跟秀茶订婚的时候,忠赫也在酒桌上作陪。男人们在酒桌上喝酒,女人们的饭摆在豆腐房那边,酒喝到一半时,秀茶被她爸爸叫过来,给客人们敬酒,她低垂着眼睛,睫毛像副门帘,敬酒的时候手在发抖。忠赫从来没喝过那么难咽的酒,酒里面带着锯齿,每一杯喝下去,都是一道伤口。
秀茶说,老尹五年前得过脑血栓,治疗得很及时,现在走路什么的,都不影响。儿子给她雇了个全职保姆帮忙照顾。
“他叫万宇。”秀茶说。
“——我去见秀茶了。”
忠赫换了拖鞋,径直走进他的房间——孩子们自立门户后,他们就分房睡了——墙上挂着老太太的照片。是她过六十大寿生日那天拍的,她穿着雪白的朝鲜族服装,领口袖口镶着白色丝缎,胸前的蝴蝶结打得端端正正,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别住头发的簪子是忠赫用根木筷子雕刻成的,打磨,上漆,再打磨,花了整整一个星期。
老太太目光幽深地望着忠赫。
老太太去世前的两年,喜欢坐在放在阳台的藤椅里,眯着眼睛望着远处的长河,黄昏时,阳光像泼洒的蛋黄覆盖在河面上,流淌的河水涌动如大蛇,一口口吸光蛋黄汁,直至把整个太阳都吞下肚去。
忠赫陪着老太太坐着,太阳往下落时,他想起很久以前跟秀茶坐在长满红菰茑的山坡上,她用细草棍儿把菰茑的筋络和籽粒从小米粒大小的洞里挑出来,把空空的薄如蝉翼的菰茑壳放在舌头上,像小灯笼那样吹满它,又用牙齿把里面的气挤出去,然后再吹满,再挤出去。她给他也弄了一个,那个小小灯笼似的壳,落在他的舌尖上,酸甜味道中夹杂着苦味儿,为了把它吹满气儿,他全身所有的力气都用上了。
“——你去见秀茶了?”
春吉还站在门口,忠赫朝她转过头时,她把手里攥着的东西朝他用力地扔过来,但那东西轻飘飘地,隔着老远就落到了地上。
“我以为你出车祸了,要么就是心脏病,脑出血。你去见秀茶了?!你见秀茶不能打个电话?!不能留个纸条?!”
忠赫看着春吉,她的脸涨得通红,眼泪从眼眶里跌出来,漫漶在脸上。春吉如此愤怒,却连忠赫的衣角都没沾到,像那个飘到地上的布袋子一样。刚才他坐在车里回家时,司机跟他说话他也是反应了好一会儿才回答。
“——这不是回来了嘛。”他说。
“回来了?”春吉冷笑一声,“魂儿呢?跟着秀茶走了吧?”
她说的对。他的魂儿就像块骨头,被秀茶的话叼走了。
忠赫不想跟春吉吵架。他们之间使用的语言从来没什么暴力,多年来跟妈妈一起生活,忠赫觉得骂了别人,自己会更加难堪。话说回来,春吉也是个温和的女人。他们上次闹不高兴是一个多月前,春吉请朋友们在家里吃烤牛肉,好几个小时以后家里还飘荡着烤肉的味道,忠赫去厨房烧开水时,发现水壶上面覆盖着油腥儿,他生起气来。
晚上吃饭时,春吉做了油焖带皮小土豆和凉拌黄豆芽,饭是白米里面加上了松仁核桃仁芝麻红豆,用石锅蒸出来的,掀开盖子,清甜气息扑面而来。忠赫一闻到饭香,火气就没了。
孩子们相继打电话回来,春吉明明在客厅,电话仍然响个没完,忠赫只好用分机接,“你去哪里了?让妈妈担心得要命。”
孩子们跟忠赫说完,要跟妈妈讲话,忠赫去客厅叫春吉,春吉眼睛盯着电视,不接他递过去的电话。
“你妈还生气呢。”忠赫跟孩子们说。
“那你就想办法将功赎罪吧。”孩子们笑着放了电话。
地方台每天晚上播三集韩剧,剧目不同但故事都差不多,不是两兄弟爱上同一个姑娘,就是两姐妹爱上同一个男人,要么就是两兄弟爱上了两姐妹。这些荒唐可笑的故事,动不动就让春吉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你多大岁数了还为这些东西哭哭啼啼的?”忠赫笑话她。
“你知道什么?!”春吉回敬他。
他知道什么?!那她呢?离开朝阳川以后,她偶尔还和镇里的人联系,而他是决意跟所有人都断了联系的。
看完电视剧春吉也不睡,客厅里灯光亮着,在门缝下面透一截进来。
忠赫去卫生间时,看见春吉把前几天别人送的新鲜沙参从冰箱里拿出来,沙参疙疙瘩瘩的厚皮跟鳄鱼皮差不多,要用小刀一点点剥下来才行,他从卫生问出来时,“——秀茶也老了吧?”春吉忽然冒出一句。
“像她那样的眼睛,老了的时候眼皮会耷拉下来把半个眼睛盖住。”
春吉心地不坏,忠赫也知道他顺水推舟地说句话就会让她消气儿,可他们谈论的是秀茶啊,“她现在也还很漂亮。”
“她就是太漂亮了,”春吉说,“妈妈才不让她当儿媳妇的,妈妈说,三岁看到老,秀茶那个长相身段儿,不会有好命的。”
“妈妈还说你是个厚道人,心眼儿好呢。”
“你这是什么腔调啊?”春吉朝他扬起脸,春吉手里的那把刀他几天前刚磨过,锋刃摸起来像冰茬儿。“我说秀茶坏话了吗?”
“我也没说你说她坏话啊。”
“秀茶本来就过得不好嘛。”春吉说,“她男人老打她,孩子被打流产过,还有一次打折了肋骨,她回娘家养了两个月呢。”
忠赫的胃里面就像刚喝了一大碗热辣椒水,身上却打冷战似地哆嗦着。他盯着春吉,想用目光戳穿她的谎言,让她把说过的话收回去,但他的目光遭到了回敬。
“你不相信?”春吉说,“朝阳川谁都知道。”
谁都知道,但他不知道。但如果他知道,他会怎么样呢?他有勇气去把秀茶从那个人身边带走吗?秀茶在挨打的时候,期待过他的到来吗?既然连春吉都知道秀茶的事儿,秀茶肯定觉得他知道她的状况。
“他们闹了大半辈子,上了法庭,总算离了婚。那个男人离婚以后天天喝酒,别说当领导,连工作也丢了,还得了脑血栓,不知道秀茶怎么想的,放着清净日子不过,又回去侍候那个男人去了!”
他怀疑春吉和秀茶说的是不是同一个人。今天秀茶说起老尹时,就像说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还说儿子有空的时候,带着他们去动物园、水族馆、游乐场,拿他们当小孩子哄。
“——秀茶的儿子,”他嘴里发干,吐出来的字像一颗颗火星,“叫万宇,是吧?”
春吉抬起头,他们对视着,都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可能是吧。”春吉又埋头剥起沙参来。
忠赫回到房间,直接走上阳台。阳台上面凉飕飕的,大河边儿上新近开发了好多楼盘,他们刚搬来这里时,河堤是石头垒出来的,石头缝里长着杂草,现在已经被水泥堤坝和成排的丁香树取代了。春末夏初,白色和紫色丁香花开得烟一片雾一片,让他想起朝阳川漫山遍野的桔梗花。但现在什么也看不见。黑黪黪的,一团虚无,风的手时轻时重地在人身上摸索一阵。
“秀茶找你干什么?”春吉跟过来,问他。
他很高兴他们站在黑暗里,这样的光线,话比较容易说出口,“万宇下个月结婚,秀茶邀请我们去参加婚礼。”
“我们的孩子结婚时她没来啊。”春吉说,“她儿子结婚倒要我们去随礼?!”
春吉让女儿挑了一家有名的美发店,花好几百块钱烫了头发,没过几天又剪掉了,只留下些发卷儿。
“那不是白花钱了?”忠赫问。
春吉说就是这么个过程。她离远了让忠赫看,“这个发型显瘦吧?”
忠赫什么也看不出来,但很肯定地回答,“瘦了不少呢。”
春吉还让女儿买回一撂面膜,每晚看韩剧时敷,白煞煞的面膜覆盖着整张脸,眼睛、鼻孔以及嘴唇抠出几个洞,忠赫第一次看见时吓了一跳。
“你抽什么疯?”
春吉在面膜下面白了他一眼。
春吉买衣服买鞋子,连内衣也买了好几套,“爸,你初恋情人到底有多漂亮?看把我妈折腾的。”女儿进门后把几个纸拎兜扔下,“大”字型扑倒在沙发上,“老妇聊发少女狂啊。”
“我这个月的业绩算泡汤了——”
“陪你妈买买东西就这么不耐烦,”忠赫说,“养育之恩可不是嘴皮子碰碰就报答的啊。”
说是这么说,忠赫也觉得春吉过分。她连饭也不吃了,每天细嚼慢咽一个苹果。自己不吃,给忠赫做饭也对付,一个星期让他吃了三顿泡菜肉丝炒饭。她还建议忠赫跟她一起喝淡盐水,吃苹果。
“胃肠也需要大扫除啊。”春吉说。
出发的前一天,春吉染了头发,染发膏的盒子上面把她染的颜色叫“甜蜜焦糖”。他跟春吉抱怨,她头发上那股蜡烛融化的味道让他吃不下饭。
“是要见到万宇了,紧张的吧?”春吉说。
春吉经过这些日子的捣腾,像变了个人似的,不光外貌,她说话做事,也变得不大一样了。
“说你的头发,关万宇什么事儿?”
“嫌弃我?”春吉拉下脸来,“我还不去了呢。”
她把门在身后摔上。
“我也没说什么啊。”忠赫推开门,“你发什么脾气?!”
“想想就窝囊,”春吉别扭起来,“你们做的好事儿,过了四十年拿出来展览,我还要去捧场?!”
忠赫刚要开口,被春吉“没有这么欺负人的!”吼了回去。
忠赫没辙,把儿子女儿叫了回来,两个孩子跟春吉关上门说了两个小时,儿子先出来,压低声音跟忠赫说:“同意去了。”
“明天我开车送你们去。”儿子说。
他们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儿子忽然笑了,忠赫看了他一眼,“你笑什么?”
“——没什么。”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女儿眼睛红红地出来,“明天我也去。”
她跟哥哥一起回家,忠赫送他们出门时,女儿扭头看看他,凑到他耳边低声说,“我都有些等不及要见见这位哥哥了。”
她叫得那么自然,忠赫心里雷一阵雨一阵,眼睛湿了。
第二天他们一早出门,忠赫和儿子坐前面,女儿和春吉坐后面。女儿先是把春吉从头夸到脚,仿佛她是个大明星似的,然后又说,他们四个很久没单独在一起了,“就像去春游。”
“秋游。”儿子纠正她。
“管他春夏秋冬的呢。”女儿一路张罗,吃这个,喝那个,说从原野上卷起的晨雾像棉絮似的,突然又指着沐浴在阳光中的枫树尖叫,“看那棵树啊,像烧着了一样!”
“别一惊一乍的。”春吉训她,从昨天晚上孩子们离开,忠赫总算听到她又开口说话了,“你也是当妈的人了。”
他们直接去了酒店。两个男人先下车,女儿在车里帮春吉补了补妆。
“他和我,谁大?”儿子问忠赫。
“——你比他大几个月吧。”
他们坐电梯上楼,连女儿都变沉默了。电梯门一开,忠赫就看见了秀茶,一个女人正拉着她往大厅里走,她用眼角余光看见他们,一下子站住了。春吉也看见了秀茶,脸色发白。
秀茶裙摆阔大,衣带飘飘,像踩着云彩奔过来,老远就冲春吉伸出了双手。两个女人加起来一百二十多岁了,抱着对方,像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刚才拉秀茶进厅里的女人过来,有些摸不着头脑,“怎么哭起来了?时间到了快进去啊。”
秀茶没理她,用纸巾替春吉吸了吸眼泪,目光在忠赫脸上一掠而过,落到他的一双儿女脸上,“你们都这么大了。”
他们一起鞠躬,给她行礼问好。
秀茶把他们拉起来,眼泪又涌出来。
女人拉秀茶一把,“都等着呢。”
“我们一起进去。”秀茶拉住春吉,带着他们往厅里走。在门口遇到手挽手的新郎新娘。
忠赫嘴唇发干,全身微微颤抖。万宇个子挺高的,穿着黑西服白衬衫,胸口别了一朵粉色玫瑰花,他的单眼皮、高鼻梁、略厚的嘴唇跟忠赫一模一样。看到忠赫时,他的表情一凛。
春吉只顾打量万宇,踩到了秀茶的裙子,差点儿把她绊倒。
“快点快点。”女人不停地催促着,推着他们这一群人先进去,秀茶先把他们送到预留的贵宾席上,才坐到礼堂中间新人家长的位置。忠赫看到老尹,坐在秀茶椅子旁边的轮椅里面,头发剪得短短的,胡子刮得千干净净,黑西服白衬衫,领带很漂亮,半边身子不动,另外半边不停地颤抖,他的眼睛盯着一个固定的方向,嘴唇哆嗦着,忠赫怀疑他还能不能完整地说出话来。
司仪宣布吉时已到,婚礼开始,全体贵宾起立,迎接新人出场。音乐响起,不是通常的婚礼进行曲,而是一组朝鲜族民谣,来宾们和着主持人鼓着掌,看着新郎新娘款款走过撒了玫瑰花瓣的地毯,一直站到台上。
司仪开始介绍新娘——他身后的大屏幕随着他的介绍,展示出新娘从婴儿直至眼下各个时期的照片——她是艺术学院的舞蹈老师,今年二十八岁。父母的掌上明珠,聪明伶俐,从五岁开始就被人追,为了万宇她至少伤了一万个男人的心。主持人的话引来阵阵掌声,年轻人聚堆儿的几桌不时传来叫好声。新娘之后介绍新郎,万宇从小聪明过人——忠赫紧盯着大屏幕上的照片,这孩子小时候非常瘦弱,有些惊恐地瞪着镜头;五六岁以后,他好像不那么怕照相了,其中有一张照片活脱脱就是忠赫小时候的模样儿;七八岁的时候,他一脸忧郁,肯定是个不爱说话的孩子;十几岁的时候,忧伤、内敛变成了他表情里固定的一部分;二十岁左右,他的眼神里面有了冷峻、沉着的东西,长成了男人了——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纺织大学,十年前创建了自己的企业,现在企业已经有固定的六七百名员工,产品不光在国内销售,在韩国、日本,乃至东南亚市场也逐渐打开了局面。“为什么现在才结婚?”主持人把话筒伸向他。
“本来没有结婚的打算,”万宇说,冲新娘笑笑,“一不小心被俘虏了。”
酒宴持续了很长时间。
万宇带着新娘过来给忠赫和春吉敬了酒。新娘近看更漂亮,敬酒的姿态很优美,嗓音甜甜地管忠赫春吉叫“舅舅、舅妈”。秀茶应付了一阵客人后,推着老尹过来,忠赫跟他握了握手,老尹的手比他想象得有力量,然后保姆就带着老尹先回家了。
那些年轻人打开了音响,一边吃饭喝酒,一边唱歌跳舞。
秀茶和春吉说起过世了的忠赫妈妈,两个人泪眼汪汪的。忠赫第一次听说,秀茶当年生万宇时,月子没坐好,差点儿丢了命,是他妈妈买了熊胆托人送过去的。
“你长得很像你奶奶。”秀茶拉着忠赫女儿的手,感慨地说。
忠赫去了一趟厕所,万宇在洗手,他们的目光在镜子里相遇,忠赫冲他点点头,走进厕所,解裤带时,他的手抖得很厉害,花了平时两倍的时间。他摸到了裤带里面的信封,除了由春吉带着的三千块钱礼金,他把自己的两万块私房钱全提了出来,他知道万宇不缺钱,但他不知道,除了钱,他还能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情。
出来时,万宇用纸擦干了手,还扯出两张递给忠赫。他们一起走出洗手间,万宇掏出烟盒,抽出一支双手递给忠赫,然后又拿出打火机给他点着。
“——对不起。”忠赫抽了口烟,他说话时,刚好咳嗽起来,他怀疑万宇压根儿没听见他说了什么。
忠赫摸着裤子里的钱,刚要拿出来,有人脸喝得红红的一把抓住万宇,把他拉回大厅,万字匆忙中回头冲忠赫点了点头。
忠赫回到礼堂,一个女人站在圆桌子上面拿着麦克风在唱歌,桌子周围里三层外三层的是跳舞的人,先是《阿里郎》,然后是《桔梗谣》:
白色桔梗花啊紫色桔梗花,站在山坡下,花像海洋从天上飞流而来,漫山遍野,凝神细看——
忠赫回到桌边儿,秀茶和春吉脸红扑扑地跟着唱:“白色桔梗花啊紫色桔梗花。”唱完后两人搂在一起,咬着对方耳朵说着什么,春吉边笑边指着酒杯冲女儿叫:“倒满倒满。”
女儿给她们倒上酒,扭头冲忠赫做了个鬼脸,说:“她们已经约定了五十件事儿了,要去给奶奶上坟,要回朝阳川豆腐房做一次豆腐,要摘梨,还要在明年春天的时候去看梨花……”
原刊责编 毛一竹
【作者简介】金仁顺,女。著有小说集《爱情冷气流》、《月光啊月光》,散文集《仿佛一场白日梦》,影视作品集《绿茶》等。现在吉林某杂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