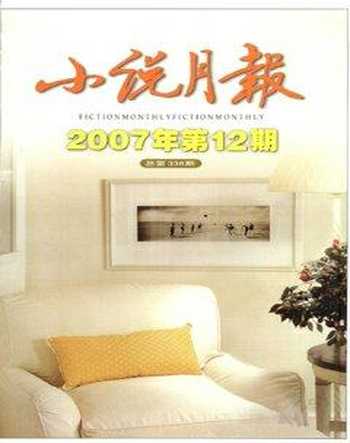知情者
改改是在最后一抹夕阳滑下山尖那一瞬间咽气的。咯噔,她的女儿们和众多的乡邻都听到她的喉眼里蹦出这么一声。随即,天色便暗了。心细眼尖的人们,发现与此同时,山尖上那抹流连许久的夕阳沉没了,仿佛也发出了与改改一样的吞咽声。区别只在于,一声切近些,苍凉些,一声遥远些,温厚些。于是,人们便真的相信,人的命真的是与天有关联的。
这时候,索索正赶着羊群从牧场回到村口。他听见了改改家传出的嚎哭声,悲伤哀婉,抑扬顿挫。他知道,是改改死了。他像一个被活埋的人,黄土淹在了胸口,漫上脖项,堵塞了五官七窍,在行将窒息而亡时,突然,有人扒开土,一股清风袭来,一种再生的感恩让他心潮澎湃。他扬起牧羊鞭,甩出一记脆响,开口吼出一段秦腔《杀狗劝妻》曹庄的唱段来:
肩挑起百斤柴春风吹送,
日过午盼回家大步流星。
靠卖柴换粮米全家度用,
虽清贫倒觉得快乐安宁。
索索是用须生腔唱的。二十年没大声说话了,乍一张口,又是在唱戏文,而秦腔本来就高亢悲壮,声薄云天,他一嗓子吼出,连自个也惊得呆了。好似一股泥石流,巨石潮涌,山崩地裂,改改家的嚎哭声马上被折断了,全村的鸡鸣狗叫声同时断了,连身边这群正在呼儿唤女急切归圈的羊,也四蹄僵立,诧然回头,怅望主人。索索不觉泪如雨下。二十年了啊,一个好端端的人,一个字正腔圆的人,硬是装聋作哑,把秘密深藏心底,风刮不出,水冲不出,刀子剜不出,甜言蜜语引不出,要是搁在战争年代,怎么着也是一个英雄。
唉,英雄也罢,狗熊也罢,人要活出来自己的主张哩。连羊都知道往草厚的地方跑哩,挨了鞭子也要去吃那几口嫩草哩。索索长叹一声,挥鞭赶着羊群,迎着一村失惊作怪的人脸走去。
当年,他是牧羊人,如今他还是牧羊人,可当下这群羊中,当年的羊早不剩一只了,他放牧是它们八代以后的子孙了。十八年,老了一个王宝钏,二十年,多少人老了,死了,多少人出生了,长大了呀。当年河边的柳树芽子,如今已长大成柳树了,树梢上,鸟雀翩翩,树下孩童嬉戏,喧哗盈耳。人生出两片嘴唇是要说话的,有事没事有话没话开口说说,人与世界的距离就扯近了,好似禾苗得到雨露的滋润,里里外外就有劲儿了。硬撑着不说话,就等于在人与世界间打了一道厚厚的隔墙,人看见世界陌生了,世界也与人生分了。连飞禽走兽都明白这个道理呢,都在不时地开口说话哩,有时,因为开口说话暴露了目标,石子枪子飞来,送了性命。可该说的还得说,不说话活着,和挨了石子枪子无甚区别。离村舍越来越近,天昏地暗,炊烟缭绕,索索已能看见人的脸面了,他却一下失去了主张。他不知该如何面对大家,又该如何面对改改一家人。这时,他又有些后悔,继续装聋作哑多好,人长着耳朵,但人都知道你听不见人说话,人就不给你说话了,你就会省去多少烦恼,人长着嘴,但却说不出话来,好话坏话听不进去,说不出来,又省去多少是非。可现在,他突然会说话了,会说话了,也就意味着能听见人说话了,也就得听人说,给人说。别人积攒了二十年的话要说给他听,又要让他说出积攒了二十年的话。那多可怕呀,这么多的人把二十年的话倾泻过来,他的两只耳朵变成两宽阔的河道才容得下,他的一张嘴要同时面对几十几百张嘴的探问,两片嘴唇非得磨成两片薄皮不可。
对改改的死去,所有的人都有充足的心理准备,她得的是绝症,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而对于索索的开口说话,着实让大家吃惊不小。人们都以为,他受了刺激,真的不会说话了,长着会说话的嘴的人,哪有沉默二十年的功力?
预想的可怕结果并没有出现,在夜色朦眬中,索索只看见一双双黑洞洞的眼睛在无神地瞅着他,一只只干瘪的嘴像一只只枯萎的喇叭花,一地的悄声无息。人们呆立两旁,呈夹道欢迎阵势,一村只有他和羊群杂杂沓沓的蹄脚声。索索一时六神无主,二十年来,他一直以为人们被他蒙在鼓里,难道人们同样也把他蒙在鼓里?一个人把众人蒙在鼓里并无什么要紧,可众人合谋把一个人蒙在鼓里,那就和命一般要紧了。
恐惧感在这一刻漫过了索索的心头。二十年来,他一人独享着保守秘密的快乐、孤独和高傲,惟独没有恐惧。而竟然,他与全村人保守的是同一个秘密,更可怕的是,全村人共同向他保守着同一个秘密。二十年来,多少个家庭、多少人极力维护的个人隐私,几乎在隐私产生的同时,也如风如雨又如雾,飘散在村庄的各个角落。在这样一个世代共居的群落里,本无什么隐私可言,而且,一个家庭、一个人如果没有令人一窥的隐私,没有隐私隔三间五暴露出来,任人评说,任人笑骂,那就意味着,这个家庭、这个人,在村中无足轻重。
这是一个村庄的生存法则,虽然可憎可厌且复可耻,却也是对相互关系的一种维系方式。
索索木然地将羊群关进圈里,游魂一般回到家里,他不知该如何将自己二十年来的反常行为向家人交待。令他一腔潸然的竟是老婆的一张虽然憔悴却也灿烂的笑脸,还有儿女虽然显得陌生却也由衷的欢欣,还有一桌丰盛的饭菜。他本是要把积聚了一肚子的话给家人说的,可他已不习惯说话了,也不会说话了,他只有对家人惨然一笑。
索索永远忘不了那个夏天,他的心绪永远走不出那个夏日的午后。
那个夏天其实是个平常的夏天,那个夏日的午后也是黄土高坡的人度过的无数个再也寻常不过的夏日的午后。艳阳高照,万里无云,热风消地,浮尘迷离。羊儿在山坡不紧不慢地吃草,他无情无绪地斜躺在山峁的树荫下,改改和丈夫在另一山头挖柴。在这个时分,除了虎口夺粮季节,村里人都躲在凉窑里歇晌的,可这两口子还在干活。日子过得紧呀!那是一面黄土悬崖,崖畔悬挂着几根椿树茬,许多人都想挖下来,可在眩晕的崖边,一个个却步了。事后,据改改的大女儿说,是她妈叫她爹一同去挖柴的。男人爬在悬崖边,努力探出半截身子,改改在他的身后。只见她将他的一条腿猛地一抬,男人像一只大鸟飞了下去,在一声遥远的闷响传出来的同时,还传来一声绝望的怒吼声。这时,改改也瘫坐在悬崖边披头散发,捶胸痛哭了。
全村的人被惊动了。改改平静下来后,一口咬定丈夫是失足坠崖。公公婆婆则一口咬定是她谋杀亲夫。公安来人了,一伙人在悬崖边比画了半天,声称失足的可能性不大,而且,改改有杀人动机。改改的肚子不争气,一连生出三个女孩,而公爹公婆和丈夫则希望她生出一个儿子来。为了老二老三,本来就菲薄的家底早被罚得一干二净。改改每生出一个女孩,便要遭受全家无休止的羞辱。他们也知道生男生女与两个人都有关,可总得有一个人需要为此承担责任,以求得大家的心理平衡。公爹公婆动嘴,丈夫动手,改改旧伤未复又添新创。老三刚满月几天,丈夫就要做那事,扬言再生不出儿子来,要给她的下身钉进一根木棒。她想那样将会很难受,而且很丢脸,好端端的,那叫什么事呀?她不能保证这一次一定能生出儿子来。丈夫缠了好几次了,虽还没得手,可两口子做这事哪有得不了手的?未来的日子咋过呀!她得活下去,像个女人那样活下去,她还有三个女儿要活人哩。那么,她们活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女儿们失去父亲,她失去丈夫。当然,这是改改的心里话。无论公爹公婆怎样闹,无论公安怎样审,她死不改口。村里人虽有种种疑惑,但都不够目击证人的条件,唯有索索完全具备。可在公安进村前,索索突然变得又聋又哑。厉声喝问,细语诱导,他一概侧着耳朵,一脸的糨糊,嘴里呜里哇啦,急得两手抓耳挠腮,总是说不出一句囫囵话来。写纸条问他,村里人共同证明,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
万般无奈,案子悬起了。索索还放羊,从此,他变得又聋又哑,他从没在任何人面前说过一句话,包括自己的家人。从那天起,他在羊圈边又挖了一孔住人的窑洞,盘了一片土炕,他怕梦中说出话来不好。间或想做那事了,他溜到老婆住的窑洞,比比画画,事情一完,立即撤退。其实,别人哪知道,他和他的羊一直在说话。从那天起,索索喜欢去远离村庄的荒沟和牧,四野无人,只有风,只有雨,只有荒草尘埃,只有飞禽走兽,只有他和他的羊群。他给天说话,给忽来忽去的风雨说话,给不通人话的飞禽走兽说话,给通人性但不会告密的羊说话。在每次说话前,他都要回环四顾,确信无人时,才极力压低声音,语调急促粘稠,说了些啥,他自个也不知道。他只是不停地说,把一天要说的话搜肠刮肚说完,说得口干舌燥,说得自己烦自己,自己憎恨自己,说得听见人说话,耳朵和嘴巴自动关闭,说得每当有了表达欲望时,就有自抽嘴巴的冲动。不这样又该咋办?说实话的,不忍心,说假话吧,他不懂得什么伪证之类的官话,他只觉说不出口。多亏了生在这样一个好时代,事情只要不是你做的,你爱说,说,不爱说,算尸求。要是包青天审案子,打板子,他绝对扛得住,咱皮实着哩!他有这个自信,上老虎凳,他也能凑合几回合。要是把明晃晃的虎头铡,呵,不对,咱一个放羊娃,哪配得上用人家那个送官员上西天的东西呢,给咱用的是狗头铡,人家把狗头铡放在咱面前说,你说不说?不说,就铡了你!那时候,他可不敢保证自己不说。死倒是无所谓的,咔嚓一声,一了百了了,可我的婆姨咋办,我的儿女咋办?咱是为了让别人的儿女能够活下去,才这样做的,反倒把自己的儿女撂下没人管,人咋说我哩,是不是说我是个二杆子,脑子不整齐?好在,这都是自己的瞎想。改改的公公婆婆告得不行,而且一口咬定索索是知情者,后来又升格为同谋者。公安被闹得没法子,又问过他几次,一句人能听的话都问不出来,就不再问了。
开始沉默的那段日子是最难熬的,多少次,索索都想痛快地吼几声,可他一次次忍住了。为了灭绝说话的欲望,他站在山尖上向沟底扔土块。日复日,年复年,二十年下来,土块越扔越远,想扔哪儿,百发百中。他的右臂比左臂粗了一圈。而哪天不扔一会儿,便坐卧不宁。过了几年,改改的公公婆婆相继过世。老两口就一个儿子,而儿子又没给他们留下孙子来。这老两口都是老脑子,把孙女不当孙子看的。改改在给婆婆过完百日的一个午后,借口挖柴来到荒沟牧场。四顾无人,她向索索蹀躞而来。走到索索跟前,她一膝跪倒,叫一声:他叔,我们母女给你磕头了。我啥也没有,就这一个烂身子,你要是不嫌弃,随你用用吧。当改改身上露出一片白肉时,索索赶上几步,扬鞭在那块白上抽出一道红来,然后,掉头不顾而去。
改改朝索索的背影磕了一个头,也走了。索索从她的背影看出了她的轻快和欢欣。这一刻,他泪流满面:死了的已经死了,活着的还得活呀,还有三个娃娃呢,撂给谁呀!
如今,改改的小女儿已经订婚了,大女儿二女儿都有了自己的孩子。改改的葬礼过后,姐妹三人来到索索家,齐齐跪在地上说,我妈留下的话,说我们欠了你二十年的话,你咋骂我们,骂多长时间都行。索索一一扶起她们。长叹一声说:我只有一句话,年头节下,别忘了给你爹你妈上坟。
原刊责编 赵剑云
【作者简介】马步升,男,1963年生,甘肃合水人,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已发表小说、散文、学术论著四百余万字。曾获中国人口文化奖、敦煌文艺奖等十余种奖项。现在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