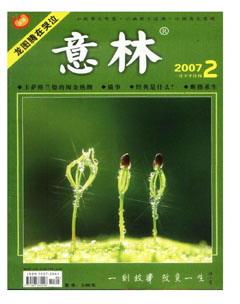斗蟋蟀
刘湛秋
建国前,在我的家乡——江南的小城,我们小巷子里几乎家家玩蟋蟀。家家床下都藏了好多盆,谁要乱动了,和你拼命。我七八岁的时候,瞎凑热闹,蹲在旁边看别人的蛐蛐两军开战,用捻子一撩,蟋蟀便起了斗性。会用捻子撩的,能让蟋蟀团团转,杀戒大开。两只咬起来,真有天旋地转、飞沙走石之势。
我一个邻居是国民党的逃兵,二十四五岁,无业游民,也参加了我们孩子玩蛐蛐的行列。他给我讲了不少蛐蛐的事。最厉害的蛐蛐叫红头将军,然后是白玉翅,还有大红袍、一点红、青玉都是有名的品种,有的一盆好蛐蛐能值万贯家私。抓蛐蛐不能只在院里抓,也不能在收割过的地裂缝中去掏,那都不是好蛐蛐。真的好蛐蛐藏在荒山的乱石中,尤其在棺材旁或棺材缝里才有好蛐蛐。这使我大为恐怖又大有兴趣。但好蟋蟀与棺材、死人有什么关系,理论上未加以阐述。
有一天晚上他和另两个孩子出发到野外了。我们真的去了野坟荒冢。我们竖耳细听,寻找真正的将军。星稀天低,秋风萧瑟,树影幽黑,添了神秘的恐怖感。我们带了罩子、竹筒、勾子等捉蛐蛐的工具,还有一只电筒,我们都有上战场并视死如归的气概。我运气好,抓了一只大的,而且我感觉是红头。我偷偷地灌进竹筒,准备明天作保留节目出台。我的邻居也抓了几只。哆哆嗦嗦,熬了半夜,总算满载、而归。
第三天上午,向一玩家挑战。我夸口说:“我这只蛐蛐,放进盆,可能把你们吓死了,差不多就是红头将军!”
一放进盆,惹得所有人都哈哈大笑,个头是大,也是蟋蟀的模样,可不能开口,更不能厮杀。原来是个蟋蟀的变种油葫芦!
我邻居的放了进去,倒是真蟋蟀,一副好模样。见捻子也开了口。但见交战的对方却转了身,再用捻子捻过来,开了几口又收了。对方追,它就跑,双方竟始终交战不成。孩子们都笑了,逗邻居说:“它跟你一样,是个逃兵吧!”
年轻的邻居放了一场高论:“夫逃兵者,有二也!一是以为此战不义,放弃也;一是以为对方档次不够,不屑为伍也。”这以后,那只被他称黑玉豹的蟋蟀,果真杀败了巷子里头号选手!这位大仁兄本人在几年后果然也成了气候,为江南一小富豪。
我信服了他。从此,我对“逃兵”也有了新的第二层的认识,不能一概以怯懦论之。
(张小洁摘自《寻找自己》
图/杨志平)